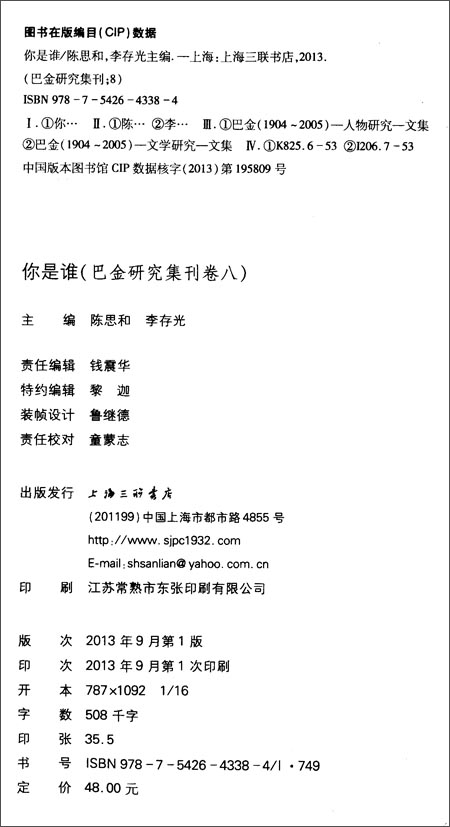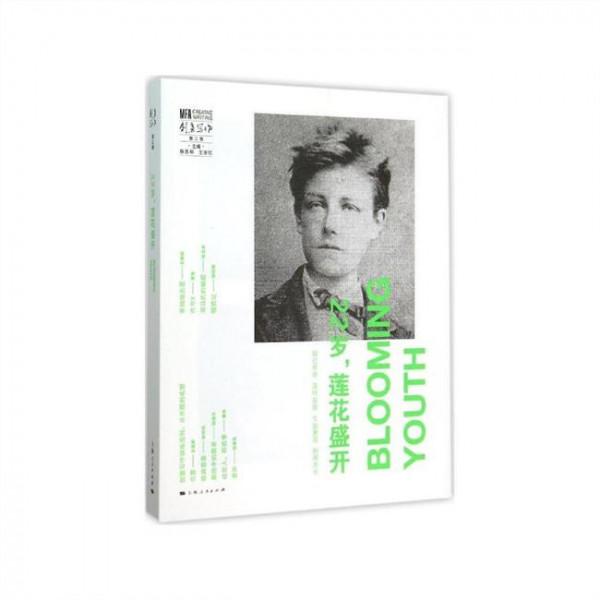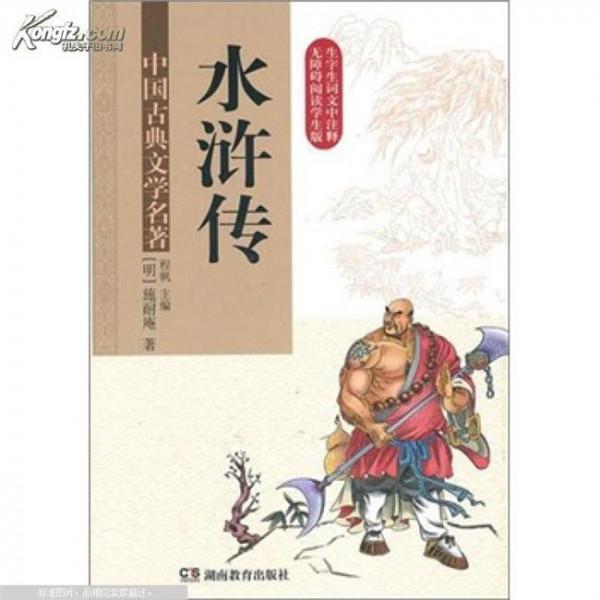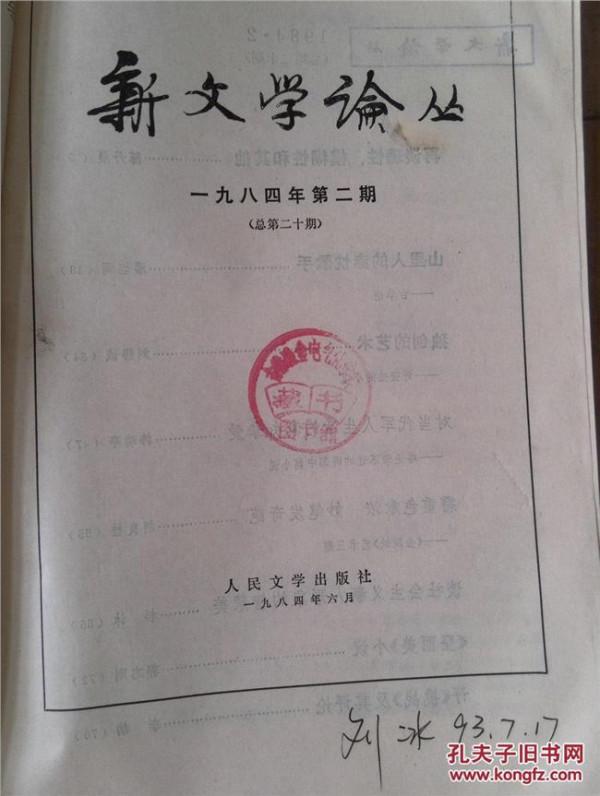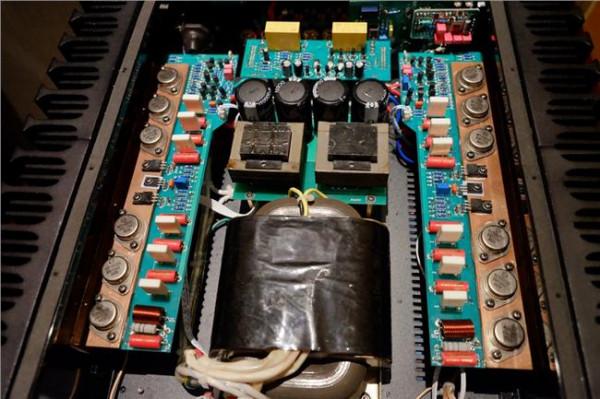陈思和《文学评论》 许子东:八十年代的《文学评论》
许子东,1954年8月生。现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郁达夫研究、张爱玲研究、“文革小说”研究等,著有《郁达夫新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香港短篇小说初探》《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等。
八十年代的《文学评论》
许子东
我之所以走上“文学评论”这条道路,第一是因为我的老师钱谷融先生(钱先生今年99岁),第二就是因为《文学评论》这个期刊(今年六十岁,祝贺)。
从1981年在《文学评论丛刊》(第8期)发表《郁达夫小说中的主观色彩》起,到最近一篇论文《“文革故事”与“后文革故事”——读莫言的长篇小说<蛙>》(2013-1),我总共在《文学评论》发表过十篇论文,约十六万字。
三十多年十篇论文,也不能算太多。但是我的一些重要的文章,大都发表在《文学评论》上。而且其中最早五篇有关郁达夫的文章(7-8万字),全发表在1981-1984三年之间。没有《文学评论》的支持,我最早的《郁达夫新论》几乎不可能完成(那么浙江文艺李庆西他们后来会不会推出 “新人文论”丛书呢?我后来会不会一直在大学里教书呢?也很难说)。
人生道路回头看,充满偶然性。
记得1979年刚进华东师大,宿舍里室友聊起《文学评论》,都很崇敬的表情。我以前读工科,竟然不知道这个期刊,曹惠民说你没看过“文评”,怎么考的研究生?令我十分惶恐。最初的论文是钱先生通过好象是董秀玉的辗转推荐,当时和我联系的编辑是王信。
王信从名字到书信都是清秀文气,数年后在哈尔滨参加现代文学年会,见面才知是一威猛粗犷豪爽的汉子。会上见到很多各地大学的教授主任院长围着王信“套近乎”,我很不解。这些教授们也很奇怪,怎么这个人当时已连续在“文评”上发文,却不认识王信。那时候的作者与编辑的关系,真的比较纯粹。
稍后,我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郁达夫风格与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在《文学评论》(1983-1)发表,附了一个标出年龄的作者简介,当时引来很多关注。这篇文章后来还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优秀理论文章二等奖”。
一等奖是钱中文批评现代派的论文。令我惭愧的是乐黛云和赵园的文章,是我很佩服的文章,却只获得三等奖。作为获奖代表发言后,我和樊骏、黄子平一起到王信家里吃了一顿便饭。吃的东西很简单,讲的是接下来应该如何在评论和研究上出“干货”。印象里王信的家很小,但回想起来,那个时期《文学评论》王信和他的同事们对中国文学评论的贡献很大。
我只是八十年代在《文学评论》上出现的一批“年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个,而且远不是最有成就的一个。在北京,通过《文学评论》,我认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友(我从那时起知道,通过阅读文章比通过友谊交往更能认识一个人):钱理群、赵园、吴福辉、王富仁、黄子平、陈平原、蓝棣之、温儒敏、刘纳、汪晖.
.....在上海,我也有一班同行,大都通过李子云主持的《上海文学》而认识:吴亮、程德培、蔡翔、陈思和、王晓明、夏中义......我后来才知道我很幸运,因为在那个呼唤期望诗和远方的浪漫启蒙的八十年代,中国最重要最有成绩的文学评论杂志,就是《文学评论》和《上海文学》(理论版)。
去年我在《文艺理论研究》(2016-3)上发表一篇论文《现代文学批评的不同类型》,尝试从文学史学术史角度讨论这个大问题:学院批评怎样影响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变化发展?我所谓的“学院批评”是和“作家批评”和“党派社团组织批评”相对而言的。
“回顾起来,其实五四作家文人大都也曾在高等学府教书,不过新文学创作多为课外兼职,学院批评还是以古典为主(如鲁迅、闻一多、郭沬若等)。现代文学(作为学科)进入学院课堂应该还是在朱自清的学生王瑶以后。
在五六十年代,学院的文学批评基本贯彻党派组织批评,成为自上而下文艺观的教材普及版。包括王瑶在内的教授们改造思想与时俱进,有时还是赶不上形势。一不小心如钱谷融等,做文学批评反而成为同行专家和学生进行“文学批评”的对象。
如北大中文系学生在50年代中期编的文学史,倒是可以证明,当时学院批评基本上就是“学生批评”。学院批评真正介入当代文学的进程,是在80年代初,也就是组织党派批评内部文艺论争相持不下各抒己见的所谓“五四”以后的“第二个启蒙时期”,一边要解放思想,一边要注意社会效果,一会儿强调创作自由,一会儿要清除精神污染…… 80年代大学体制正在恢复,重新获得话语权的老专家与不同年龄层的新人们互相促进,既重建学术规范,也面对尖锐的问题。
”《文学评论》(特别是“我的文学观”栏目)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参与介入了80年代的中国文学,其历史作用值得总结。
“但80年代很短”,在同一篇论文里我接着说:“学院批评很快被一种看上去更‘学院’的学术研究秩序所取代,学院于是又悄悄退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主流。这是一种被李泽厚和陈平原或贬或褒称之为‘从思想到学术’的转变。
具体说是从注重思想锋芒到讲究学术规范,从强调文化影响到关心项目资金的转变。90年代后学院批评的这种转变,一方面适合大学体制国际化同步,另一方面也和国家对文学管理方法的转变有关。”当然,在近二十多年重建中国文学评论的学术秩序和研究规范的进程中,《文学评论》也毫无疑问起了很大的作用。好像现在年轻一代学人要评教授,《文学评论》至关重要。我所任教的香港岭南大学,也将《文学评论》列为A级学术期刊。
但我还是很怀念当年的《文学评论》,以及那个时代那种气氛。我还是固执地不无偏见地认为,《文学评论》六十年了,八十年代是她最可爱最闪光也是对中国贡献最大的一个时期。
后来我有自以为重要的文章,还是想投稿“文评”。“新时期文学十年”研讨会上我读了一篇《新时期的三种文学》,两万多字,较早提出“通俗文学”与主流文学的相通之处(共创性)。后来还有篇二三万字的《新时期文学与现代主义》,是为一套最后没有出版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评论大系》(现代主义卷)写的序言,也发表在《文学评论》上。
我前些年做的有关“文革集体记忆”的研究,也有一篇寄给“文评”,董之林审稿时对我说,你当年写郁达夫的论文,文字多么清新流畅。我明白这是在婉转批评我近作技术繁复文字艰涩。这是追求“学术性”的必然代价吗?我在反省,《文学评论》的很多作者读者,或者也有类似的思考。
期望《文学评论》继续保卫自己的学术原则,也期望《文学评论》能够再现昔日的思想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