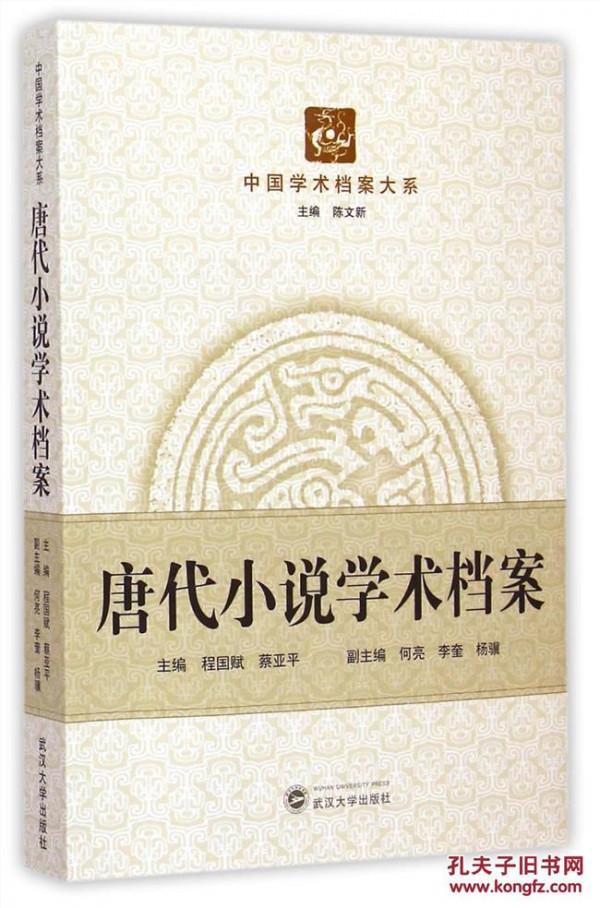陈染女儿 从陈染的小说看新生代女性主义写作
从陈染的小说看新生代女性主义写作 从女性主义立场纵观当代女作家陈染的小说创作,正是性别精神立场使她创制了一套个性化女性叙事原则,以对于女性心理和感知的深度开掘构成奇特审美世界;想象的丰富奇诡跨越时空幻觉与意识流动,把女性心理情节的曲折复杂蔽亮于语言,女性主体反抗与自救的冒险足迹,构成陈染“自叙传”或“自画像”式写妇女的文本序列。
以《私人生活》为代表的个人化叙事作品,作为90年代自觉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在建构女性话语和塑造真实复杂的女性人物形象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在《私人生活》中,陈染在倪拗拗和父亲、班主任T和先生尹楠的男女关系的书写中将女性人物放于主体和张看的位置上,清晰地显露了作为书写者的女性对男权文化大一统规范下男女性别角色的反转,对两性角色的重新定位,也显露了女性写作试图建构独特女性话语的写作姿态。
我们知道自从母亲社会父亲社会取代后,菲勒斯中心意识便从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对女性施行强制压制,使女性成为边缘处境中用以证明男性价值的“他者”。
“家”则是实施这一压制策略的关键场所——在中国,“夫受命与朝,妻受命与家”的社会分工将女性逐出社会,禁锢在狭小的生活圈内;“夫者妻之天的封建礼教将男性看作是主体和超越,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庸,是一种不具主体性的“物”的存在;在西方,菲勒斯中心意识通过对女性气质、女性价值的宣扬,使女性自动回到家庭,安于操持家务、生儿育女的性别角色。
在许多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成了体现男性审美理想的介质、贞洁、顺从、贤淑、无私……,这些都是男性审美规范中作为“天使”女人的标准。
对此,女权主义者吉尔伯特和格巴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她们变成了艺术对象还是圣徒,她们都回避着她们自己——或她们自身的舒适,或自我愿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就是那些美丽的天使一样的妇女的最主要的行为,更确切地说,这种献祭注定她们走向死亡和天堂。
因为,无私不仅意味着高贵,还意味着死亡。
像歌德玛甘泪这样没有故事的生活,使真正的死亡死亡生活,是生活在死亡中。”这种女权神圣化为天使的做法,实际上是将男性的审美理想寄托在女性形象上,正如西蒙?波娃所指出的那样,她们只是一种对象性存在,没有自由意志。
陈染在她的小说中以形象化方式传达了与伍尔夫类似的女权思想,即女性要敢于面对这一事实:“没有人会伸出手臂来挽扶我们,我们独自行走,我们要与真实世界确立联系,而不仅仅是男男女女芸芸众生的物质世界建立联系”,这样,“我们”(指女性)才能摧毁自己目中的父权形象和精神上的依赖性,发现自己本身存在的力量。
所以,陈染笔下的女性与女性传统迥然不同,敢于主动地背叛,但这种背叛并非简单的“乾坤颠倒”,而是,在当代社会中,强者生存的境遇使女性逐渐意识到:失去爱情,一切还可以重来;失去自我,一切都失去了。
陈染用文字,对传统的创作方法进行了爆破,她沿袭独特的创作思想为自己建构了一套在中国大陆上被称做是“独一无二”的写作模式,尽管这模式还存在一些缺陷与遗憾,但它还是证明了陈染已用自己的方式,告别传统、走向世界。 文:仰望蓝天的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