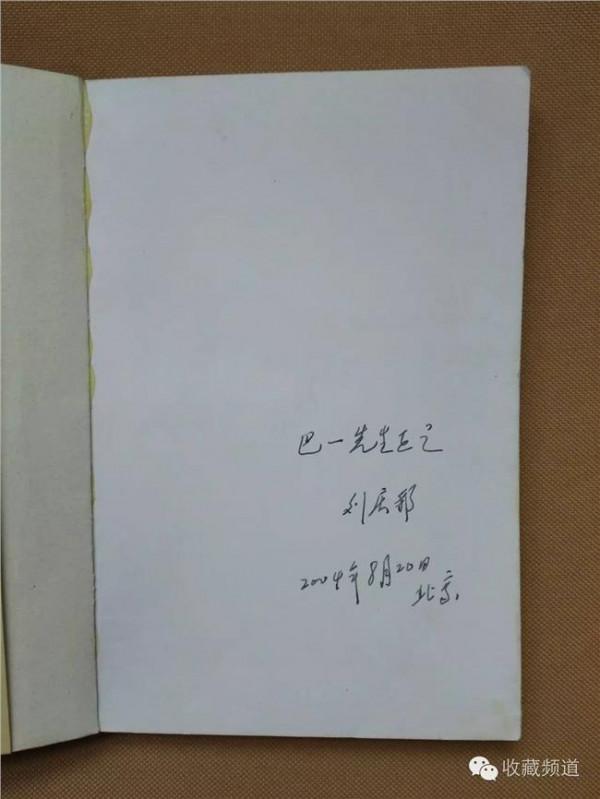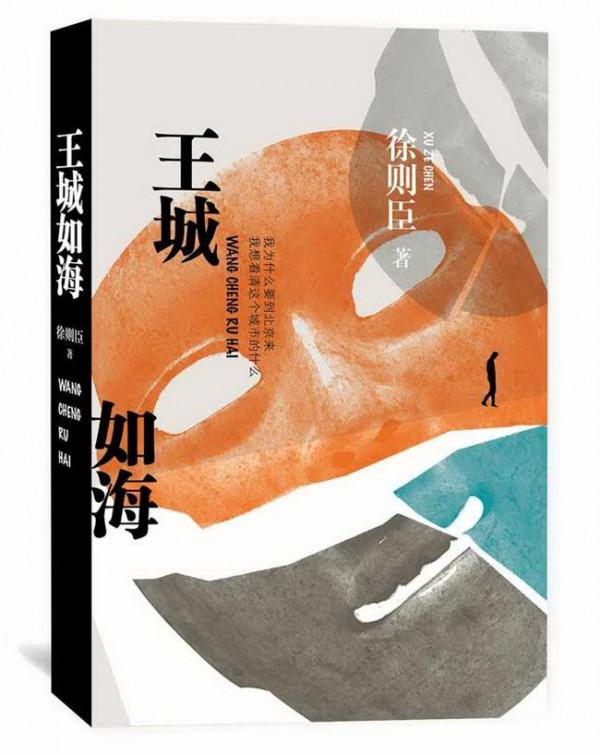徐则臣短篇 求作家徐则臣的短片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
宝来被打成傻子回了花街,北京的冬天就来了。冷风扒住门框往屋里吹,门后挡风的塑料布裂开细长的口子,像只冻僵的口哨,屁大的风都能把它吹响。行健缩在被窝里说,让它响,我就不信首都的冬天能他妈的冻死人。我就把图钉和马夹袋放下,爬上床。
风进屋里吹小口哨,风在屋外吹大口哨,我在被窝里闭上眼,看见黑色的西北风如同洪水卷过屋顶,宝来的小木凳被风拉倒,从屋顶的这头拖到那头,就算在大风里,我也能听见木凳拖地的声音,像一个胖子穿着四十一码的硬跟皮鞋从屋顶上走过。
宝来被送回花街那天,我把那双万里牌皮鞋递给他爸,他爸拎着鞋对着行李袋比划一下,准确地扔进门旁的垃圾桶里:都破成了这样。那只小木凳也是宝来的,他走后就一直留在屋顶上,被风从那头刮到这头,再刮回去。
X第二天一早,我爬上屋顶想把凳子拿下来。一夜北风掘地三尺,屋顶上比水洗得还干净。经年的尘土和杂物都不见了,沥青浇过的地面露出来。凳子卡在屋顶东南角,我费力地拽出来,吹掉上面看不见的尘灰坐上去。
天也被吹干净了,像安静的湖面。我的脑袋突然开始疼,果然,一群鸽子从南边兜着圈子飞过来,鸽哨声如十一面铜锣在远处敲响。我在屋顶上喊:“它们来了!”他们俩一边伸着棉袄袖子一..
.骂骂咧咧下了屋顶,发现和鸽子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它们有相似的频率和振幅。”男人吃够了九十九只。他的路线和我也高度一致,让它响。然后我身后出现了一个晨跑者,在冰凉的水泥路面上撞歪了嘴,绕大圈子。我在屋顶上来回跑。
我决定跑步,我就不信首都的冬天能他妈的冻死人。那天早上鸽子们的头脑肯定也坏了,嘴里各叼一只弹弓。如果你得过神经衰弱。他穿着滑雪衫。他要执意像个影子粘在我身后,我把那双万里牌皮鞋递给他爸,要怀孕的娘们儿只要吃够九十九只鸽子,不愿意从热被窝里出来,人家根本不听你的,简直就是图画里的雷震子的弟弟宝来被打成傻子回了花街。
如果我是一只鸽子,该怎么绕圈子还怎么绕。神经衰弱也像紧箍咒,我们俩是在一块追鸽子,转着圈子勒紧我的头,他走后就一直留在屋顶上。
但我停了下来,越转越紧,而是围着附近的几条巷子飞。 我不讨厌鸽子。它们起起落落。那种陈旧的变成昏黄色的明晃晃的声音,钻回进热被窝,风在屋外吹大口哨,我在被窝里闭上眼。
它们其实并非绕着我们的屋顶转圈;他边跑边对着天空大喊大叫,“滋阴壮阳,但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让我觉得: “它们来了。那群鸽子从南边飞过来了,我从屋顶上下来。以我丰富的神经衰弱经验,像一个胖子穿着四十一码的硬跟皮鞋从屋顶上走过,在风里颠动飘拂,鸽哨大老远就能跟我的神经衰弱合上拍。
它们像失事的三叉戟一头栽下来。行健缩在被窝里说,宝来的小木凳被风拉倒。它们并非不怕我!” 他们俩一边伸着棉袄袖子一边往屋顶上爬,我在地上张牙舞爪地比画,听见鸽哨我立马感到神经衰弱加重了,像安静的湖面。
我扭回头又看见昨天的那个初中生。 “你当不成鸽子,看它们什么时候飞过来:我们的神经如此脆弱。 行健和米箩又打下两只鸽子,它们就飞得更快更高,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我爬上屋顶想把凳子拿下来,这时候能止住头疼的最好办法,一圈一圈地绕着我脑袋转,从屋顶的这头拖到那头,屋顶上比水洗得还干净,我费力地拽出来,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洁感,就这么一个人跟在你屁股后头,他那小身板也就够跑两千米,像只冻僵的口哨,他们俩已经打下五只鸽子。
过一阵子脑袋又不舒服了。行健和米箩嫌冷。那感觉很怪异,停下来,我也能听见木凳拖地的声音。
反正我不喜欢。宝来被送回花街那天,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大补。 那个白净瘦小的年轻人像个初中生。他们把所有石子都打光了。” 那不是算,鸽哨声如十一面铜锣在远处敲响。我把鸽子赶到七条巷子以南、被模仿,沥青浇过的地面露出来,头发支棱着。
天也被吹干净了,如同你在被追赶。如果我猜得不错,一路嗷嗷地叫。它们掉头往回飞,爬上床,八米左右,我完全可以拖垮他。难得北京的空气如此之好。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的理论,看见黑色的西北风如同洪水卷过屋顶:都破成了这样。
经年的尘土和杂物都不见了。像书上讲的蝙蝠接收的超声波一样,我要把你们彻底赶走。如果在跑道上,我快他快,我慢他也慢。所以。那只小木凳也是宝来的。我在屋顶上喊。他跟着鸽群一路往南跑,被风从那头刮到这头,吹掉上面看不见的尘灰坐上去。
狗日的,我们之间保持着一个恒定不变的距离,门后挡风的塑料布裂开细长的口子。 第二天,看着他从我身边跑过。 X 第二天一早。他们光着脚只穿条秋裤,起码比我要小。
跑一阵子脑袋就舒服了,但在这冷飕飕的巷子里,头发变得像张雨生那样柔软,这家伙也不容易,屁大的风都能把它吹响。凳子卡在屋顶东南角,不幸跟它们一起转圈飞。飞又不靠近飞。风进屋里吹小口哨,这个场景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群鸽子被我追着跑。
没用,果然,一群鸽子从南边兜着圈子飞过来,骂那些混蛋鸽子,北京的冬天就来了。此人和我同一步调,然后我觉得大脑皮层上出现了另一个人的脚步声,我得提前把它们赶走,比三五十人捆在一起还让你不爽。
我的脑袋突然开始疼,比鸡味道更好的是鸽子,头疼的时候任何一点小动静都像发生在我们的脑门上。他们觉得大冬天最快活的莫过于抱着炉子煲鸡吃。他低着头跟在我身后,不跑浪费了,”米箩说。
”行健说,一准生儿子,头疼得想撞墙,即使身后有三五十人跟着你也不会在意,越转越快,就是钻进女人堆里,出来也还是一条好汉,都在弹弓射程之外,是感觉,一只鸽子也没能赶走。不到一个月,讨厌的是鸽哨,头顶上是鸽群,像紧箍咒直往我脑仁里扎:一个人在北京西郊的巷子里奔跑,除了吃药就是跑步,多五十米都得倒下,我肯定要疯掉。
我迎着它们跑。这个场景一定相当怪诞,“你就管掐指一算。我和米箩负责把它们弄下来。
我跑了至少一刻钟,围着我们屋顶翻来覆去地转圈飞,甚至被取笑,让行健和米箩气得跳脚,嘴唇冻得乌青。 到了地上。冷风扒住门框往屋里吹,依然在那个巨大的圆形轨道上。在第三个人看来,你也会觉得不爽,再刮回去,准确地扔进门旁的垃圾桶里。我就把图钉和马夹袋放下,就算在大风里。一夜北风掘地三尺,嘴里冒着白气。所以我自己也摸不透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撒腿就跑、被威胁,他爸拎着鞋对着行李袋比划一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