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陈国富 胡金铨杨德昌侯孝贤李安魏德圣台湾电影三代导演代表群像素描
那一代前辈中与胡金铨并驾齐驱的台湾导演,是江南才子李行。有趣的是,这位上海籍导演关注的不是市民世界,而是乡村田野那种洋溢着泥土芬芳的纯朴人情。即便是片名,都充满这样的情调,诸如《养鸭人家》《小城故事》《吾土吾民》之类。
仅就审美情趣而言,李行的电影是哈代式的怀旧,也是小津安二郎那样之于纯朴人情的守护。当然,李行从来不用小津风格的长镜头。但李行的《养鸭人家》,绝对不比小津的《晚春》逊色。区别只是,同样的父女情深,李行叙述得淋漓尽致,小津讲说得含而不露。
与之相反的一个对比是,小津在《东京物语》里之于人情凉薄可谓一唱三叹,而李行的《小城故事》却将一首恋曲写得举重若轻。《小城故事》的完美在于,导、演、画面、插曲,无不丝丝入扣。最美的民间传奇,也不过如此。似可如此描述此片的魅力,即便过了一千年,倘若要找出一部原汁原味的华语影片,非《小城故事》莫属。
但李行的巅峰之作,窃以为,当属《秋决》。该片立意之深邃,犹如胡金铨的《空山灵雨》。其电影叙事,可说是完美无缺。而整个叙事基调,又一如既往的纯朴。至于整部影片的聚焦,又是李行所擅长的,开掘人性的底蕴。几乎所有的情节,与其说是导向故事结局,不如说是指向人性堂奥。
至于其中的每一次转折,都引发了人性深处的剧变。不仅囚徒在剧变,囚徒的祖母、祖母的侍女、甚至看守囚徒的典狱长,全都跟着一变再变。最为震撼的挣扎,发生在牢房之中,发生在等待秋决的死刑犯身上。
最后,死囚上路,走向刑场之际,一切剧变都业已完成。临刑的死囚,平静如水。典狱长一声叹息之后,也随之平静了。即将成为未亡人的囚徒女人,更是在垂泣中接受了冷酷的命运。对比卡夫卡《审判》中的冷峻,《秋决》呈现出的是暖色。《审判》的基调是荒诞,《秋决》想要诉说的是如何从荒诞中解脱。
李行的电影,从不陷入绝望的泥潭。或者说,总是让希望与死亡同在。由秦汉和林凤娇主演的《汪洋中的一条船》和《原乡人》,皆以男主身亡作结,却都给未亡人、给身后的家庭、甚至给观众,留下了满满的希望。死者已逝,希望生者活得更好。
此种亮色,在《养鸭人家》里是非亲生的女儿与养父和好如初,在《小城故事》里则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李行与哈代很不相同之处。哈代之于人世间乡野诗情的毁灭是痛心疾首,旷野呼告不已;李行之于人间的纯朴温情,犹如一位守护使者。即便是死亡,也不能使之消失殆尽。
或许是如此的守护,致使李行的影片总有天使般的女主角出现。诸如《养鸭人家》里的女儿,《小城故事》里的哑女,《汪洋中的一条船》里那位贤妻,《原乡人》里与一生做着文学梦的少爷私奔然后受尽煎熬的那个不识字的乡下女人,更不用说《秋决》中最后与死囚成婚的那位女侍。
所有这些女子,都以自己的坚韧不拔、忠诚奉献成为男性世界的守护者。这在当今的女权主义者看来,也许是愚蠢的,不可接受的,但这在李行的电影里却无疑成为女性之于世界的一种救赎方式。
她们好比伦勃朗画面上的那道顶光,在照亮他人的同时,也照亮了整个世界。只消走出家门,她们就成了特蕾莎修女。反过来说,倘若特蕾莎修女返身走回家庭,就变成了李行影片里的那些女主角。事实上,《秋决》里的女主角,就是特蕾莎修女在牢房里的死囚救赎版。正如胡金铨的《空山灵雨》成为中国武侠电影的一个标高,李行的《秋决》也标画出了一个为华语电影所难以企及的审美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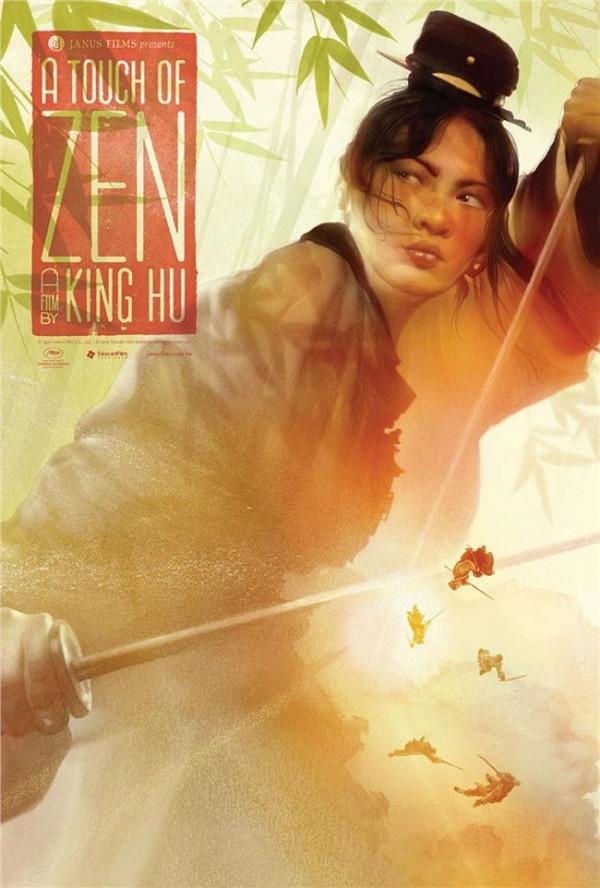




![>刘若英陈升陈国富 [转帖]刘若英夜带导演陈国富回家 疑十年交情升级](https://pic.bilezu.com/upload/1/3e/13eb921f3a99570da2f827dc337c99d3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