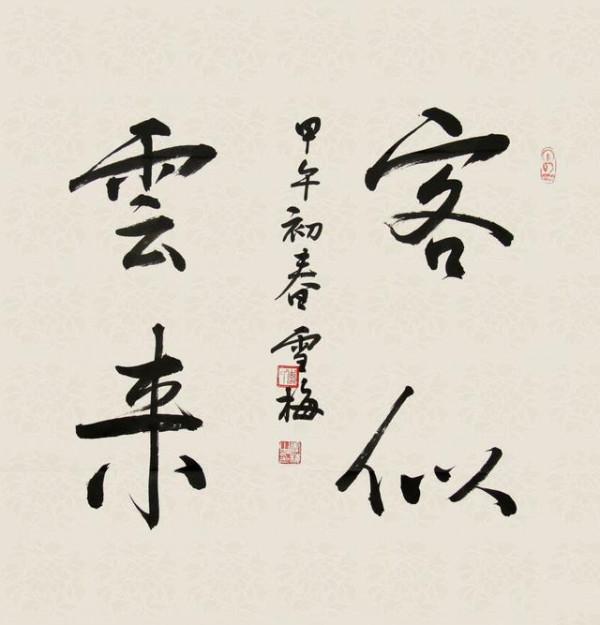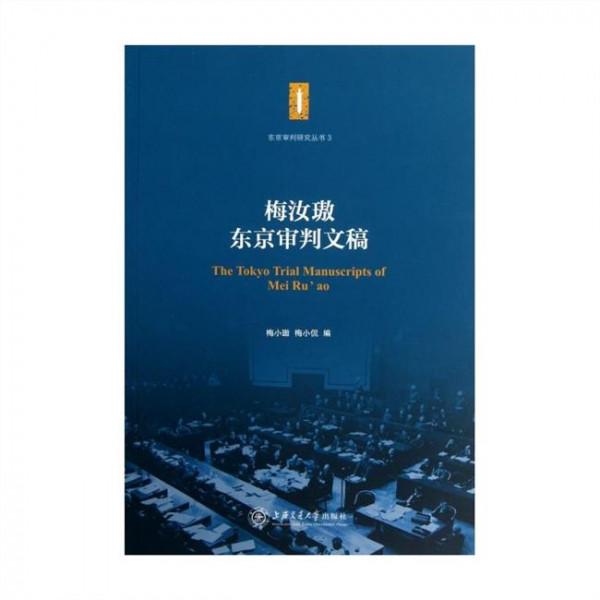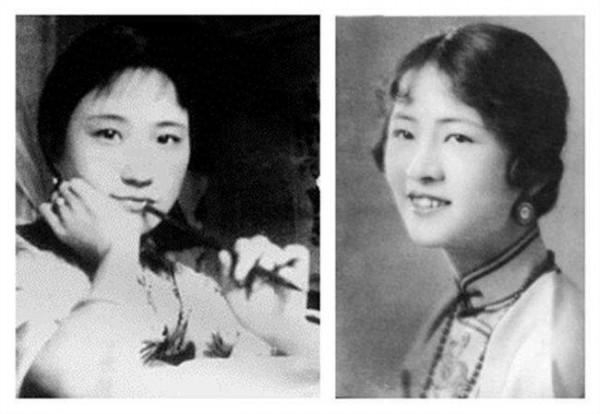陆梅的书 陆梅:沿着那条我们从未走过的甬道
编Saying: 陆梅的《格子的时光书》日前获得德国国际青少年图书馆颁发的2014年白乌鸦奖(White Ravens),该奖系每年从五十多个国家的三十多种语言的儿童文学作品中选出。沿着“甬道”,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创作者的心路历程。
过去可能存在和已经存在的 都指向一个始终存在的终点。 足音在记忆中回响 沿着那条我们从未走过的甬道 飘向那重我们从未打开的门 进入玫瑰园。 ——引自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汤永宽 译)
姐姐在微信里发图,说爷爷的墓3月31日迁葬。小狗妞妞伫立田间地头做“最后守望”。清和明丽的阳光打在妞妞金闪闪的脊背上,晃得我眼睛生疼!家乡很快要被夷为平地,新一轮的旧城改造“已全面启动”——我在前一日的报纸上找到了佐证:“松江区旧改加速:让百姓早日解困,让老城焕发活力”,跨版标题粗大的黑字宣告了一个铁的事实:父亲母亲和村子里住了一辈子的乡亲都得迁往别处去居住。
家里至亲的墓地也不得不迁出。古话说:“穷不改门,富不迁坟。”万般空茫愁绪无语凝噎!
——从此后,我再也不能早春时节念念着老家门前那棵紫玉兰,相逢一场“纷纷开且落”的辛夷花事;再也不能坐在庭院天伞般华盖的老桂树下,和家人一起说话喝茶、无限欢喜了!从此后,“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鲁迅)
心念一闪,想到这日凌晨的梦境,悚然一惊。清楚记得睡梦中突然感觉到我的床前站了一个人,明明含着笑,还是吓了我一跳。他似乎有话说,却被我的蒙头一惊搅了气氛。这个人,个子不高,穿对襟靛蓝粗布衣、束一袭大腰布襕,长及脚背的宽大布襕,装得下一个小人儿。
他是我爷爷吗?把自己整饬得干净、古风,不论劳作还是去小镇街上喝早茶,都这样一副装扮。那是印在我脑海里的经典画面。果真是他,那么他想要跟我说什么?是来告别吗?还是为家乡容不得他的安宁想来托梦于我,要我记得那些将要和已经逝去的人和事?
在完成长篇儿童小说《格子的时光书》后,我曾起意写写爷爷——“一个人和他命运的友情”,余华对《活着》的评价令我心有所动,我也想写下一个故事,时间的故事——多大的主题也莫过于时间的主题,一切悲怆的故事莫不是时间的故事,所有浩大的成本莫过于时间的成本。
书名我都想好了:《再见,婆婆纳》——还是以漫生野长的乡间草木为引子——《格子的时光书》里是鸭跖草,这本爷爷的故事里是阿拉伯婆婆纳,它们都开蓝莹莹的小花,都是女孩格子熟稔并喜欢的。
但鸭跖草花顶着晨露而开,只开一上午,太阳一出就凋零了。一如小说里格子和男孩小胖的叹息:原来美的东西都不长久啊……而阿拉伯婆婆纳却有着强劲的生命力,田间、坡地、山冈、坟头,到处是云母般闪烁着蓝光的小碎花。它们就像爷爷的生命。
我脑海里的爷爷可不单单干净古风,还执拗凶悍,小时候的我总和他对着干,想尽一切办法侵入他的领地。那些交织着争吵、赌气、和解、伤害……的日子,水一样漫漫开来,人生何其短暂,容不得我们徘徊、虚假。和格子一样,我在时间里看见了命运。有一天我在心里发愿:我要写写爷爷。还是以女孩格子为视角,还是以故乡小镇为故事发生地,我甚而还新备了一个本子,随手记下想到的素材。
如今为写这小文,我从叠叠复叠叠的书里抽出这个本子,扉页笔迹标着:“2012年8月8日台风中”——我的怠惰啊,无颜以对!倘若没有家乡的拆迁,没有因为拆迁而不得不迁坟惊动了爷爷,是否我真就把这件事给忘了?爷爷偏偏早不来晚不来,就在迁他坟的当日进入了我的梦境,而事先我对此一无所知,父亲顾念我的忙碌不曾告知……
爷爷,是否连你也不满意我的一宕再宕?你一直对我有期待,期待我能为这个家做点什么……眼下、现在,我所能做的,恐怕只有写几个字了。可是我连这件事也做不好,难怪你等不及,亲自跑来给我神启……
“过去是不会真正离去的:我们正在经历着的一切仅仅存在于逝去的瞬间之中。”那个凌晨的“晤面”后,我脑海里总盘旋着加拿大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这句话。过去、现在,说的不就是时间吗?时间里的命运,和命运里的时间。
有那么一刻,当我意识到,原来我可以用笔在纸上再建一个故乡时,所有堵在胸口的凝噎终于有了释放的出口!是呀,这也正是爷爷的期待!
我其实已经这么做了——《格子的时光书》里,我想象了一个芦荻镇:古旧的、安静的、水汽弥漫的,同时也是炙热的、沉睡的、午后的热焰噼噼啪啪爆裂的。还在童年里走着的女孩格子,就在这样一个古镇小街上游荡,百无聊赖,无所事事。
“格子的十二岁夏天,是在暖水瓶的忧伤碎裂声中惊醒的。”这是小说的开头,我在敲下这第一句话时,似乎给小说定下了基调:忧伤的,懵懂的,惊醒的——是一个十二岁少女眼中的世界。而我着力要刻画的,就是这个叫格子的少女,面对一个复杂世界的所有感触、哀愁和心灵的激荡。我特意为小说画了一张人物关系图和小街平面图,我甚至还给小说勾勒了一个梗概。
有一天我写到多年后老梅、格子和瘦猴,昔日童年玩伴在芦荻镇破败的小街上不期而遇,老梅和格子不约而同问起了留在小镇的瘦猴——
“恩养堂的觉持师父还在吗?”
“早圆寂了。”
“那个叫静莲的小尼姑呢?”
“走了,不知去了哪里……”
“还有个和尚呢,叫静守师父的?”
“也不在了……”
“那恩养堂……”
“恩养堂还在,镇政府接管,还在边上建了一所养老院,平日里他们看护庵堂。”
“那就没住持了?”
“有,但是不常来,听说是一个叫觉守的大和尚兼着,他住别的寺庙……”
我流畅而不经大脑地敲下一长段文字,似乎本该如此,就是如此,这在我的写作经验里甚少有过。我似乎总在思考,字斟句酌,改改停停。我的耳边呼啸着老梅心底的呐喊:“小镇啊,你的街道永远寂静!没有一个人能够再回来说:你为何人去巷空一片荒寂?”
写这小说时,不曾想到有一天家乡要被夷为平地。然而家乡仍挡不住席卷而来的变化。曾经熟稔的山丘、竹林、田园、打谷场……仿佛一夜间消失。沿高速公路向故乡进发,眼前不断变换延伸的,不再是清风与花香的稻田,不再是喧腾璀璨一望无边的油菜花,而是高密度的楼盘、热气腾腾的建筑工地。
乡村的概念在改变。视野所及,不再有人种地,人人都向往城市。
记忆里的村庄不再。河流干涸,紫云英寂寞开放。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纷纷涌进,向工业化飞速发展的城郊进驻。——他们正以一种极其谙熟的姿势生活在我童年的村庄。
《格子的时光书》里,我有意安排了一个“插叙”,让读者从格子的小世界里抽一下身,回望或者远看,让长大了的格子踏上返乡之路,给家乡的孩子上一堂阅读课。等待她的,恰是多年前的自己。时间和空间,故乡和他乡,童年“梦中的真”和“真中的梦”,乐土不再的喟叹……以及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但愿读者能够理解我的“一厢情愿”。
一直,我很喜欢童年这个词。我在很多书里寻找童年温暖会心的细节。童年于我是这样一种存在:它静静躺在黝黑山谷间,始终在着,需要你去找回,去唤醒,去完成。而我的一遍遍重返我的童年,仅仅、只是,希图在纸上再建一个故乡——童年所在,才是故乡。
那天,从姐姐微信里获知家事后,晚间吃饭,我说与家人听,十岁小女哀怜地问:“妈妈,为什么外公外婆家要拆呢?能不能不拆?或者是拆了还可以在原地改造?……”小女差不多快到格子的年龄,可她比懵懂的格子经世面得多了。
吃完饭,我净了手,悉心置放友人从金阁寺请回的香炉。我给爷爷点了一炷好香。我抄录了一节T.S艾略特的诗,念给爷爷听:
过去可能存在和已经存在的 都指向一个始终存在的终点。 足音在记忆中回响 沿着那条我们从未走过的甬道 飘向那重我们从未打开的门 进入玫瑰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