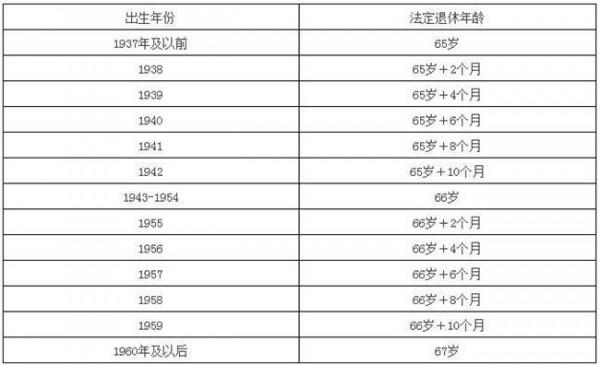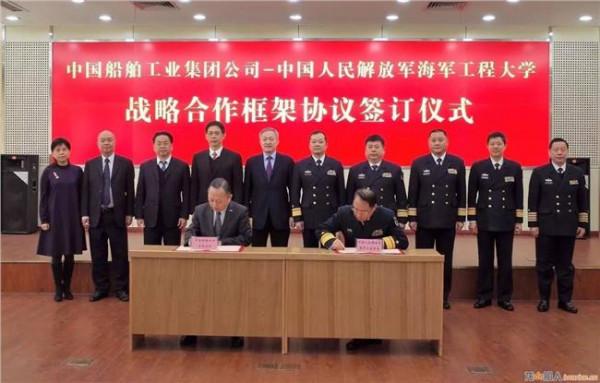董登新水平 董登新:中国社保实际缴费水平远低于法定水平
本文作者为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特邀成员 董登新
特别提示:本文采用的概念是“社会保障”,而不是“社会保险”。因为社会保障是总负担,社会保险只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本文所讲的“社会保障负担”是指雇主缴费与雇员缴费的总和;“实际负担”是指全体劳工实际平均缴费水平(包括无数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
一直以来,民众有一种认识,那就是中国人的社会保障负担远超其他国家。其中,最具代表性、最能吸引公众眼球的一种观点是:“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 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 50% ;我国的社保缴费率在全球 181 个国家中排名第一。”
其实,这一观点存在两大误区 :第一,它混淆了“社保负担”的概念,以偏概全,误导视听。众所周知,所谓一国国民的社保负担,是由雇主和雇员为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而共同承担的缴费总负担。尤其是比较一国与另一国国民社保负担时,必须准确而全面,不能片面、有失公允。
第二,所谓“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 40%”,这只是一种“名义缴费率”的表述。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缴费率的分母,我们的缴费工资基数统计口径相对较小,远低于国外通用的“全部劳动报酬”口径,这无意间夸大了我们的“名义缴费率”。
此外,在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正在走向全覆盖的进程中,农民工、“劳务派遣工”往往被一些企业排斥在社会保险之外。因此,无论我们是否剔除农村“新农保”、“新农合”,中国社会保险的“实际缴费率”并不高,甚至按全部工人数计算的人均实际缴费率也是很低的。
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养老保障与医疗保障是所有类型的社会保障项目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两大构成部分。为此,我们将重点就中美两国养老保障与医疗保障总负担进行比较。
一、养老保障总负担比较
按照制度化的、法定限制的缴费标准来计算,国民养老保障总负担应该由两个部分所组成:一是社会养老保险(即公共养老计划)中的雇主和雇员缴费 ;二是补充养老计划(即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中的雇主和雇员缴费。
在美国,制度化的国民养老负担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国家养老(俗称社保),雇主与雇员总缴费为雇员工资的 12.4%,其中,雇员、雇主各缴 6.2%;第二部分是雇主单独提供的补充养老(主要是指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雇主与雇员合缴限制规定为 :不得超过雇员工资的 25%。
相比之下,在国民养老负担上,中国企业基本上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它们大多数不给雇员提供补充养老(企业年金),只有少数大型企业创设了企业年金计划。因此,在中国,大多数企业承担的养老负担只有单一的“社会养老保险缴费”,雇主总缴费率约为雇员工资的 20%,雇员总缴费率约为 8%,两者合计约为 28%,在有些省市缴费标准要低许多,比方,深圳市和浙江省企业缴费比例仅为14%,而不是20%。
在这里,我们所称的“养老总负担”,是由法律统一规定了缴费最大限额标准的各种养老计划的缴费总和,它是一个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但都必须由参保人自己或与雇主一起缴费。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原因,中国人只有单一的社保,而大多数雇员都没有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也没有个人退休账户,因此,中国人的养老负担比较单一地集中在社保缴费上。
社会养老保险就是中国国民的总养老负担。因此,当我们比较中美两国国民的养老负担时,不能片面地只拿一个社保来单独比较,而应该采用“国民养老缴费总负担”来比较,这样,才能让结论更科学、更准确、更负责任。
二、医疗保障总负担比较
一般地,从法律、制度安排来看,国民医疗保障总负担至少也应该由两部分构成 :一是社会医疗保险(公共医疗计划)中的雇主和雇员缴费 ;二是补充医疗保险(团体健康保险)中的雇主和雇员缴费。在医疗保障负担总水平上,中美两国之间差别很大。美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出现较晚,其主要原因是,雇主提供的团体健康保险在美国不但历史悠久,而且一直占主导地位。
1965 年,美国历史上首次产生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然而,在美国面世的社会医疗保险并不相同于其他国家的医疗保险,它完全借鉴并移植了社会养老保险的基本原理,除肾衰竭等少数几种人群外,所有参保人在整个工作期间必须不断缴费,但只有年满 65 岁的参保人,才有资格享受医保的支付与补偿待遇。
也就是说,参保人在未满 65 岁前是没有资格享受任何医保待遇的。这就是养老模式的美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终身缴费、长期积累、退休享受。不过,美国的社会医疗保险总缴费仅为 2.9%,即雇员、雇主各缴雇员工资的 1.45%。
因此,在美国,65 岁以下的公民,必须依靠雇主单独为雇员提供的团体健康保险,并以此满足雇员本人及家属的医疗支付。也就是说,在美国医疗保障方面,65 岁以上的人靠国家提供的社会医疗保险 ;65 岁以下的人,则靠雇主提供的团体健康保险。为此,有人感叹,在美国,找一份好工作,就是找一个好老板。
事实上,美国人的医疗保障与养老保障一样,也是“三条腿”的体系,除了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险、雇主的团体健康保险外,还有个人健康保险及社会医疗救助,后者主要是为了弥补前者的不足。总体而言,在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医疗保障的“市场化”程度是比较高的。
相反,在中国,医疗保障与养老保障一样,实际上仍是“一条腿”走路,我们企业大多不会给员工提供团体健康保险,个人购买商业保险的意识也比较淡漠,因此,社会医疗保险成为唯一支柱,而且是即投即保,只要你参保缴费,立即就可以享受医保支付待遇。这是美国人所不能想像的。
目前,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标准大体是 :雇员缴费率为工资的 2%,雇主缴费则为雇员工资 6% 左右。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医保总负担约为 8%,高于美国医保 2.9% 的负担,实际上,美国雇主大多提供的团体健康保险,其缴费总负担应远高于中国的雇主。因此,如果将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险与雇主的团体健康保险加起来,美国人的医疗保障总负担明显高于中国人。
三、社保制度覆盖面及制度漏损比较
在美国,社会保险制度起点高、覆盖面广,几乎没有任何制度漏损。与西方国家相比,美国社会保险制度起步相对晚一些,但起点远比西方国家要高得多。美国的社会养老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从一开始就实施“以税代费”,将社会保险缴费以税收形式进行强制征缴,而且由联邦政府实现全国统筹。
因此,美国社会养老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推行,没有城乡、地区和职业差别,只要有劳动收入,就必须强制参保,并同时强制缴费。社保缴费就和普通税收征缴一样,没有雇主和雇员能够偷税、漏税。美国人主动纳税申报意识很强,而且税务稽查也十分严格,偷税、漏税风险很大。由此可见,美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真正做到了全国统筹、全民覆盖,没有任何制度漏损。
此外,作为一个发达国家,美国雇主为雇员主动提供的补充养老(私人养老金)及补充医疗(团体健康保险),是一件十分流行、普及而正常的事情。补充养老与补充医疗被看作是一种雇员福利,同时也是雇员报酬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是雇主对雇员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当绝大多数雇主都为雇员提供补充养老和补充医疗时,它就成为了工会谈判、劳动者维权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农村人口比重大,而且城乡经济水平差距大,地区间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因此,中国社会保险制度起步很晚、起点低。1998 年,中国开始为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建立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直至2011年我们才象征性地建立了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直至2014年10月1日,我们才将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然而,湖北和江苏两省的省直机关及事业单位职工仍在享受传统而落后的公费医疗,他们迟迟不肯进入社会医疗保险(其他省均已进入)。
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最初从城镇国有企业职工试点起步,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努力与改革,参保覆盖面不断拓展,现在已包括了城镇集体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大部分职工。然而,尽管原则上我们已经实现了城镇企业职工全覆盖的社会保险制度,但仍存在重大制度漏损。
比方,进城务工的农民(农民工),他们已成为城镇“企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庞大的劳动力群体,但由于他们流动性大、维权意识差,许多中小企业发现其中有机可乘,一些企业主便通过有意漏报、瞒报,不让农民工参加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这样就可以为企业节省大笔费用。当然,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也是违法的。
此外,所谓的“劳务派遣”,也成为用工单位利用劳动合同法的挡箭牌,大钻社会保险法的“空子”和“漏洞”。据统计,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公司在内的大量企业,常年大规模使用“劳务派遣工”,却不必承担这些“劳务派遣工”的法定社保和福利待遇,“劳务派遣工”参加社保总是短斤少两,比方,五险两金只让你参加“三险”,缴费工资不按雇员实际工资,而是“一刀切”地采用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60%作为缴费工资的最低标准。
此外,在劳动合同上,许多中小企业雇主公然违反劳动合同法,比方,法律规定最长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而大多数中小企业却有意将合同期延长为一年;法律规定从雇员入职当月起就应加入社保并为他们缴费,而这些不良的雇主却不让雇员在试用期内参加社保,这既是对劳工福利的剥夺,也是一种变相的剥削,更是一种用工歧视。
显而易见,从社保覆盖率及缴费水平来看,中国社会的实际社保负担,是远低于法律规定要求的“名义负担”的,即便我们完全撇开覆盖面更广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因为如果将农村社会养老与社会医保也计算进来,则全体国民的平均缴费率(社保负担)更低。
更何况,中国绝大多数企业都没有为雇员提供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补充医疗保险(团体健康险)!哪来中国社保负担(雇主与雇员总缴费率)世界第一?
四、中国社会保障负担急需分散化、均衡化
中国单一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以及单一支柱的医疗保障体系,无形之中加大了国家财政的负担和压力。同时,国家支柱的社会保险给付的“替代率”偏高,严重挤压并抑制了雇主提供的补充养老如企业年金,和补充医疗如团体健康险的发展空间。因此,美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坚持三条腿走路,可以使国家、用人单位及家庭个人这三大支柱能够均匀受力,才能分散社会保障的过大压力与风险,并让三方负担的论坛原则得以有效贯彻实施。
以养老保障为例。很显然,与美国相比,我们应该大幅降低社会养老保险给付的替代率,并实质性地降低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水平,比方,将雇员缴费率降至 5% 左右,将雇主缴费率降至 10%左右。 与此同时,鼓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大发展,激励雇主为雇员单独建立补充养老计划,允许雇员和雇主税前缴费参加补充养老计划,缴费标准可限制在雇员工资的 15%左右。
将社会养老保险与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加起来的总缴费率控制在 30% 左右,就可以与现行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大体相当。
在不增加缴费总负担的前提下,鼓励并促进雇主补充养老计划的大发展。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养老负担数字游戏的口舌之争,另一方面,可以实质性地均衡发展三支柱、多层次的国民养老保障体系。
同样,在医疗保障方面,除了进一步完善现行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外,我们还要大力鼓励雇主创设团体健康保险,为雇员提供补充医疗计划福利,这样也可以分散社会医疗保险的过大压力,并进一步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三支柱的医疗保障体系。因此,我们有必要适度降低现行社会医疗保险的缴费率,比方,将雇员雇主合计缴费率控制在 6%左右,以此留下空间,鼓励雇主自愿为其雇员提供福利优厚的团体健康保险计划。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保障总负担与国外相比,并非很高,更不是最高。相反,比社会保障总负担更重要、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处理好“三方负担”原则,有效均衡社会保障负担。在中国,处理好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大力发展由雇主提供的补充养老计划和补充医疗计划。此外,建立全民覆盖、全国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宏伟目标,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改革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