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贻湘军 “中兴”的阴面:曾国藩湘军与甚奇的“刺马案”
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巳时前后,即上午十点左右,南京城督署府衙西侧校场,两江总督马新贻刚刚循例检阅将士操练完毕。时值盛夏,本来酷热,刚好前一天细雨绵绵,放晴后天清气爽,故校场内外,观者如堵。
据当日身处南京的士人张文虎所记,马新贻在随从簇拥下离开校场时,忽一人从围观百姓中冲出拦路喊冤,马新贻“方接状,一人自后至刺刃,亲兵急救不及”。总督大人肋部要害被刺,“已不能言,气息如丝,刃处无血而口中反流血”。刺客张汶祥被当场捕获,但马新贻伤势过重,次日不治而亡。此即轰动晚清朝野的“刺马案”。
当时清廷相继平定绵延多年的太平天国与捻军反叛,对外与英法讲和,对内则努力“自强”,衰颓的国势有所振作,史称“同治中兴”。偏偏堂堂朝廷一品重臣、封疆大吏,居然于光天化日之下遇刺殒命,真如晴空惊雷一般,令百官惶恐,中枢震怒。同治帝师翁同龢更惊呼:“三百年未有之奇事也,嘻,衰征矣!”
飞来横祸
俗话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听闻马新贻的噩耗,他的两江总督前任曾国藩极为错愕。虽然他的直隶总督也不好当,正为久拖不决的天津教案焦头烂额,卧病在床,但仍对“刺马案”缘何发生感到不解:
“马帅中正和平,得之天性。莅任以来,一切用人行政,无一不允惬众望,似不致招人仇怨。忽尔罹此奇祸,殊出意料之外。怀贤念旧,感喟良深”。
正受命北上接替曾国藩直隶总督一职的李鸿章,与马新贻为进士同年(皆为道光二十七年即1847年进士),关系又深一层,得知马氏死于非命,亦慨叹“骇痛殊深”。马新贻赴任两江总督前,曾为浙江巡抚三年多,颇有政声,又升闽浙总督,时任浙江巡抚杨昌濬闻讯的第一反应是“穀帅(马新贻字穀山)之事真是天外飞来!”
外患未靖,内忧纷至,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不胜骇异”之余,随即下旨:“凶犯张汶详,胆敢伺隙行刺,戕杀总督重臣,实属罪大恶极。必应研讯确情,从严惩办,以申国法。”于是谕令江宁将军魁玉“督饬司道各官设法熬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情事,一一审出,据实奏闻”。数日后,清廷又委派漕运总督张之万会同魁玉查案,“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不得稍有含混”。
按理说,如此“高配置”阵容办案,案犯又当场抓获,案情理应很快水落石出。孰料魁、张二人审讯足足数月,竟因“供词尚属支离,自系因一时未得实供”,迟迟不能结案。后经朝廷中枢严斥,二人终于勉强拿出一个结论,大意是:
据称凶犯张汶详曾投“发逆”(指太平军),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杀伤其同党甚多,又因其妻罗氏被人拐跑,趁马新贻巡查边防到宁波时,拦路伸冤,未获审理,故心怀忿恨。后该犯私开小典当铺,适逢马新贻严令禁止,本利俱亏,追念前仇,杀机愈决。当日混进督署,突然行凶,经再三审讯,口供不变,并称别无主使之人,所述各项情形,尚属可信。
对此案情汇报,两宫太后无法满意,认定其间“尚有不实不尽”之处,倘以此结案,如何瞒得过南北众人之目,塞得住天下悠悠之口?
既然这两位主审官不行,那索性换一拨。于是朝廷下旨,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抵任后会同严讯,务得实情。又派刑部尚书郑敦谨兼程赶往南京协同审理。
各怀心事
前脚刚从天津教案漩涡迈出,后脚又被推入“刺马案”迷局当中,曾国藩叫苦不迭。接到朝廷调令时,他函告儿子曾纪泽,“余目疾不能服官,太后及枢廷皆早知之,不知何以复有此调?”“趁此尽可隐退,何必再到江南画蛇添足?”但上书请辞,迅即被中枢驳回。
曾氏的如意算盘,是先在天津、北京拖延些时日,待“刺马案”尘埃落定,再徐徐南下上任,谁知道朝廷一再催促其尽早动身。离京前夕,曾国藩两度入朝晋见,第一次是九月廿六日(10月20日),慈禧先与曾氏略谈津案情形,突然话锋一转,问道:“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曾对曰:“这事很奇。”慈禧又道:“马新贻办事很好。”曾答:“他办事和平、精细”。
慈禧与曾国藩此番对话,看似稀松平常,但彼此心中对“刺马案”的“甚奇”之处何在,恐怕想法大相径庭。
马新贻,山东菏泽人,1847年中进士后,从安徽太和县知县起步,二十年间,先后出任安徽按察使及布政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等职,1868年底接替曾国藩执掌两江。由其履历可知,马氏任职之地,皆为太平军、捻军来往纵横之处,亦是湘军、淮军之主战场。他以一介书生,又非湘淮嫡系,能够在战火之中稳步高升,最终接过功勋卓著的曾大帅的位子,说没有一点过硬的背景谁相信?深谙内情的曾国藩幕僚王闿运一语点出玄机:
“新贻起家牧令,虽在兵间,然无殊勋特绩。数年之间,致位督抚,竟代国藩总督两江重地,亦必有为之张目,隐以抗湘淮诸帅者”。
换言之,他与官文(满洲旗人,曾任湖广总督,曾国藩批评他“才具平庸”)、吴棠(以镇压捻军有功,先后任漕运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四川总督等)诸督抚一样,是朝廷中央用来节制湘淮势力的棋子。
马新贻赴任两江总督后,不辱使命,在裁撤湘军、镇压淮军索饷等事宜上不遗余力。他曾上奏折称,“浙省湘楚两军,马步水陆共计二万七千余人”“经臣挑留水陆五千余人,合之现升藩司杨昌濬所部楚军,共计一万四千余人。”大笔一挥,27000名湘军被裁掉近一半。因而在不少湘淮系大佬眼中,马新贻乃惹不起、招人烦的狠角色。而在十分忌惮湘淮军人坐大的朝廷看来,马新贻真是办事精干、雷厉风行的好帮手。
马氏猝亡,谁是最大受益者和幕后指使者呢?慈禧之“甚奇”相信就在这里。
曾国藩之“甚奇”则在于,湘淮军固然向来对马新贻打压异己的做法看不惯,但尚不至于采取如此极端手段来解决。湘淮系的曾、左、胡、李诸人,对于政敌,要么私下贿赂,与之结好,要么上折抵制或弹劾,令对方无法在本派系势力范围内久待。但此案显然涉及湘淮系利益,慈禧言语间似乎也起了疑心,为何又命公认的湘淮系领袖前去主审呢?
大约10天之后,曾国藩再度进宫,慈禧催问他:“几时起程赴江南?”曾答道:“臣明日进内随班行礼,礼毕后两日即起程前赴江南。”慈禧再次催促道:“江南的事要紧,望你早些儿去。”
又过了7天,曾国藩总算离京出发了。此行究竟是吉是凶,恐怕久经沙场的他,心里也一点没底。
浮言难息
一路走走停停,花了大半个月,曾国藩终于在1870年12月3日抵达南京。接过两江总督大印后,曾国藩终日走访旧雨新朋,却不急于审案。他在等待另一位主审官郑敦谨。时任刑部尚书郑敦谨是湖南长沙人,向以治事严苛著称,朝廷委以重任,自有望其一查究竟之意,曾国藩对此心知肚明。
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初二,曾国藩与郑敦谨联手提审凶手张汶祥,一连审了十四天,岂料进展甚微,并无突破。两人商量后,因“该犯一味狡展,毫无确供,将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只是在量刑上做文章,加重罪名,将张汶祥“比照谋反叛逆”处理。
既然一审再审,也查不出“幕后黑手”来,朝廷也只好认账,下旨说“既据郑敦谨等审讯确实。验明凶器,亦无药毒,并无另有主使之人。著即将张汶详凌迟处死,并于马新贻柩前摘心致祭,以彰国法而慰忠魂”。
“刺马案”办到这里,总算接近尾声,张汶祥最终定性为无固定职业、有私人怨恨、无后台主使、有犯罪前科的社会游民,一杀了之。但此案的重重疑云,真的自此消散了吗?还没有呢。
首先,在结案呈词上,马新贻亲信孙衣言拒绝画押;其次,在写给同僚的信中,曾国藩反复提及“刺马案”处理结果“尚恐不足惬众望而息浮言”;再次,结案不久,曾国藩悄悄派手下给郑敦谨送去路费白银千两,曾氏声称此“盖诸君之公意,非一人之私忱”,但郑坚决拒收。
最令人费解的是,数十年后,在民国初年修纂的《清史稿》中,史家为郑氏作盖棺之论时,特意留下“江宁之狱,论者多谓未尽得其情,敦谨未覆命,遽解官以去,其亦有所未慊於衷欤”一句话,也就是说,郑敦谨似有难言之隐。
仔细审读曾国藩有关“刺马案”的奏稿,可发现其已略泄天机。在上呈两宫太后的结案陈词中,曾氏提到张汶祥的一段经历:同治三年(1864年)年底,张与同乡时金彪见太平军大势已去,“乘便同时逃出,投提督黄少春营剃发,欲献计破贼报效,该营以无确保未收,酌给盘费回籍”。
黄少春乃曾国藩手下将领,张投靠黄,意味着进入湘军效力,而黄给张路费,将其遣散,则恐怕与当年攻陷天京,剿灭太平军后,曾国藩着手裁撤湘军的大背景有关。
兵匪一家
民国著名军事家蒋方震曾如此评价湘军:
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谚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则既成矣。虽然,书生之变相,则官僚也,民兵之变相,则土匪也,故湘军之末流,其上者变而为官僚,各督、抚是也,其下者变而为土匪,哥老会是也。
蒋氏此言,精炼地梳理出湘军攻下南京、大功告成后分化的脉络:书生蜕变为官僚,升到上层;民兵演变成会匪,流落底层。
当年曾国藩裁撤湘军,确是大势所趋,一来历经十数年作战,湘军已暮气沉沉、不可复用;二来为“避权势、保令名”,他亦须自剪羽翼、以示忠心;三来多数将士思乡情切、普遍厌战,命他们解甲归田顺乎人心。
故自同治三年五月攻下天京后,至同治五年年底,湘军先后裁撤遣散约30万人。但这批拿过屠刀、杀人如麻的兵勇,数目如此巨大,倘不能妥善安置,势必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大问题。张汶祥沦为无业流民铤而走险,不能不说是拜此所赐。
曾国藩恰恰在退伍湘军的善后安置上鲜有良策。第一,湘军军饷始终未得解决。自古“饷源足则士气盛,粮草缺则军心乱”,曾国藩虽主要以“忠义血性”治湘军,但亦以名利相诱导。曾国荃部攻入天京后,纵兵大肆抢掠,所得钱财不少,但湘军内部赏罚不一、欠饷过多的问题仍然严重。
湘军前身是地方团练,多依赖就地筹饷,加之将领克扣,士兵月饷普遍仅发五六成,有时竟一连数月无饷可发。如攻入天京前,曾国藩部属有8万多人,李续宜部下有2万人,“欠饷多者十五个月,少亦八九个月”。
至攻克天京后,湘军欠饷总额近500万两,尤其是鲍超的霆军,积欠军饷数目达120万两。裁军启动后,拖欠军饷仍未能如数补齐,遣散费又过于微薄,湘军中哗变事件不时爆发。
第二,湘军营中盛行“拜盟”之风。早在编练湘勇之始,曾国藩就“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寄希望于练勇“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
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这实际上是鼓励练勇歃血盟誓,结拜兄弟。“拜盟”之盛行,显然与湘军的组织结构息息相关,但也助长了湘军内部的江湖气,不利于军纪维护。
第三,湘军上层统领与基层士兵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左宗棠曾描述过军中士兵流传的一种说法:“诸将擢至总兵,则位尊金多,自为之念重。军中所以有‘顶红心黑’之谣也。”“顶红”,代指官阶高,“心黑”,比喻心肠毒。“顶红心黑”,就是说将领品级越高内心越坏,对士兵越是敲骨吸髓,横加盘剥。
“自陷于贼”
总而言之,积欠巨饷、“义气”横行、将士不睦,兵勇们一旦遭到裁撤,“江湖落魄,年复一年,糊口无资,栖身无地,其流而为匪者,情也,亦势也”,他们很容易为地下秘密社会组织所吸纳。太平天国战事结束后,由于唆诱大批退伍湘军入伙,哥老会发展迅猛,以四川、湖南最盛,湖北、江西次之,福建、广西、广东、江苏、浙江、安徽、山西、陕西、甘肃亦颇有势力,甚至蔓延到直隶、新疆、台湾地区。
同治一朝,由哥老会发动的较大规模叛乱就达60多起,以湖南最为严重。
湘军大佬们对此局面极为关注,左宗棠即认为哥老会“势之既成,遂若积重难返,黠桀者倡之,愚懦者附之,其患盖有不可胜言者”。赋闲在湘的曾国藩幕僚刘蓉目睹哥老会气势汹汹,预感湖南必定大乱,“要不出三数年间,不待智者而言矣”。屡次参与镇压哥老会的湘军大将刘坤一更是慨叹:“前则为国剿贼,今竟自陷于贼,将来为人所剿,良可痛心!”
对此情形,曾国藩自有清醒认识。早在咸丰八年(1858年),鉴于湘军中哥老会势力蔓延,曾出台营规:“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其态度不可谓不严厉。
然而随着湘军大规模裁撤,昔日子弟兵涌回湖南加盟哥老会,若再采用雷霆手段,既不利于乡梓安定,又会大失人心,曾国藩不得不转变策略,“但问其有罪无罪,不问其是会非会”且采用“就案问案”的方式,只问具体案情,不问是否入会,尽量缩小打击面。他期望借此达到“会中之千万好人安心而可保无事,会中数千恶人势孤而不能惑众”之效。
不过,退役将士的待遇与出路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任何宽严相济、刚柔并用的权宜之计俱是徒劳。同治八年二月,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哥老会首领赖荣甫率六七百人攻打县城,并欲“直下湘潭”,侵犯省城长沙;同治九年五月,另一哥老会头目邱志儒等约期先抢浏阳县城,烧署劫狱,再进犯长沙;同治十年,湖南哥老会再度大规模集结,先后攻破益阳、龙阳县城。
面对燎原之势,曾国藩惟有慨叹:“湘省年年发难,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纵使十次全胜而设有一次迁徙,则桑梓之患不堪设想,殊深焦虑。”
就在哥老会连年作乱之际,曾为湘军效力、又遭强行遣散、背负会党嫌疑的张汶祥,一刀结果了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性命,于公于私,曾国藩肯定想方设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旦此事真相曝光,不仅牵连数十万退伍湘军,对于仍身居军政要职的湘军大佬们,也不是什么好事,至于地方政局震动,君臣互相猜疑,那就更不是年近花甲、精力日衰的曾国藩所愿见到的了。
故此,曾国藩只好能掩一时算一时,且瞒一日就一日。这大概就是一生处事从不含糊的他,不得不含糊处理“刺马案”的重要原因。郑敦谨同为湖南人,想必亦深深体会到曾国藩的进退两难,于乡于国于君于民,他唯有与老乡联手保持沉默。
曾国藩当年一手培育的湘军,挽狂澜于既倒,极力支撑起清廷“同治中兴”的大局,但此后数十年的各种暴动、民变、教案、起义乃至革命中,以老湘军为骨干的哥老会的身影时时可见,竟然转化为覆灭清廷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之一,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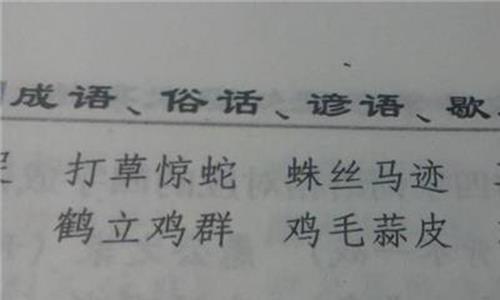

![两江总督马新贻之死 [史话]清末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疑案(上)!](https://pic.bilezu.com/upload/b/6b/b6b2528febe94eb652de806d36d5dd5a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