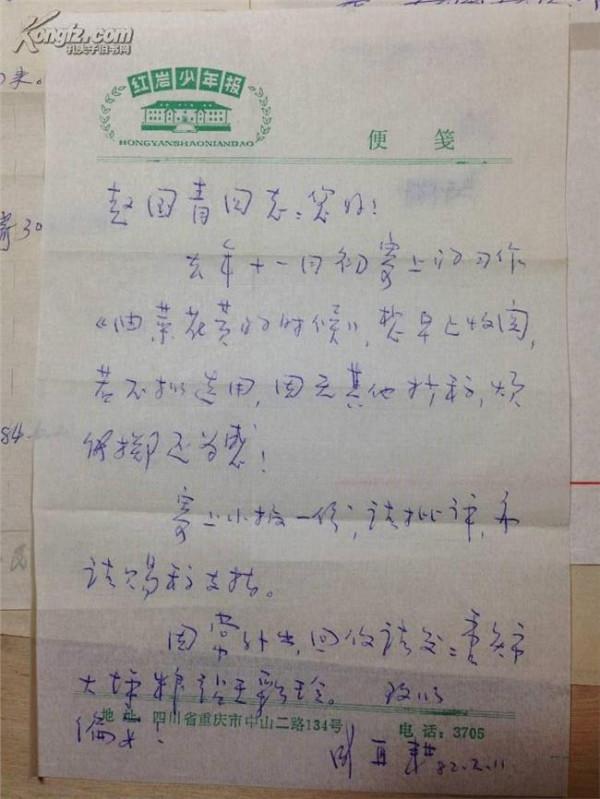孙甘露信使之函 小说的挽歌——论孙甘露的《信使之函》
小说的挽歌——论孙甘露的《信使之函》 ----杂拌之二 (2008-05-05 12:17:00) 标签:杂谈 我以一种古代的姿态迈入你的庭院 我被无数时代朗诵着来到你的桌边 抚摩你的双眼 ——孙甘露 孙甘露的《信使之函》是当代中国小说中的最极端的作品。
被人称作是“一次绝对的写作,是语词举行的盛大舞会,一次语词或写作的自恋。象是一次盲目的冒险或永无归期的流放…”。阅读孙甘露的这篇小说,我时常陶醉于作品中华美的句子,流畅的叙述,明丽的情景;同时,又被那神出鬼没的人物,似是而非的哲理弄的莫名其妙。
然而,在阅读结束的时候,在心灵深处,却有一种畅饮过后的迷醉,仿佛在现实与梦境之间,我们被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那么,那些貌似祈祷、忏悔、梦呓与胡说的文字究竟还是不是小说呢?我想从叙事的内容、叙述的形式,语言的风格三个角度来分析《信使之函》这篇小说的文体特征。 一、写作的梦境 《信使之函》是孙甘露的一次“梦游”,他自己在谈到写作时也提到“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我热切地倾向于一种含糊其词的叙述了。
我在其中生活了很久的这个城市已使我越来越感到陌生。它的曲折回旋的街道具有冷酷而令人发憷的迷宫的风格。它的雨夜的情怀和晴日的景致纷纷拥入我乱梦般的睡思。
在我的同时代人的匆忙的奔波中我已由一个嗜梦者变成了梦中人。我的世俗的情感被我的叙述谨慎的予以拒绝,我无可挽回地被我的坦率的梦想所葬送。”孙甘露以《信使之函》创造了一个远离世俗的,并且否定生活世界常规秩序的语言幻想世界。
他始终在存在的“临界”地带眺望着实在的生活。所谓临界感觉,是指叙述人或故事中的角色处于语言与客观世界、语言与意义的双重辨析的情境,叙述始终处于真实与幻想的临界状态。
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完全是语词的诗性碰撞引发的连锁反应组合而成,他的作品自始至终拒绝进入实在世界,他用散乱无序的语词制造出一个非秩序化的支离破碎的存在状态。《信使之函》中的人物如“致意者、六指人、温柔的睡莲、僧侣等完全是一群来去匆匆支离破碎得人物,他们生活在一个漂流不定,没有真实含义的虚幻世界里,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
他们往往只保留瞬间的情态,而这瞬间的情态又总是雕塑般化为了永恒的印记。
《信使之函》中的世界与人物占据着“临界时空”,穿梭在真实与幻觉的边缘,使得存在变的无边无际,使得写作者乐而忘返,然而,这全是一个梦境,一个幻想的空间,孙甘露从没有打算把我们带入任何故事,认识任何人物,他只是用语言搭建起一座迷宫,任凭语言与思绪在其中漂流,至于你我就看会不会做梦了。
二、叙述的天堂 《信使之函》全篇充满了无所顾忌的诗意描写和放任自流的奇谈怪论,孙甘露把写作彻底改变为个人的语调游戏,解放的语言在幻想的世界自由漂流。
他最大限度地滥用了诗性和哲理凝练组合成的叙述语式。例如:在五十多个“信是…”的判断句里,他把一个事物的可能性推倒了极端,它被无限制的运用,“信”变的无所不在、无处不在。
无限制的重复,不仅表明存在物的不可限定,而且揭示了存在总是在追寻中迷失。象“信是纯朴情怀的伤感的流亡”这样的句子更是不依照意义逻辑的语法程序,而是语词相互碰撞的自然而自由的结果。孙甘露的叙述因为没有明确的主题而消除了叙述结构,只剩下叙述话语在本文里自由穿梭往来,而瞬间的诗性情状 哲理性的感悟补充使他的叙述话语在诗性描摹了瞬间的状态时,语意获得了永恒的哲理感悟;当哲理穿透了瞬间的存在时,诗性的情状就获得了永恒的定格。
这种叙述文体最大限度地拆除了小说与诗和哲学随想录的界线。而追求启示录式的思想,不厌其烦的打破常规语意,把最不协调的字词和语句拼和在一起,也的确带来了创造与阅读一种怪诞的快感。
三、抒情地放纵 在孙甘露的小说《我是少年酒坛子》中,有一段著名的独白“我为何至今依然漂泊无定,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段往事。今夜我诗情洋溢,这不好。这我知道。毫无办法,诗情洋溢”。所谓“诗情”不过就是内心压抑不住的表达欲望。
为了满足这种表达欲望,于是便常常为了描写而描写,热衷于捕捉纯粹的语言感觉,在《信使之函》中,象“送葬的行列过去了,街上空无一人。从建筑物隙缝间吹来的劲风打着旋在空荡荡的街道间与枯枝败叶寻欢作乐,它们在墙根和道口带动起行人抛弃的废纸或果皮,迅疾地转几个舞步式的圆圈,便弃如敝履似的舍之而去,再与沟沿或门角那些油腻的蹲伏者亲热一番,即刻钻入附近的过道或回廊无影无踪。
”这类描写性组织同时也是抒情性句式它们在叙事中随意出现制造出情境氛围和强烈的抒情风格。
可以说孙甘露的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纯粹的抒情,故事情节与细节均变的无关紧要。另外,孙甘露的抒情风格还体现在语词的放任自流相互碰撞之下产生的“反讽意味”。
孙甘露无所顾忌的诗性祈祷是语言全面错位的堆砌,它包含了一种对传统语法的恶意模仿,也是对人们常规想象关系的善意破坏。《信使之函》通篇充满了喋喋不休的描写,夸夸其谈的言论,似是而非的抒情很多句子优美典雅宛如汉魏六朝的骈句,而描述的对象却是生活的全部荒诞性。
语词的游戏与生活的游戏完全重合,抒情的叙事仅仅是满足了戏谑的快感。而将反讽植入抒情性叙事中,也是孙甘露作品的基本文体特征之一。
孙甘露以临界的叙述角度,言语的自由漂流,抒情的善意反讽,对小说传统的经典权威文体加以别具一格的颠覆,拆除了小说写作的各种戒律与规范,他凭借虚张声势的语词游戏,温文尔雅的抒情风格为小说的传统唱出一只华丽的挽歌。不过,挽歌之后也许会是一片更加璀璨的的朝霞。 网文


















![>[周玗希]周玗函周玗希打架事件](https://pic.bilezu.com/upload/1/a3/1a37ed548ecf6d5f797c175ee69cfd64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