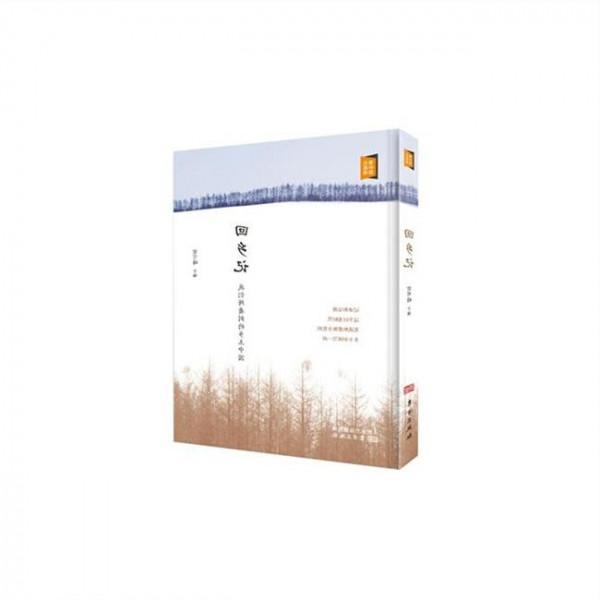汪晖情人 秦晖、温铁军、汪晖三人谈(一)
【编者按】 这是2003年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大事,代表当时(到目前仍是)中国知识界左、中、右三派的代表人物——汪晖、温铁军、秦晖三位就中国当下的改革方向与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对话与争论。起初,这个活动的动机有一个超越党派性的诉求,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也许算是达到了,因为三人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域基本达成了共识,但这些共识还没有多到足以构成秦晖所谓的“共同的底线”的程度,其实在相当多的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分歧。
这个对话在当时比较准确地折射了思想界的状况和困境,也昭示了当时中国改革的处境,即使到今天仍然具有不小的现实意义,很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清晰化、明朗化的问题结论仍然是少数的,这些问题的歧路正是今天讨论的重要启示。
这里选取的是秦晖整理的纪录版本,此外还有温铁军的版本,在一些部分有不可忽视的区别,但大体一致。在这个版本中,秦晖加入了不少当时谈话时没有说的补充性内容,使自己的逻辑性更通畅,而其他两位的则相应显得简单粗糙了一些。重发这个对话,对于思考和讨论今天的一些关键问题希望能有所助益。因文章太长,所以将分为4部分发出来。
—— 王大爷
【整理者按】这是秦晖、温铁军、汪晖三人的一个对话。《天涯》与《中国改革》杂志曾先后发表过未经笔者审阅及认可的两个删改版,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发表未删改的文本以正视听。在这个由笔者整理的版本中,本人的谈话部分有相当篇幅的进一步补充,同时也保留了其它两位对话者的全部对话内容(包括两位事后整理增补的内容及前后文的顺序、体例,乃至两位认为应当放进来的他人言论,均一字不删,以对历史负责),但他们的对话内容在文中的性质属于引文,不影响笔者自负文责、自享文权。
——秦晖
翻译(“翻译”指该大会上外国学者[录音中无法分辨具体是谁]的发言[同声传译]——整理者注):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跟大的国家相比,东欧国家相对比较小。如果跟俄罗斯比,俄罗斯寿命指数下降了。
现在他们男性的平均寿命比印度男性的平均寿命低。
秦晖:俄罗斯转轨中的问题我们都承认。可是在前苏联东欧范围内,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采取了俄罗斯转轨的方式,比如乌克兰、白俄罗斯就没有采用。
但是他们现在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去。所以我们当然也应该反思俄罗斯转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如果要和东欧作比较的话,我们要考虑东欧内部和中国内部的不同,然后才可以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俄罗斯转轨过程中不公平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这种不公正也是和它的政治民主化不如波捷匈有关的。
关于俄罗斯如今存在许多混乱的解释。由于俄罗斯经济搞得不好,我们经济学界的“左”“右”双方都拿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说事。
“左派”说俄国人一分了私有化证券就拿去换酒喝,有人乘机收购大量证券,于是便霸占了国有资产成为寡头,这多不公平!可见这家千万分不得,自由主义罪该万死,还是让大家长管着好。
“右派”则说俄国人就是穷讲究什幺公平,要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结果股权极度分散,造成公司治理不好效率低下,要是把产权交给经理就好了!可见分家就是要依靠强者,平民立场罪莫大焉。
其实,金雁的研究证明:当时叶利钦政府实际上是借通货膨胀和资产重新定价之机赖掉了原先许诺的资产分配。
主要的国有资产根本就没有 “分”, “私有化证券”只能换一些垃圾股,大量收购这些证券的人后来基本上都破产了,根本没有变成“寡头”。
后来的寡头实际上是在1994年俄国私有化“改分为卖”之后,一些权贵通过“内部人交易”(这恰恰正是中国现在流行的做法)把国家耍赖没有拿出来分给老百姓的那些资产攫为己有的结果,他们根本不是通过收集私有化证券发迹的。
也就是说,如果当时俄国像捷克那样认真地通过“证券私有化”搞了资产的公平分配,后来的经济发展肯定是另一个样子。
而且,主张把资产公平分配给人民也不能说仅仅是“自由主义”的立场。
美国著名的左派教授、马克思主义者罗默论证过的“证券社会主义”不也和捷克的做法很类似吗?这也就是我讲的“共同的底线”吧。当然底线实现以后还是会有“左右”之别:罗默的证券资产及身而止,不能传之后世。
捷克的证券资产则可以继承——但那种区别是一代人以后的事了。
当然后来的进程表明捷克式的“公平分配”也有它的缺陷,我们对此作过研究,在肯定捷克式的“起点平等”的同时也指出其“投资私有化基金(IPF)”的后来运作有问题。
国内一些拥护现行私有化方式的经济学家常常批评我主张“只分不卖”,其实我从未有过这种说法。我只是在批评某些人以俄罗斯 “平分国有资产导致经济失败”为借口主张直接把公共资产私相授受时,澄清过俄国“证券私有化”的真相,指出俄国寡头经济之弊恰恰是由于“内部人交易”而并没有真正实行资产公平分配的事实。
我们认为在民主参与、公共监督的基础上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私有化问题并不是什幺乌托邦,无论是“起点平等、公平竞争”式的分配,还是公平出售国有资产并用所得充实社会保障与公益福利基金,都是可行的。
相反,如果是专制条件下权贵们暗箱操作,无论偷“卖”还是私“分” 都意味着对公众的剥夺。
即使绝对公平不可能,我们至少应当力争尽可能的公平。
总之,俄罗斯的问题根本不是“分”了以后由于“证券自由买卖”造成了寡头,而是政府口头说“分”实际赖了账,然后把赖着不“分”的资产私相授受给了“内部人”。
作为中国人,恐怕很难用这样一个例子来反证我们现在没有问题。因为仅就一些不公平的经济指数来看,比如基尼系数,中国现在就不低于俄罗斯,肯定远远高于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捷克、匈牙利。
翻译:50年代中期,中国集体化的道路似乎比东欧、苏联进行得顺利,没有遭到很多来自农民的抗争。这是否要考虑在中国社会中农民的其它一些因素。
汪晖:1988年到1989年前后,社会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中国市场制度的一些基本要素形成,第一个是价格改革,当时在价格改革过程当中首先形成了所谓商品价格双轨制度,导致了权力市场化,包括寻租行为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在1988年曾经推动过两次价格闯关,这两次闯关都因为引起通货膨胀和社会不稳定,而无法完成。1989年发生了社会危机,很多人把1989年到1992年这3年的调整看成是一个对这之前的市场改革的反动时期。
1989年9月国家又重新开始了价格改革,利率,汇率,整个的价格改革就是从这个时期重新启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时期对原来市场化的整顿完成了什幺内容。
第一是货币政策成为主要调控手段。第二个是大幅度调整外汇牌价,促进汇率的统一,扩大出口,形成对外贸易竞争以及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也就是外贸体制整个改革了,双轨制的差距也缩小了,上海浦东开始开放了,各地的开发区也出现了。
从1989年到1992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幺短的时期里所发生的市场扩张和国家控制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个互动关系或悖论关系可以概括为:一方面,没有国家政策的调节、法律体系和政治保障,市场体系的扩张、培育和发展几乎不能想象,没有这些就不存在市场。
另一方面,市场体制对国家的依赖,同时也是权力和市场进行交易的前提。
原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和市场之间形成奇特的互动关系,我觉得不能完全看作是对立的关系,市场的形成对国家是有所依赖的。所以,现实市场形成的过程事实上是依赖反市场的力量,而国家也相当大程度地依赖市场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例如,1989年以后国家克服合法性危机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市场扩张来完成的。
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关于国家退出的理论,既不能解释改革以来国家的积极政策比如价格政策,及产业政策下获得的成就,也不能解释在国有资产大规模私有化过程当中发生的严重的权钱交易和社会分化。
假定说在自由市场和国家这个二元选择当中,市场形成就一定要国家退出的话,那幺我们就既不能解释中国改革过程中市场化的成就,也不能解释市场扩张当中形成的腐败和其它问题。
第二点我想讲一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能不能构成分析问题的框架。首先在1989年到1992年这个所谓三年调整时期,我们在社会氛围和政治上看到的好象是完全反动的时期,完全旧的形态、旧的手段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重新出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是因为旧的体制丧失了它的合理性,新的市场扩张才能够被看成是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
虽然政治的结构没有改变,但是它的意识形态几乎丧失了基本的说服力。比如在中美之间 WTO 协议形成的过程整个社会和知识分子是不知道的,但整个社会都在为之欢呼,很多人认为WTO有助于中国进入一个民主的社会,但是进入WTO的过程是没有什幺民主可谈的。
认为为未来欢呼的惟一理由就是对过去的拒绝。这也就是说,现实秩序和过程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对旧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拒绝的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原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析方式在这个语境中是很难使用的。
第三个问题我想谈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是怎幺被替换的。在80年代社会思潮和80年代末社会运动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推动中国民主化过程的是社会力量。
在90年代以后,社会这个概念几乎完全被市场这个概念替换了。社会的变革,法律体系的转换,新的法律体系大规模的出台,推动这个过程的不是社会,而是市场规则。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本身的含义就发生了变化。
因为国家变成了维护市场机制的一个体系,一个按照新的规则来重塑法律的主要执行者了。1989年以后,程序民主、形式主义的民主等等观念,把大众民主概念与程序民主完全对立起来,并且把社会运动及其实际的变革诉求全部排斥掉,说这是激进主义或民粹主义。
知识界取向的变化是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左右两派分歧的要害并不是要不要程序性的民主,而在于什幺才是民主的真正的动力。把无论什幺样的保护性运动都指责为民粹主义,或者是中国传统的流民文化等等,只是空洞地提程序性民主,那就等于放弃对于民主动力的追寻来推动民主进程。
这个进程再好也没有可能自发地实现。90年代中国知识界进行过对市民社会与中产阶级的讨论,认为这个新阶级可以作为未来社会的基础。
我们不妨以波兰与中国作一个比较。波兰在80年代社会运动过程中,团结工会在宪章中把工人阶级看成是原来社会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基础。90年代中国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与民主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讨论的核心都是企业、老板、市场。
当瓦文萨等代表的团结工会向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转化之后,他们也就不能代表波兰的民主力量了。看一看今天波兰的政治格局,我们还能看到他们的有效力量吗?
在私有化过程中,至少应区分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温州模式,是从家庭、从民间发展起来的小市场。
是通过低额利润,制造衣服、鞋子,植根于社会根部慢慢发展起来的私有化。
还有一种,实际是非国有化。在非国有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国有资产被非法的和合法的转换为私有财产。这个过程是今天腐败、犯罪和社会不公的最重要的根源。以广东汕头来看,90年代经济一度发展得很快,主要的原因是走私石油。
近几年打击走私以后,汕头发展就垮了。沿海地区走私石油、钢铁等工业原料的过程与国有企业大规模下岗、破产的过程是并行的。他们破产的过程是更为宏观的条件决定的。为什幺70年代到80年代前期农村改革取得了成功,但是到80年代末问题不断出现,这并不完全是一个所有制问题,还要放在一个更大的经济环境中来看,比如城乡互动等等。
我认为应该对这个问题做三个区分。第一,应该在自由竞争或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和现代市场经济形成和运营的历史过程之间做个区分。
第二个必须在新自由主义市场意识形态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秩序和经济政策之间做出区分。新自由主义要求国家彻底退出,但它的市场秩序和经济政策经常还要依赖国家。
它们是密切的伙伴。
第三,必须在市场的范畴和社会的范畴之间做出区分。
按照第一个区分,市场社会和它的规则的形成就在国家干预、制度创制、垄断关系、社会情况和历史事件的交错关系中形成和运行着,自由竞争仅仅构成了非常局部的条件。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不能就等同于否定市场机制。
按照第二个区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国家实行放任自流的政策,也就是放弃国家对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责任,放弃国家调节市场活动的经济手段,现在很多危机比如国有企业、农业危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实际上是政策安排的结果。
放弃责任本身实际上是依赖于特定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利益关系形成政策的结果。
按照第三个区分,我觉得市场的规约不能等同于社会的规约,社会民主机制的形成不能等同于完善市场的过程。
我们做这些区分的目的是要形成一个概念:在一个社会里,除了国家之外,社会到底应该作些什幺呢?社会需要形成它的一些变革的取向,用这个来推动、逼迫国家来做一些政策安排,朝有利于民主和社会保障的方向发展。
汪:如果只是习惯于认为非白即黑就是逻辑清晰的话,在历史分析中就必定会出现混乱。我的基本观点是,在所谓的市场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国家的角色是没有办法取消的,无论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
因此不应是简单的取消国家,或者让它自己退出,而是要改变,要通过什幺样的社会力量,让它朝着有利于社会的方向来做。这样,民主的必要性就显示出来了。
如果按照让国家退出的模式,那幺民主的必要性也不存在了。民主的实践是以社会的自我管理为取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取消政治结构。
(有人插话:我认为有个基本论点:国家是任何时候都不能避免的,关键是怎样表现国家职能,是制造市场还是产生剥削,还是在其它方面显示作用。
)
翻译:汪晖说在中国,非国有化过程是造成腐败的主要的原因,他认为新自由主义说的只有通过私有化,把国家资产都私有化了,国家就不存在了,腐败也就不存在了……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
温:我认为应该先把概念搞清楚,我们刚才谈到国家退出与否的时候,引用的是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的概念,而在中国,政府不是一个西方式的政府,它是一个经济主体。
它在经济领域中不存在退出的问题。
汪:对。正因为如此,问题才不能简化为国家是否推出,而是通过何种力量、以何种方式进行民主化改革的问题,即国家职能的改变的问题。
安德森先生提到温州模式和非国有化过程中的腐败,是不是温州就没有腐败?当然不是,实际上温州模式实现的过程,早些年被批评得非常厉害。
而它的形成过程依赖的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民营经济,是私有的,不是国家的。我刚才说到汕头,走私的多是地方国营公司。中国国营的外贸公司中出问题的非常之多。
翻译:你讲到私有化的问题,没有谈到私有化的利益问题。
以阿根廷为例,大的财团想得到私有化的利益,最后政府完全被某些大财团所控制。直到面临经济的崩溃,这些财团又需要政府的救助,我想说的是:私有化就会有这样噩梦般的事情出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