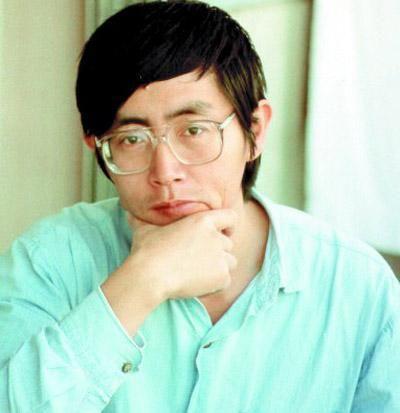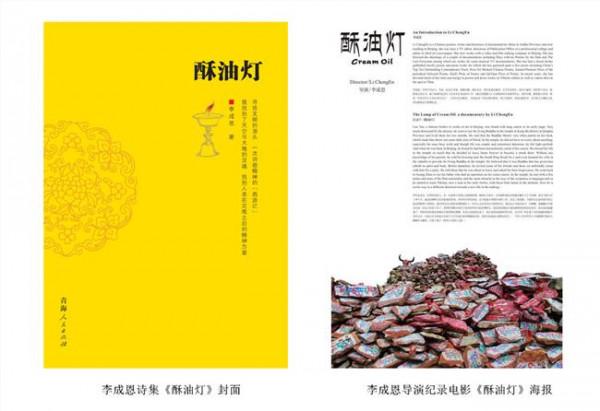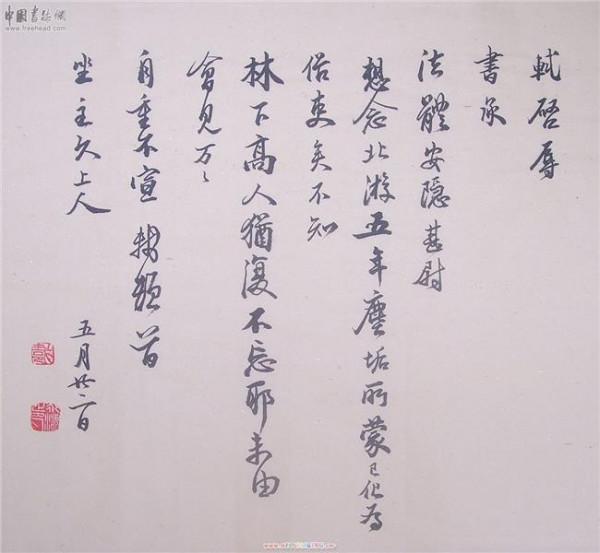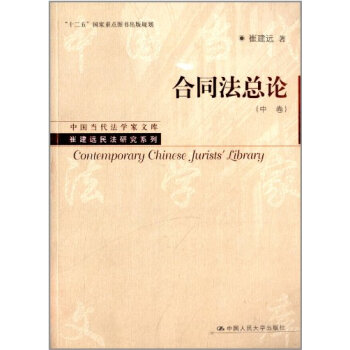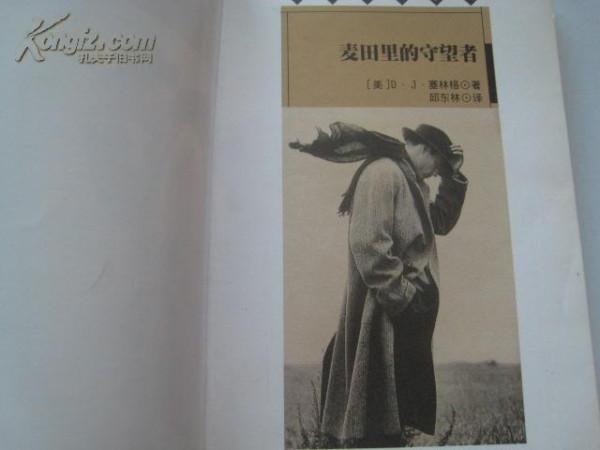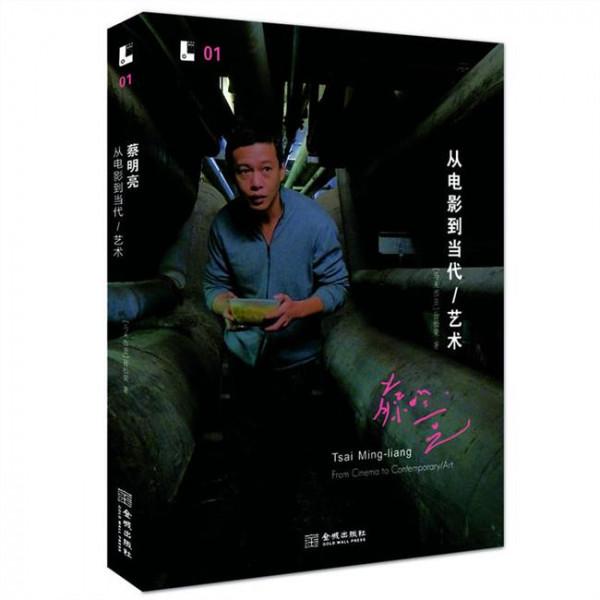潘洗尘代表作 中国当代诗人系列访谈:潘洗尘
提问:王西平,1980年生,诗人,记者,《核诗歌小杂志》主编。
回答:潘洗尘,1963年生,诗人,现经营一家公司,主编几种诗歌刊物。
一、 记忆
问:您出生于一个叫恰博旗的小村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村子?它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哪些变化?
答:我的出生地恰博旗村坐落在松花江边,距县城中心不足两公里。全村拥有七百户人家三千多人口,其中潘姓家族是村子里最大的一个家族。虽说我的家住在东北的松花江边,但那里并没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所以直到1982年我离开家乡去省城读书时,仍有很多乡亲们还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如果说到变化,那唯一可以让我直接感受到的变化就只有当年和我一般大小的少年伙伴们的身形,如今都早已渐呈老态,再就是家中日历盘上那总是一闪而过的时间了。
问:内蒙古有很多的地方叫什么什么旗,以前蒙古的每个部落都有一面旗帜代表这个部落的象征。而现在内蒙古的旗,是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县。那么恰博旗,是一面什么“旗”,有说法吗?
答:我曾查过当地的县志,这里过去确有大量的蒙古族人居住,现在也还设有蒙族自治乡。但对于我的出生地恰博旗村,县志里没有任何记载,村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得清她的来龙去脉。
问:我记得您有一组诗,专门描写恰博旗人物的。比如在《我的小学校长陈立本》这首诗中,你说“陈立本是我的小学校长”,同时还提到了陈立本的儿子陈小三,您的舅舅王清录,以及乔乔、张连祥等人。这些乡村人物构成了关于“恰博旗”的主要记忆。请讲讲有关他们的故事吧。
答:在我的组诗《恰博旗人物志》里,陈立本和乔乔我都使用了化名,前者曾给我的少年时代留下过许多心理阴影,但毕竟早已时过境迁,这个人物之所以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会出现在我的诗歌里,主要是为了检验一下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自己对旧有事物的认识有了那些改变,以及心性上有了哪些变化;而乔乔则是我从那个始终“冥顽不化”的小村里发现的唯一的“亮点”。
在恰博旗,乔乔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道德观的代表,不仅从此为那个始终固步自封死水一潭的小村注入了多元的元素,也为我更深入地感受和感知这个北方小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场域;而王清录是我死去的舅舅,更是我少年时代的精神原乡。
他不仅在文学上启蒙了我,更教会了我做人始终应该保有的两种最基本的品格:“宽容”和“坚强”。
另外,他还是我的朋友,这在那样一个精神和物质都极度贫瘠但传统的辈分观念却森严壁垒的地方,恐怕就是我所接受到的最早的“民主”与“平等”意识了;至于张连祥,则是我在《恰博旗人物志》里写到次数最多的一个人物,前后一共有四首诗吧。
他和乔乔一样,代表着恰博旗的现在。而一个让人充满希望的乔乔和一个令人忍不住绝望的张连祥,不仅构成着一个完整的现实的恰博旗,也正好暗合了我全部的生命观和未来观。
问:“父亲没读过一天书,不满十三岁/便靠一支小小的牧羊鞭/独自赡养我四体不勤的祖父/和一生都神经错乱的祖母”。迄今为止,您从“目不识丁”的父亲那里得到了什么?如果有两个不同的“潘洗尘”,即诗人潘洗尘和商人潘洗尘,要求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您希望的答案是什么?
答:作为诗人的潘洗尘,我从父亲那里承袭的是一种叫“宽厚”的品格,以及对一切“手艺”的尊重感与好奇感(父亲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铁匠、木匠和厨师);而作为商人的潘洗尘,则从父亲那里获得了一种叫“勤劳”和“坚韧”的精神。
问:1970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11月11日晚上,江青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在海南岛,天气暖融融,到处鲜花盛开,遍地是成熟了的又甜又脆的无籽大西瓜,她吃了一块又一块。1970年冬季,甘肃陇西县枪毙一个裁缝,好像叫“小杨师”。
1970年冬天,周恩来在听取秦山核电站工程汇报的中央专委会议上谈中国发展载人飞船计划。1970年,散文家周涛写下了题为《冬天里遇到的童话》的一首诗……那么1970年的冬天,当青年人“上山下乡”的时候,潘洗尘,您在干什么?
答:真的是很巧,大约是在2005年前后吧,我曾写过一首《遥想1970年的冬天》,现录于此,正好作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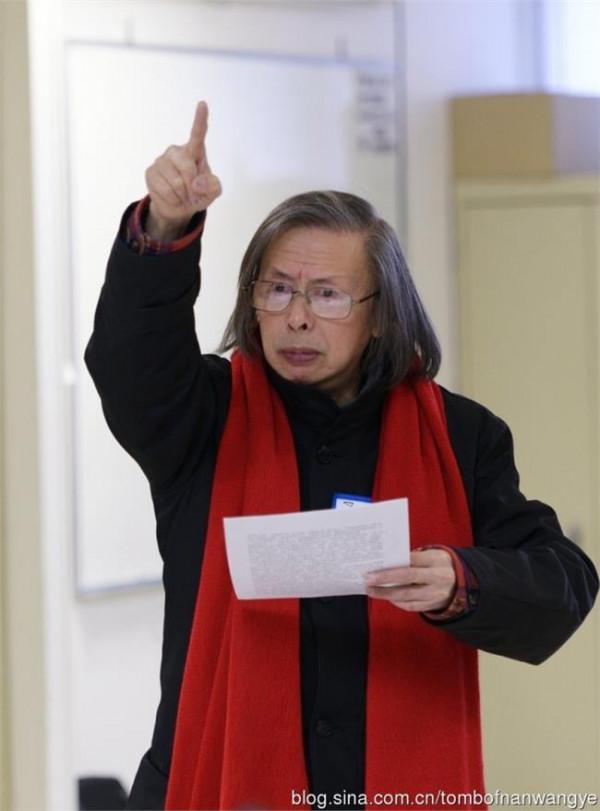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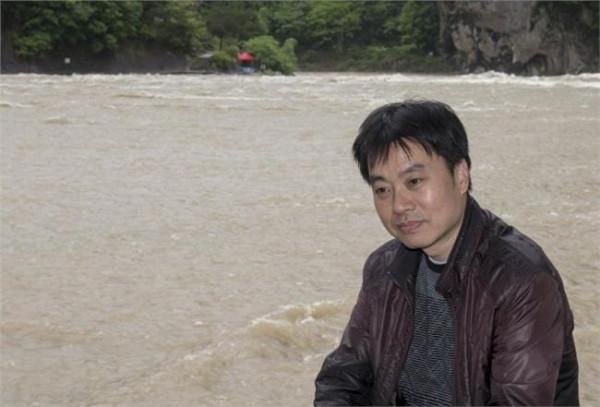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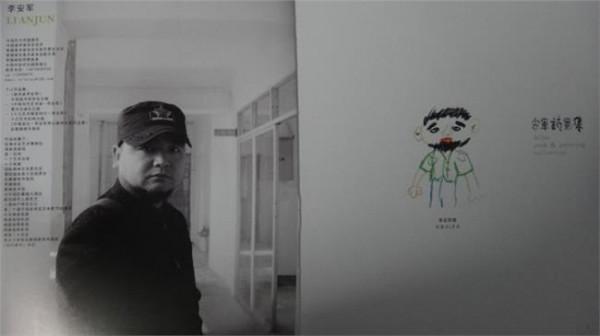





![伊拉克流沙河 流沙河[中国当代诗人]](https://pic.bilezu.com/upload/b/a3/ba3a0993f72dc6b182142047fc07e0ad_thum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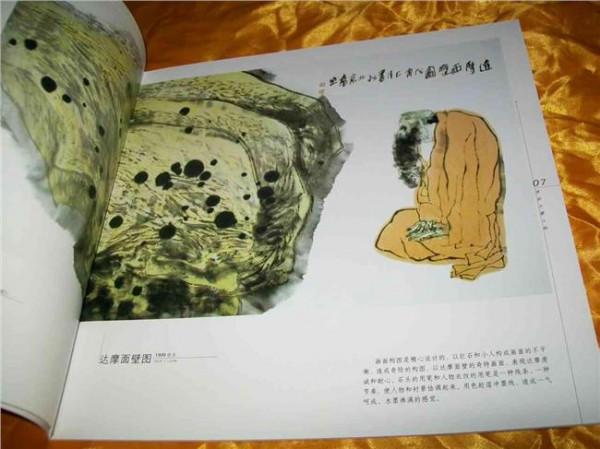
![王向明北京大学 [人民网]走进北京高校 感受思政魅力系列访谈—中国人民大学](https://pic.bilezu.com/upload/9/33/933379787715e72d36ff51c249d9ea9c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