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卡拉ok潘知常 潘知常:纸上的卡拉OK
对于目前大行其道的"小女人散文",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纸上的卡拉OK,或者用笔唱的流行歌曲。在我看来,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小女人散文"的价值类似话梅、瓜子、口香糖,不能充饥,也无营养,但是却可以消磨时间。
它的出现,迎合了当代美学的对传统美学的意义、深度的消解。传统的散文往往是写一种"大丈夫"的心态,抒发的是国家、民族的豪情,例如杨朔刘白羽的散文。现在却转向了写一种"小女人"的心态,是以平面的姿态对传统散文中的深度加以消解,去对普通人的生活加以关照与还原。
因此,它有其存在的意义。然而,目前无论是在"小女人散文"的撰写者还是评论者那里,都出现了一种对它人为地加以抬高并且避而不谈它的根本缺撼的倾向,这则是"小女人散文"的一种误区。
事实上,它的根本缺撼是极为明显的。从作品本身而言,所谓"小女人散文"无非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如果说过去的文学作品过于强调深度,意义,那么现在"小女人散文"就干脆放弃了深度、价值、意义。
因此它披挂的语言外衣再精制、漂亮,也不过是满篇漂亮的废话(它与林语堂的生活散文也不同。在后者,日常生活只是能指,对于现代性的关注却是所指)。它的立足点从过去对意义的消费转向对语言的单纯消费,变成为语言而语言,更是一种公开的媚俗。
而它所导致的最终结果,也正是使散文丧失了应有的美学品格,并且流于平庸、无聊。而从作者的角度讲,所谓"小女人散文"的出现则是经济发展、繁荣之后的特定现象。
经济的发展、繁荣造就了一批"金屋藏娇"的"太太"们。这些"太太"们往往是经济上没有负担,也不再需要面对社会上日益严峻的竞争,并且开始退回家庭。然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她们又会产生一种特有的少女心态,我把她称之为"少妇聊发少女狂"。
与琼瑶席慕容三毛一样,她们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需要思考了,就非常地怀旧、非常地多情。于是开始百无聊赖地用一种少女的情态在社会中编造诗意以期丰富自己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她们代表了大陆的某个写作阶层。
她们以笔去寻找生活中的趣味,这种寻找具有浓烈的刻意色彩。这类作品从表面上看好象要是回到真实,并与传统美学中的虚伪的东西进行决裂。但是生活在本质上却是气象万千的。我们不禁要问:所谓生活的真实性本身就包含着艰苦卓绝的一面,比如困惑、忧患、焦虑。
这些难道就不真实了吗.将复杂的人生中痛苦失败的一面化解掉,而单纯地描写所谓平静琐碎的生活感受,其结果,就不能不充斥着琐屑的小女人心绪。
据说在上海竟然有大学教授以能背诵《美人肩与美人背〉这类散文为荣,我对这位大学教授的美学趣味只能表示怀疑。因为散文中涉及的美学知识相当肤浅简单。如果如此这般就是写出了生活的真实、写出了美,我认为实在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自欺与欺人。
实际上,只要随便翻阅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处处浸透着的一种小女人的非常庸俗的自鸣得意。有评论家赞颂在这些散文里"树很直,石头很光洁",似乎唯独她们才写出了真正的树和真正的石头,但是树、石头多有不同。
比如有些石头就相当媚俗,只供掌中把玩,但石头中也不乏在狂风巨浪中傲然挺立的礁石;公园里的树当然很悦目,但泰山顶上的十八棵青松,不是更为令人敬仰吗?最后,就读者来说,则只是一种小市民趣味的渲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对读者中不健康心理的迎合,有评论家说这些"小女人散文"是对市民趣味的迎合,这并不准确。
市民趣味代表的是一个整体,所谓"小女人散文"只是对其中的小市民的趣味的迎合。
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小女人散文"在广州发源地并不受欢迎,但是在上海却大受欢迎。上海所存在的小市民趣味是有目共睹的。这主要体现在缺乏坦荡的心胸,善打小算盘,自私自利,对生活中无聊的东西津津乐道,对不劳而获充满幻想和迷恋。
这无疑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趣味。与此相应,"小女人散文"主要表现的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趣味。总之,所谓"小女人散文"混淆了平常与平庸的界限。散文固然可以从崇高转向平常,但却绝不能从崇高转向平庸。
在这里,平庸与平常之间不能等同起来。平庸是对日常生活的不全面的理解,而真正的生活则是平常的。这是一种有艰难有困苦有牺牲有眼泪的平常,也是一种有温情有闲适有家长有里短的平常,就象生活中有"东西",也有"南北",我们固然可以爱东西,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忘记南北,而且同时也要爱南北。在我看来,这,才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创作心态,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审美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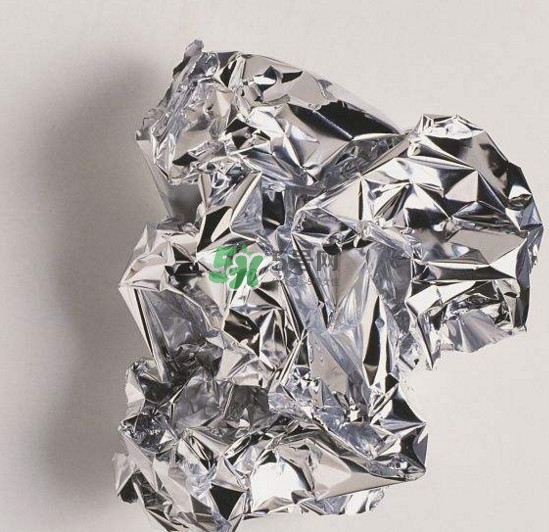






![>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 潘复生[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https://pic.bilezu.com/upload/7/40/74019e5a140356b61ea2c5cf64d49120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