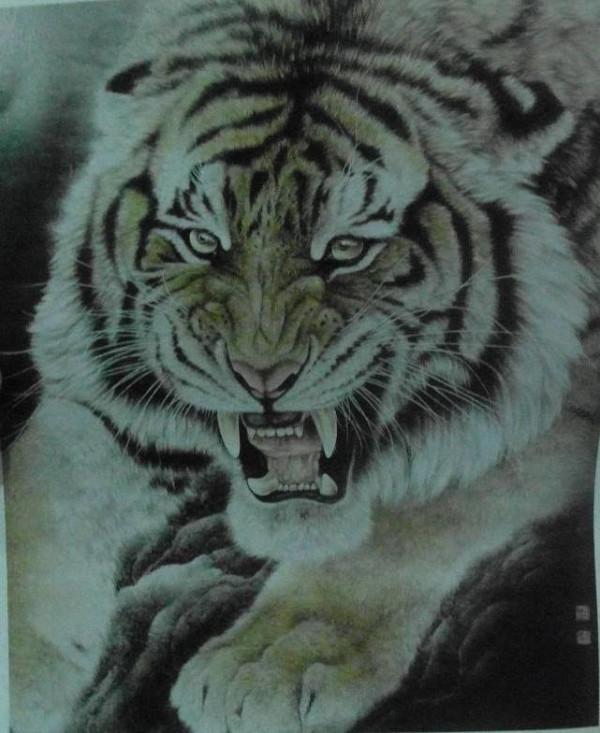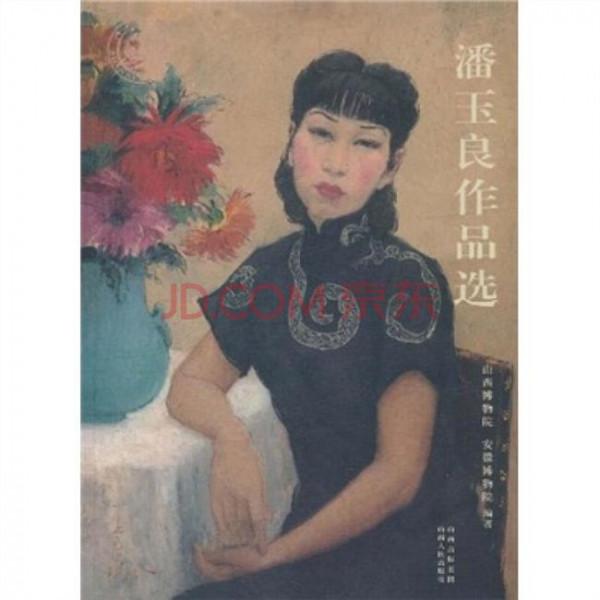潘知常艺术关怀 潘知常:从终极关怀看中国艺术
一、从审美活动的价值取向到艺术活动的价值取向
一个关键性的缺憾:未能关注中国艺术价值取向
首先从终极关怀的角度对中国艺术加以考察。
“中国艺术”,人们都很熟悉,不过我还是要界定一下,我所说的中国艺术主要是以中国书画中国建筑中国戏曲为主,当然,其它的中国艺术的门类也会有所涉及。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领域,无疑是因为有感于当今中国艺术的研究现状。我尽管不研究中国艺术,但是由于自己从事的美学专业的关系,——特别是因为自己有十几年的时间曾集中精力研究过中国古代美学,我对中国艺术领域的研究也并不陌生。
根据我的了解,这些研究成果非常令人鼓舞,可是也存在一个关键性的缺憾,就是未能关注中国艺术的终极关怀也就是价值取向的问题。而且,也恰恰因为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因此也就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艺术方面的研究成果的深入与拓展。
在前面,我已经讨论过审美活动的价值取向问题,其实,在中国艺术的研究上,也同样存在着中国艺术的价值取向问题。
遗憾的是,我们在中国艺术的研究中与在美学研究中一样,对于中国艺术之为中国艺术的价值取向同样关注得不够。因而,也就影响了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的深入。例如,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关于中国艺术的具体研究、专业研究,这些研究从局部来看,都很有水平,但是,恰恰因为缺乏对于中国艺术的价值取向的研究,因此也就都难以做出真正的学术发现。
再如,还有很多很多的中西艺术比较的研究,也因为大多缺乏对于中国艺术的价值取向的研究,因此也就都难以做出真正的学术发现。
上述研究的缺憾,集中表现在对于中国艺术的未来前景的展望方面。因为缺乏对于中国艺术的价值取向的研究,为中国艺术大唱赞歌甚至以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学者固然昏聩,即便是那些力主唱衰中国艺术的,尽管声音非常耸人听闻,但是,也仍旧仅仅留下一片争议甚至非议。
以多年来最为著名的三次关于中国艺术的讨论为例——这其中的二次都与我们南京有关,第一次,是李小山。李小山说,中国画已经日暮途穷。不难想见,他的唱衰中国艺术的看法在当时的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继而,李小山的话音还没落,吴冠中先生又破门而出,他说,中国艺术的笔墨等于零。
平心而论,李小山的看法还只是一种历史判断,还不太伤害中国艺术,但是,吴冠中先生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他否定的是中国艺术的立身之本——笔墨。
这就很让人有点受不了了,因为他显然就是在进行专业的评判。但是,这一切都还不够,后来南京师大的林逸鹏教授又出来大发感慨,说:何止是笔墨等于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现在凡是收藏当代中国绘画的,其实完全就是在收藏废纸。
毋庸讳言,这三次挑战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也都很有意义。但是,平心而论,却直到今日也没有能够让中国艺术领域的学者们心服口服。清朝的学者沈宗骞指出:在讨论中国艺术的时候,“万万不可务外观而不顾中藏也”, 看来,这个毛病一下子就持续了百年,而且,改也难!
那么,如何才能够“顾中藏”呢?在我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关注中国艺术的价值取向,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学术空间。
十年前,我就开始关注中国艺术的价值取向问题,2005年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我专门做过两次演讲,第一次,是2005 年 6 月 12 日在江苏省国画院“拥抱多元创新时代,推进先进文化发展”中国画理论研讨会上,我有一个发言:《多元创新时代与中国画创新》;发言之后,听说效果尚可。
而且,可能也是因为效果尚可,没过几天,江苏省国画院的赵绪成院长又专门邀请我,在国画院再做了一次主题演讲:《从中国的抒情美学传统看中国画的美学空间》。事后又听说,很多与会的学者和画家也都感觉还是言之成理的。
我的基本看法,简单来说,从2005年到现在,都是——也一直是:中国艺术在历史上非常成功,而且,即便在今天,也还仍旧有着自己的发展空间,但是,同样也必须指出的是,中国艺术的发展空间已经十分有限,而且,如果不及时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也已经根本无法再展辉煌。
“集中意识”与“支援意识”
之所以这样说,当然不是发一时之感慨,而是出之于以中国艺术的价值取向为背景的学术思考。
我们知道,西方的英籍犹太裔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波兰尼(1891-1976)曾经有过一个重要的发现:一个科学家、作家的创新活动可以被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可以言传的的层面,他称之为“集中意识”,还有一个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层面,他称之为“支援意识”。
而一个科学家、作家的创新无疑应该是这两个层面的融会贯通。举个通俗的例子,在科学家的研究工作里,他的研究能力就是“集中意识”,而他的价值取向则是“支援意识”。在作家的创作过程里,他的写作能力就是“集中意识”,而他的价值取向则是“支援意识”。
显然,在这里“支援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科学家、作家的创新其实都是非常主观的,而不是完全客观的。可是,即便是科学家、作家本人也未必就对其中的“主观”属性完全了解,因为在他非常“主观”地思考问题的时候,他的全部精力都是集中在“思考问题”上的,至于“如何”思考问题,这却可能是为他所忽视不计的。
何况,不论他是忽视还是不忽视,这个“如何”都还是会自行发生着作用。
例如,同样是面对火药,中国人想到的是可以用来驱神避邪,西方人想到的却是可以用来制作大炮;同样是面对指南针,中国人想到的是用来看风水,西方人想到的是可以用来做航海的罗盘,其中,就存在着“主观”的差别,也存在着“如何”的差别。
由此可见,在审美活动中,“支援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进入审美活动以后其实都是非常主观的,而不是非常客观的。可是,所有的审美者却未必能够对其中的“主观”属性完全了解,因为在非常“主观”地进行审美活动的时候,他的全部精力都是集中在“怎样”审美之上的,至于“何以”审美,却往往被忽视不计。
然而,审美过程中的主观属性却不能不予以深究。何况,在审美活动中,主观属性要表现得远比在科学活动等中更为充分也更为根本。
这就是说,在审美活动中,既存在着“主观”的差别,也存在着“如何”的差别。而这个“主观”的差别与“如何”的差别,就正是研究审美活动的关键,也是研究中国艺术的关键。
即令不“国”,也不能不“粹”
“主观”与“如何”,涉及的是价值取向的问题。长期以来,在事关中国艺术的生死存亡的讨论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声音中存在着某种偏激。这就是:以“国粹”、以“中国特色”作为保护伞来袒护中国艺术。或者说,先天地认定只要是“国粹”、只要是“中国特色”,就一定会是不会衰落的。
当然,事实不应该是如此。我必须强调,,“国粹”两字,在很多人那里,都太重视“国”了,而且,也太不重视“粹”了,以至于错误地认定只要是祖宗留下来的就是宝贝,只要是中国的,就是宝贝。但是,事实上,“国粹”、“国粹”,重要的是“粹”而不是“国”,如果不“粹”,什么样的“国”都没有用。反之,现代意义的中国艺术,即令不“国”,也不能不“粹”。
换言之,只要是“中国”的,就一味地认定肯定也是“艺术”的,这种看法是毫无逻辑的。在这里,重要的是讨论“艺术”,而不是讨论“中国”;首先要讨论的也是“艺术”,而不是“中国”。
而要首先讨论“国粹”之“粹”,则必须首先讨论中国艺术中的“艺术”,我们亟待考察的,应该是中国艺术的价值取向,也就是中国艺术与艺术之为艺术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而中国艺术与艺术之为艺术的价值取向之间吻合程度的高低,则决定了中国艺术本身的发展前景的有无以及中国艺术的发展空间的大小。
必须强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背景的艺术固然都有其自身的“特色”,但是,却又有其共同的内涵。这共同的内涵,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背景的艺术之中所蕴含的最大公约数、所蕴含的公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过:“既然地球和人类都只有一个,东方西方就不能把人性分裂成彼此不同的两半”。 “味之于口,有同嗜焉”。 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背景的艺术之中所蕴含的最大公约数、所蕴含的公理,根源于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所本有的那种休戚相关的共同性。它是人类生存和文明存续的普遍需要。
世界是平的,艺术也是平的。在艺术之为艺术的问题上,是绝对不允许有艺术“钉子户”的存在的。而且,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艺术中蕴含着程度不同的最大公约数与公理,从特殊价值到最大公约数与公理的攀升则意味着不同文化文化不同民族的艺术自觉所能够达到的某种境界。蕴含最大公约数与公理越多的艺术,就越先进,反之,则越落后。所以,不仅可以从中国艺术的角度去论证公共价值,也可以从西方艺术的角度去论证公共价值。
另外一个方面,在今天看来是特殊价值的东西,例如中国艺术的某些价值取向,也许在中国艺术中曾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价值,但是而今一旦被放在整个人类艺术的整体格局来看,则已经又属特殊价值,这是因为,人类已经认同了更加超越、更加美好和更加重要的价值。
也因此,我们所谓的最大公约数与公理并不与艺术多样性彼此抵触,不但不抵触,而且,我们所谓的最大公约数与公理恰恰就应该来自于多样性的艺术,在这当中,最大公约数与公理无非只是从多种多样的艺术中通约出来的“公分母”,而那些无法通约的部分,则就是所谓的多样艺术了。
不过,艺术的多样性存在无疑是有赖于最大公约数与公理的存在的。没有最大公约数与公理,艺术的多样性也就没有了发展的必要前提,犹如没有了艺术的多样性,最大公约数与公理也就没有了存身之地。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者所特别感兴趣的“中国特色”尽管绝对并非一个负面的东西,但是,“中国特色”却绝非一个不需要任何前提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的提倡,也必须强调一个前提,这就是:这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对于艺术的最大公约数与公理的接受或拒斥。
如果接受,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如果拒斥,则是虚假的“中国特色”。也因此,任何特殊价值的迷恋与推崇都不允许超越其所属文明的界限,以艺术多样性或艺术相对主义的名义拒斥最大公约数与公理,显然是非常不明智的。
二 、“有形式的神性”与“有形式的人性”
有形式的意味
对于中国艺术的价值取向问题的关注,让我们意识到了艺术之为艺术的价值取向的作为参照背景的重要性,显然,时时刻刻清晰地意识到艺术之为艺术的价值取向何在,是我们研究中国艺术问题时的一个绝对不可或缺的前提。
那么,艺术之为艺术的价值取向何在?
还回到康德“主观的普遍必然性”的看法,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主观的普遍必然性”中的“主观”,涉及的是审美活动所构成的东西,“主观的普遍必然性”中的“普遍必然性”,涉及的则是构成审美活动的东西。现在,如果还需要再进而言之,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里的“主观”,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形式”,这里说到的“普遍必然性”,则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意味”。
因此,如果简而言之,我们也可以把西方美学家克莱夫比尔的定义颠倒一下,他的定义是: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而我们则可以把艺术定义为:有形式的意味。
西方美学特别喜欢讨论“形式”问题,那么,什么是“形式”?从理论上,当然会有很多种说法,不过究其实质,其实也无非就是指的有助于显现对象身上的那些不是自身的价值而是对于我们的价值,那些向我们显示着的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的东西。
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威《建筑十书》提到:苏格拉底学派的哲学家阿里斯提普斯航海遇难,漂流到洛得斯海岸的时候,他看到了在沙子上描绘的几何图形,于是就跟同伴们说:有希望了,我们终于看到了人的踪迹。
显然,这里的“几何图形”就是那个有助于显现对象身上的那些不是自身的价值而是对于我们的价值、那些向我们显示着的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的东西。所以卡西尔说:“艺术家是自然的各种形式的发现者,正像科学家是各种事实或自然法则的发现者一样” 其实,这里的“形式”无非就是人类对于世界的期待的象征。
而他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身上看到那些能够满足这种期待的东西,就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形式”。所以卡西尔又说:“我们可能会一千次地遇见一个普通感觉经验的对象而从未‘看见’它的形式。
” 打个比方,这让我们想起了情书与情诗的区别。为什么情书只能感动自己的恋人?而情诗却会感动所有的人?还不就是因为在情诗里更加有助于找到那些不是自身的价值而是对于我们的价值、找到那些向我们显示着的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