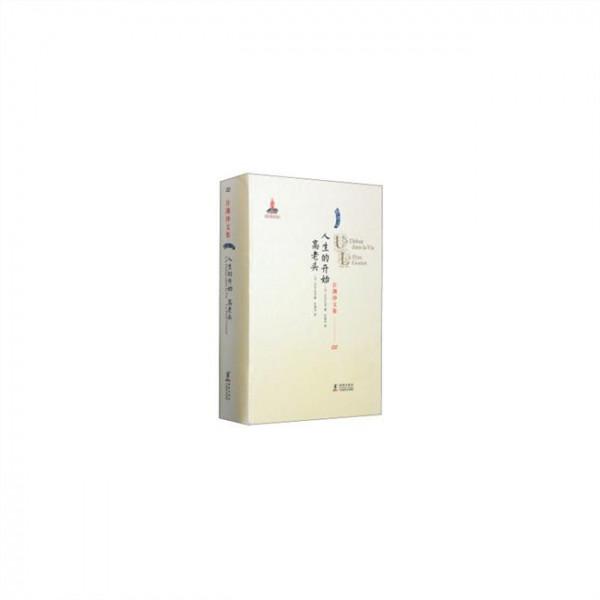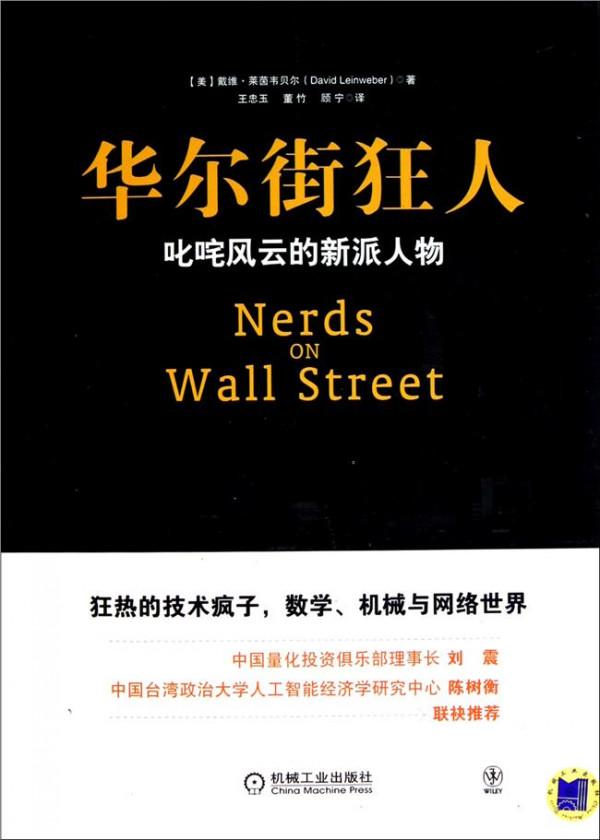许钧哪里人 译界人物:许钧的翻译人生
许钧在法国的声誉很好,朋友尤其多。他在1993年、1998年两度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奖译金”,1999年又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这些奖项与翻译,让他与国内外很多大学者、大文豪成为挚友。
“这种交往都是从理解开始的。”许钧说,“很多的交往都是从阅读他们的文本和理解他们的思想开始的,比如说20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勒克莱齐奥,我是通过翻译遇到了不能解决的问题向他求教,之后慢慢成为好朋友的。”
但正因为翻译事业的特殊性,许钧的交友既是深交,又是“神交”。因为《安娜·玛丽》,许钧结识了法国当代作家博达尔。1998年,他到博达尔家中拜访,立时就被其家中填满六七个房间的书给震惊了。他很快就沉浸到这些法文书的世界里,甚至连和主人交谈的时间都没有。
饭后,博达尔的夫人、法国著名的《观点》杂志文学版主编跟许钧说:“许先生,看你这么爱书的样子,今天我给你一个礼物,你看上的书都可以拿走,但这辈子只能拿一次。”
这些书大多十分昂贵,有几本中国古典名著的法国译本,在1998年一本就价值1000多法郎。因为与博达尔家的友谊很深,他顾不上客套,立时选了法国七星文库出版的中国四大文学名著,之后又欣喜若狂地装满了两大袋书。博达尔也全部慷慨地赠予了他。
无论国内外,这样超脱的交往故事,在许钧的身上屡见不鲜。许钧的一位同事说:“不管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即使再沉闷,和许钧在一起也能感觉如沐春风,很开心,会变得很健谈。”这两年应他之邀,勒克莱齐奥还担任了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今年9月就要来给南大学生开设一门选修课。
而另一位被称为“法国的钱锺书”的著名汉学家艾田蒲,在巴黎与许钧研究完《中国之欧洲》的翻译问题后,回到家,84岁高龄的他给许钧手写了一封信。在信的开头,艾田蒲说:“杰出的同行,请允许我把我和你的见面视作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我们共进午餐的时候,我不断地在欣赏着从你的脸上发出的那种智慧的光芒。”
但有着这么多朋友的、活跃的译者许钧却经常说:“翻译家是孤独的。”无数个伴着孤灯书香的夜晚,许钧都在深思翻译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他说,翻译致力于不同文化的交流,转换中一定会失去很多东西,面对这些,翻译家感到非常孤独,“他孤独无援,他永远在想怎么把这些差异传达到别的文化中去。”
翻译家们面临一个悖论:一面要消除语言的差异,一面要传达文化的差异。如果不能传达文化差异,根本的任务就失去了,而语言方式一变,其意义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言当中得到的反应可能完全不同。许钧甚至常常悲观地想,这就像因盗取圣火而获罪于上帝的普罗米修斯,上帝命他将一块巨石从奥林匹斯山脚推上山顶,但每当要到山顶时,上帝便又将巨石推下,普罗米修斯每天不断接近终点,每天却又重归起点,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更重要的是,翻译永远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而且不可能一劳永逸。一部作品的翻译是为一代人服务的,因为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在不断加深,语言在不断变化。“译者中的新人要不断地推出新的翻译,而老者则眼睁睁看着一部作品离开,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
无数的夜晚,许钧在这种孤独当中寻求翻译的意义与使命,在不可能中不断前行。许钧说,如果说翻译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既要有勇敢,也要有一种孤独的不可为而为之的壮烈。一个翻译者,必须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刻的理解,而这一定是孤独的行为,只能独自完成。
“译者的孤独就在于他在追寻一个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业,但当两种事物达成沟通之后,译者永远是不在场的,他永远隐藏在作者和其他交流者的后面。”许钧说,翻译本身就是孤独的行为,翻译家也只能孤独,但这又是幸运的,因为“如果你选择了一部优秀的作品,就可以和大师神交。这是一种承载着历史使命与时代文化的灵魂的交流。”
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翻译是必经之路
许钧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叫《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翻译已不再是事业的范畴,甚而重于生命。他的使命感从未像今天这样清晰,而最为急迫的就是要推动翻译学科的发展。
作为国内最杰出的翻译家之一,2006年,他全程参与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设置论证工作。经过不懈努力,2007年1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终于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3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作为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和人力资源部聘任的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参与制定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方案和标准,并与其他学者共同主编了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系列教材。
近年来,许钧更是频繁奔走于100多所院校,讲授“翻译概论”示范课,成为国内翻译学科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长期奔波,让许钧的身体有些吃不消,医生诊断他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嘱咐他要卧床休息,但他依旧坚持到教室给学生上课,有时候上完一堂课,要学生扶着才能站起来。这一切为的就是推动翻译学科的建立,尽快带出来一批核心力量。
在许钧看来,目前“全民学英语”的社会氛围,恰恰妨碍了跨文化交流,也妨碍了翻译学科的建立,不利于翻译人才的培养。而令人更为不安的是,社会普遍认为翻译只是一种实践,没有系统的理论认识,特别是很多人觉得只要学外语的都会翻译。
面对这些问题,许钧在各种场合一再大声疾呼:“翻译有其根本性的问题,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翻译所做的贡献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交流日渐频繁,对翻译事业的要求也日趋提高,国内翻译理论研究急需向系统、科学的方向转型。”
这个性格温和、几乎从不与人争执的谦谦君子,在这件事上变得特别急迫。“一个民族语言的消失,便意味着其文化的消亡。”许钧郑重地说,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尤其不能以牺牲民族语言为代价,仅仅用英语去谋求与外部世界的交流。
与很多爱慕外国文化与热衷“秀外语”的翻译者相比,许钧显得很冷静,他坚持应该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使用与发扬中国语言,同时培养更多的翻译人才来满足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学科的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
“翻译是一项事业,许老师不断鼓励我们认准方向并坚持下去,以成就这门学科。”许钧教授曾经的学生、现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刘云虹说,这个方向伴随着老师多年,他人生之路就是中国翻译学科建立的艰难之路。
从1975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许钧在38个年头里,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理想。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许钧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没有他们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中国的文学才可以变为世界的文学”。
在南京大学,由于许钧的推动,涵盖本、硕、博士各学历层次的翻译人才培养体系逐渐建立。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的许钧,希望能亲手带出一批深具翻译使命感的弟子,为高水平翻译人才的培养做出贡献。如今,他的学生中有著名的翻译家,有国内大学的法语系主任,有外语学院的院长,有省市翻译协会的副会长,全国法语界5位“新世纪优秀人才”中有3位出自他的门下。
“翻译学科意味着什么?”许钧说,它事关我国的对外交流;事关中华文明的发展;事关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民族文化是否能闪耀更为灿烂的光辉。在他的心底,翻译早已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文字转换游戏,更不单纯是文学的交流,而是一个国家走出愚昧、走向开放、走向文明的标志,“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翻译是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