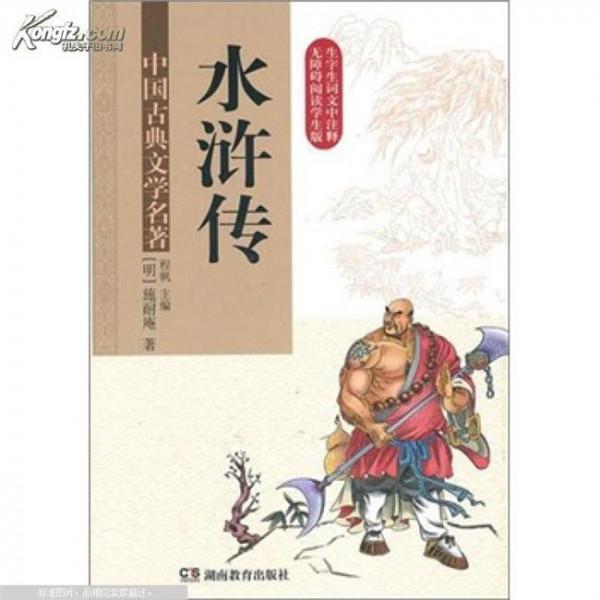文学的前途夏志清 夏志清《文学的前途》读书笔记
不可否认的夏先生的学术和作品都是相当有价值的。以下只是读书过程中的一点感想,记下来留待以后反思、修正,或印证。没有读过这本书的还是要慎入,以免被误导。当然,有可能来这里参观的某M某喵与某姜,我相信你们都是没有耐心看完全文的。
夏先生是位中国人,却领有一个西方汉学家的头衔,这样的身份,实在不能不说是奇怪。也大概也正因为这样的缘故,虽然这本书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有些分析客观、深刻,但是整体上拥有的倾向性却很难让我完全认同。
这本书里的两篇文章都节选自《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是夏先生用英文著成的一本书,与他的另一本书《中国古典文学》一起,造就了他在西方汉学界的声望。撇开英译中的过程带来的损伤不谈,抛开内容不谈,单就文章段落结构与句式而言,也的确可以看出夏先生受西方文学浸染之深,说真的,单从中译本的文笔而讲,这确实不能算是一本文笔流畅的好作品。
相比之下,原始作品就是用中文写就的《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要好得多。
夏先生是研究英美文学的底子,20世纪初期文化革命(即我们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成长的人,早年赴美。这样的背景不难从书中看出来,尽管是在评述中国现代文学与小说,夏先生仍然会用英美文学中的相关典型进行多方面比照与参考。
拥有英美文学研究背景,应该是对研究中国文学无害的,它带来的外部视角确实是我这个乡土读者本身所不具有的,我也时时看的入神。但是,实在是可以用而不可以滥用。在夏先生的笔下,不管是沈从文还是白先勇,都与英美文学有着不可切割的渊源,对英美文学的学习与运用,甚至成为了他们两个文学创作的转折。
他们的某些侧面,也一定可以找到华斯莱斯,艾略特或者是叶芝福克纳的影子,这一点让我觉得实在牵强。而,卷入整个新文化运动及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建国之前的变革中发挥作用的每一位文学创作者,也无一不是因为受了外国文学的浸染才可以有所作为(好的或坏的),他们甚至可以简单地被划分为英美派系与日本派系(我总结的,夏先生的描述方式是一帮是留学英美的人,对立的另一帮是留学日本的人),在打开封闭的国门后,中国现代文学受西方文学影响(不管是力挺的还是反对的,那个时候的文学作者都是逃不开的)是不可否认的,只是这种一刀切的划分未免失于武断。
但或者,事实就是如此,只是我才疏学浅不太了解。 在《文学的革命》这一篇里,夏先生谈了他对新化文化运动的看法,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夏先生“西方汉学家”这一身份带给他的影响。我觉得不能够用右或者自由化倾向来评判夏先生,但是夏先生却是很喜欢这样给他人定性。
在他的眼里,新文化运动中有两个派别:一个是留学日本和法国的激进派(以陈独秀为代表),另一个是留学英美的民主派(以胡适为代表),整个新文化运动以及之后一系统社会变革中的文学力量,都是非左即右的。
夏先生对于当时的文化现象以及文学作品有着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因为才会有“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除了鲁迅、叶绍多、冰心、凌叔华、落华生和郁达夫等人的作品,都是不成熟的。
”这样的价值标准,我不能够全然接受,尽管我也不能够完全理解,我把自己所能达到的理解程度记录一下。 夏先生的价值标准首先是以民主思想为基石的,这不仅体现在《文学的革命》这一篇,后面关于沈从文的一篇也可以看出来,尽管对于左派文学的激进和自由派的软弱与狭窄他都有明显的批评,但是对于历史最终被激进的左派所控制从而使中国发展成今天这样是极为不满的。
可以体现他民主思想的,还有他对于“尊重个人尊严”这一点的肯定。
在文中他曾提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是很推崇个人主义的,但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这一点在文学界日渐消亡,“虽然在五十年代,不少作家发现自己在私底原来一直是个个人主义信徒”。
另外,即是以西方文学为参考,并暗含对西方文学思想及写作技巧的推崇。透过我认真研读的三篇(还有一篇是关于白先勇的),可以总结出来他对于华斯莱斯、叶芝、艾略特、福克纳是相当推崇的,虽然不具有大方面的共性与可比性,夏先生仍然时不时地将沈、白二人与他们相对比,如若发现有某一具体方面有细微的共性,是一定要写出来的。
在提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们的一些不足时,也用了”缺乏对西方古典文学的的研读”(不是原话)类似的描述。
担心我看到的只是一些个例,还专门看了本不感兴趣的《老残游记新论》,果然在这里发现了类似的对比,当然不只有这些对比这么狭窄,对于夏先生的学识,尚轮不到我置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倒觉得,夏先生更适合去做比较文学的研究,而不必是个单纯的“汉学家”。
在读《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这一篇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从分析方法上而言,夏先生也是西方色彩浓郁的。有位留学海外的朋友跟我讲述西方人的写作方式——追求结构上的严谨,大论小著对结构的要求几乎是一致的,因为我并没有太多的考察西方文学,权且把它当成事实来看。
沈从文早期短篇小说结构“松懈”恰是被夏先生诟病颇多的。完全将沈从文的人品与作品分离开来单纯评述他的作品的文学评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是我孤陋,不是评论欠缺),而这恰是我认为夏先生没有读懂沈从文的关键。
“为了表示他与其他作家的不同,沈从文很喜欢强调自己的农村背景”,“这种看法,当然是道家和罗曼蒂克的看法”,“我们都可以找到表现沈从文高度印象主义写作技巧的例子”,诸如此类的说法就是例子。
我也不懂沈从文 ,但在我的观念里,沈从文的作品与他的人品是绝对不可分割的,他所想要描写和展现的情景,是源于自己内心的某种境界的。
像是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他可以不必结构严谨,修辞得当。完全抛弃了沈从文的人品,“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这种句子,自然是不能够完全被理解的。让我觉得诧异的是,这句话在我的眼中,似乎是在透过主人公周围的眼睛来看这个人,而他周围的人,都是朴实的苗乡人民,他们使用这样的修辞是很自然很正常的,虽然没有提及沈从文人品,却对他的成长背景有一定了解的夏先生,为何竟没有看出来呢? 透过上面的例子,我也可以说,夏先生的文学评论方式,是纯技术性的。
在他的文中,我们常见他给文学创作者以定性,冠以“XX主义”。对于创作文学作品的作者内心世界的作用,他虽然有所关注,但有单纯透过作品去了解的局限。
对于白先勇,夏先生直言“我同白先勇先生虽然见过几次面,通过不少信,但从谈及他的家世和私人生活,但从他的作品上的推测,我们可以知道他早年的一些经历。”而这些从作品中发现的经历又成为了分析其作品性格的佐证。
对于沈从文先生,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的了解多半是来自于一本“从文自传”。我以为,至少应该会有一些左右旁他的资料来更深入地了解一下,佐证一下才好。所以,尽管他说“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富有象征、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我仍然觉得,他没有真正的理解沈从文,但是这对于理性的文学评论来说,也许并不是必备的。
我也因为这样浅浅的接触,而对夏先生持有两个疑问。其一,在夏先生的眼里,中国现代小说,究竟是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西方文学。
夏先生对于西方文学的技巧的推崇不言而喻,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发展,是以运用西方小说技巧起步的。他笔下的沈从文、白先勇二人短篇小说的成熟,都是与受西方文学影响分割不开的。
在提到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成功开端时,用了这样的表述“他(鲁迅)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地运用了西方小说的技巧,与中国传统的说故事方法完全两样,因此可以称为是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始祖”。
同时,他对完全割裂了本国传统文化单独的吸收西方方式,是很反对的。从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左派文学的评价中可以略见一斑,而白先勇则正是因为对二者有很好的揉和,并加入了自己的发展而获得他的肯定。
其二,则是,文学在对人类心灵问题的探讨与对现实的责任二者中,应该对哪个付出更多的关心。前者是《文学的革命》中提到的新文化运动拉开的改革序幕中所缺乏的,而缺乏后者则是在《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中所提到的沈从文的不足。
解释这两个问题,大概我真的要去读一下夏先生的两本名著,只是说实话,我对纯技术的评论所能提起的兴趣可能仅止于白先勇和沈从文(我最喜欢的两位文学家),也或者我并不真正需要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一定要给一个定性的话,我也许会太过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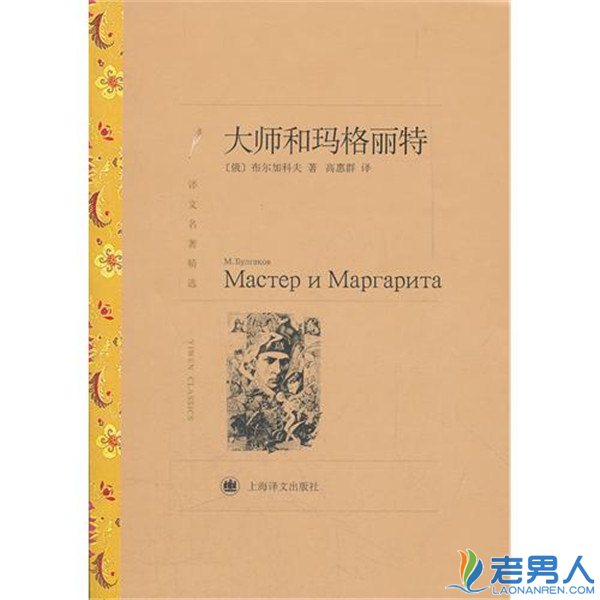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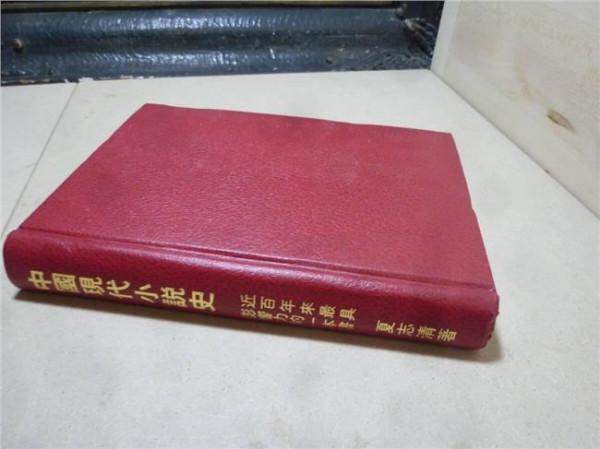
![>夏志清论张爱玲 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去世曾收到张爱玲103封信[图]【2】](https://pic.bilezu.com/upload/1/34/1346d47effaad8921e7fc8a92e5b6d38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