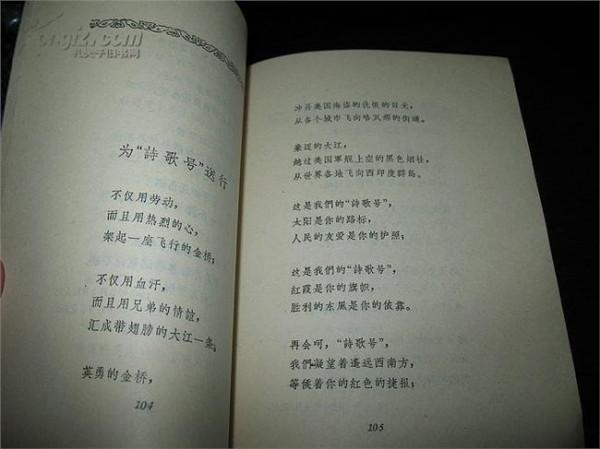宋小川和大牛 宋小川:幸福和快乐可以测量吗
人类有史以来就将对幸福和快乐的追求作为奋斗目标。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对追求人生的幸福和快乐都留下了富有哲理的寓言、美丽的神话、动人的故事和脍炙人口的描述。然而,什么是幸福和快乐?如何去计算和测量幸福和快乐?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和快乐?求解这一快乐之谜的使命落在了被称为“沉闷科学”(dismalsci-ence)的经济学肩上。
古老命题的求解
经济学家对幸福和快乐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英国伦理学家边沁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口号。此后,19世纪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功利主义”也把追求快乐和幸福视为人们行为的动机。
几百年来,经济学家们为如何去计算和测量幸福和快乐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令人郁闷的是,时至今日,经济学家既未能对幸福和快乐达成一个普遍可接受的严格定义,也没有找到一个科学测量幸福和快乐的方法。
自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活动代替了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活动后,幸福和快乐便沾染了铜臭。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日益盛行,拜金主义在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泛滥成灾,在经济迅猛发展的转型经济国家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追求幸福和快乐的愿望是美好的,可悲的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通往地狱的道路恰恰是由这种美好的愿望铺成的。冷静的人们也许该再次反思这一古老而又热门的话题:钱能买到幸福吗?
当著名经济史专家RichardEasterlin,在20世纪70年代根据他对快乐经济学的研究,得出钱不能买到幸福的结论时,他的经济学同僚们还在嘲笑他的研究成果是鸡尾酒会的闲谈,而非严肃的经济学课题。而今天,日益增加的研究人员正在试图通过对快乐经济学的研究寻找通向幸福之路。
Easterlin于上世纪70年代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时,已经将人口统计学从传统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并从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中得知若干散见的有关人们快乐程度的调查。他通过对20多个国家的统计、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得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反论”(EasterlinParadox):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其中美国居第一,古巴接近美国,居第二。
Easterlin对其发现的分析和解释也颇具说服力:尽管文化传统的差异会使某些国家人民的快乐感超过其他国家,但不同社会生活水平存在着差异的现实是超越国界的。问题的关键是,越富有的国家,人们期望的就越多,因而降低了“财富振奋精神”(wealthliftsspirits)的机会。
所以,决定人们快乐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对幸福和快乐的“渴望”(aspirations)。这种渴望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收入水平开始影响人们的幸福水平。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或期望值对人们的快乐和幸福程度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足者常乐就是这个道理。
这些发现引起了Easterlin的极大兴趣,但却受到了他的同事,的奚落:“你以为这是突破,但经济学界绝不会买你的账”。然而,20多年后,快乐经济学的研究再度兴起,不过这次是以欧洲为中心。近年来,美国对快乐经济学的研究在Easterlin早期发现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起步。
Easterlin本人也于10多年前再次步入这一研究领域。美国流行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O'Sulli-van和Sheffrin以《钱能买到幸福吗?》为题,根据Blanchflower和Oswald的发现,按种族、性别和年龄逐项对人们的幸福水平进行了比较和总结。
通向幸福之路何在
通常,经济学家们热衷于描述人的实际经济行为,而对用民意调查去测量幸福和快乐的可靠性、客观性和科学性表示怀疑。社会学家先走了一步。一批欧洲社会学家每年都会对由15000欧洲人组成的随机样本提出这类问题:“总体来说,你对生活非常满意,还算满意,不太满意还是根本不满意?”这些研究人员还对许多其他国家的抽样调查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对四个答案分配4到1的分数,据此去测量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以探求决定人们幸福水平的要素。
许多研究神经系统的科学家,特别是心理学家,也时常与经济学家联手进行研究。
将人们的快乐程度简约为数字和经济学家所痴迷的数学公式无疑是对经济学的挑战。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Rayo和Becker应用和发展了演进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并结合数学分析,去探讨人们经历幸福的方式。行为经济学家和试验经济学家们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MichaelMcBride和LoyolaMarymount大学的JamesKonow采用心理学家的试验手段,将研究对象——人放到实验室进行测试,观测人们对一种赌博游戏的不同规则和结果的反应。快乐经济学家们还试图测量影响快乐水平的因素,并把它们折算成货币价值。
诚然,经济学家承认,人们可以评估从消费一种商品得到的满意程度是否大于消费另一种商品;人们也可以判断本周的总体满意程度是否高于上一周。但许多经济学家质疑一个人消费某种商品获得的满意程度可以与另一个人相比,特别是某一个人在某一时点的总体快乐水平超过另一个人。
许多习惯了GDP一类指标的经济学家们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对人的满意程度进行测量的努力,他们怀疑建立在民意测验基础上的研究是否能真正科学地测量人们的幸福水平。
如果赚更多的钱通常不能使人们,尤其是整个社会更加快乐,那么什么能够提高人们和全社会的幸福和快乐水平呢?
人们的快乐和幸福程度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构成的,其中制度、文化和心理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对生活水平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人们在生活和就业方面的压力及安全感,社会是否给人们提供了相对公平的机会,离婚率、犯罪率、司法公正程度,民主和政治方面的透明度和官僚的腐败程度等等,这些都影响着社会的净经济福利和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因此,快乐经济学的研究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它为政府在以上各个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遭到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主流经济学除了质疑“看法调查”(attitudesurvey)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外,还把这种研究斥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左翼倾向。
快乐经济学家们并不否认其研究的政策倾向,他们强调快乐经济学并不单单是对人类情感的研究,其最终目的是使经济学更好地造福于人类和帮助指导公共政策。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过于注重经济增长,而应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在实质上可使人民更加快乐和幸福的事情上。
比如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改善教育条件等。虽然这些活动不会直接增加人们腰包里的现金,还耗费巨资,但却能有效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和人民的幸福水平。快乐经济学还对古老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注入了新的政策含义。许多研究证明,尽管人们不喜欢物价上涨,但失业会使人们更加不快乐,因此,政策制定者即便冒着通货膨胀的风险也应促进稳定的就业。
快乐经济学研究与构建和谐社会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人们的效用函数是凸型的,即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收入由富人向穷人的转移会增进整个社会加总的福利水平。尽管这种收入再分配会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但是如果这种转移带来的穷人效用增加与富人效用减少之差,即效用净值的增加大于效率的损失,那么,这种收入再分配政策仍然是最优的。
凸型的效用函数还意味着收入期望值的效用大于效用的期望值。其经济含义是,人类的本性是厌恶风险,他们宁愿接受平均较低的稳定收入而不愿冒平均较高但大起大落的收入的风险,这也是保险学理论的最基本原理。效用函数的这一本质特征为我国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个发达、成熟、和谐的社会,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每个公民在生病时能得到适当的治疗是文明社会的最低要求。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保证每个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不仅可以直接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而且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增长的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解决全球性经济失衡的根本出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稳定和美满的婚姻、和睦的家庭成员关系和人际关系也是决定人们幸福水平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建立和谐社会,增进人们福祉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政府、社区和全社会在这些方面做出积极的努力,创造和谐、适宜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以及相应配套的法律咨询服务,包括建立文化和体育中心,提供健康的社交场所、婚介服务、家庭和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等。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类的适应性是极强的,人们最终几乎能适应任何事情和任何环境,特别是在金钱和收入方面。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吃苦耐劳传统就是明证。人们在金钱方面的适应性通常超过非金钱方面,一些改变人生和命运的重大事件,比如丧失亲人等,会对人生的幸福和快乐产生持久的影响。
由于绝大多数政策的制定都是基于对福利的金钱方面的考虑,因而过于强调了收入增加对福利的重要性,忽视了收入以外的许多重要因素,如健康、家庭和稳定的就业等。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
在我国改革开放由“黄金发展期”过渡到“矛盾凸显期”的关键历史时刻,我们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去的片面追求货币收入、物质财富转变到关注和增进人们的精神财富,以提高普通劳苦大众的快乐和幸福水平为中心的科学增长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快乐经济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