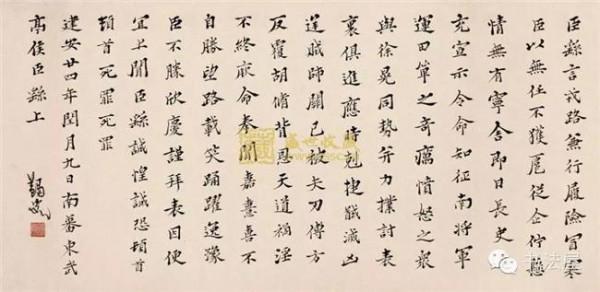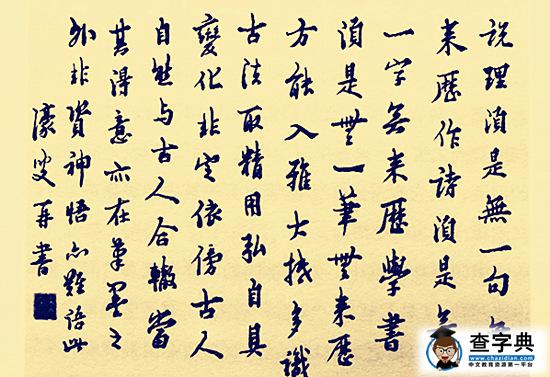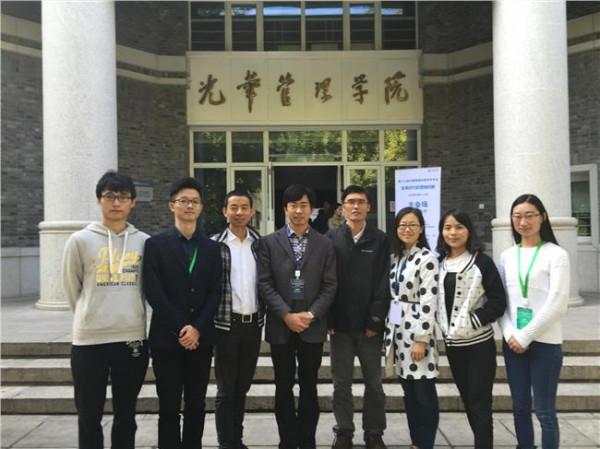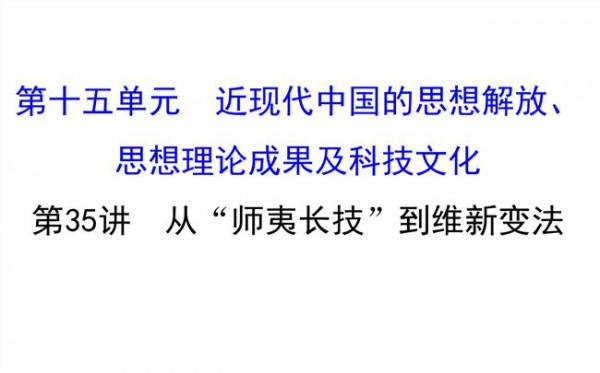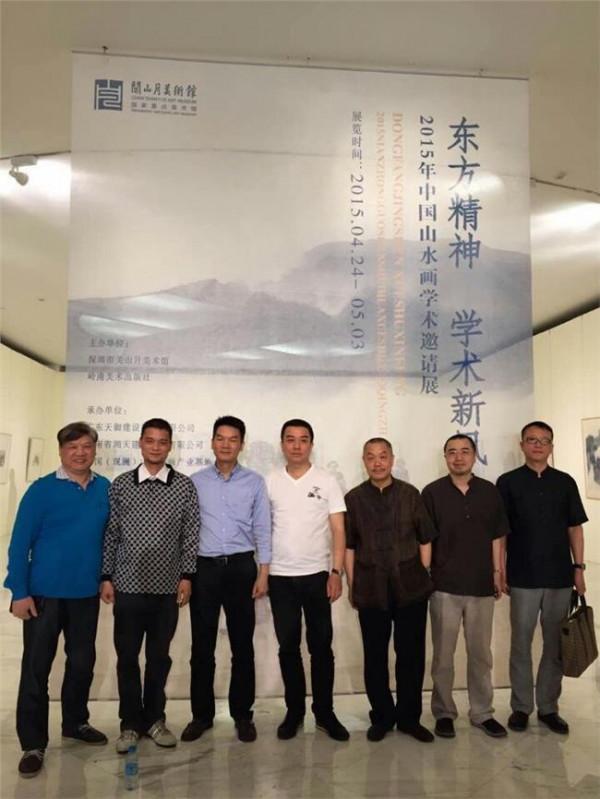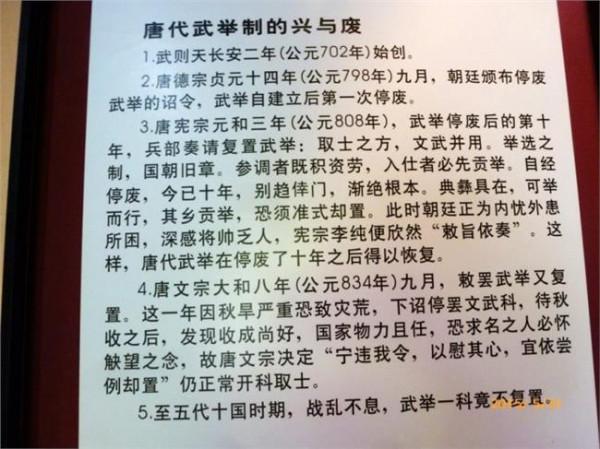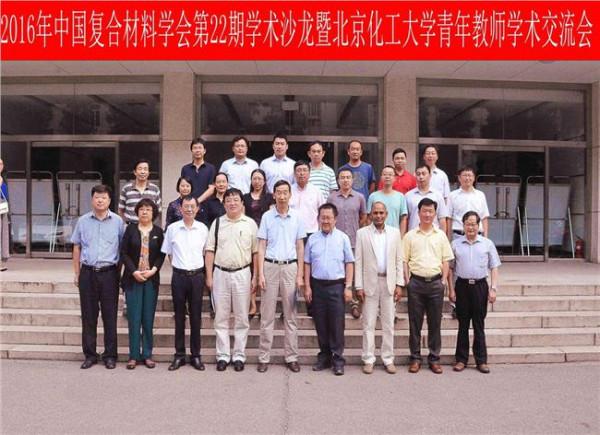马一浮六艺 马一浮: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
何以言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约为二门:一、六艺统诸子;二、六艺统四部。(诸子依《汉志》,四部依《隋志》。) 甲、六艺统诸子。 欲知诸子出于六艺,须先明六艺流失。《经解》曰:“《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学者须知,六艺本无流失,“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俱可适道。其有流失者,习也。心习才有所偏重,便一向往习熟一边去,而于所不习者便有所遗,高者为贤、知之过,下者为愚、不肖之不及,遂成流失。
佛氏谓之边见,庄子谓之往而不反,此流失所从来,便是“学焉而得其习之所近”,慎勿误为六艺本体之失,此须料简明白。 《汉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其实九家之中,举其要者,不过五家,儒、墨、名、法、道是已。
出于王官之说,不可依据,今所不用。(《学记》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民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此明官、师有别,师之所诏并非官之所守也。《周礼》司徒之官有“师氏掌以媺诏王”,“保氏掌谏王恶”。凡“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师氏“使其属率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
”保氏“使其属守王闱”。此如后世侍从之官。郑注《冢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乃以诸侯之师氏、保氏当之,变保为儒,此实于义乖舛,不可从。《论语》:“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又语子夏:“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此所言师、儒,岂可以官目之邪?《七略》旧文某家者流出于某官,亦以其言有关政治,换言之,犹曰某家者可使为某官。如“雍也,可使南面”云尔,岂谓如书吏之抱档案邪?如谓道家出于史官,今《老子》五千是否周之国史?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今墨书所言并非笾豆之事。
此最易明。吾乡章实斋作《文史通义》,创为“六经皆史”之说,以六经皆先王政典,守在王官,古无私家著述之例,遂以孔子之业并属周公,不知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乃以其道言之。
若政典,则三王不同礼,五帝不同乐,且孔子称《韶》《武》,则明有抑扬,论十世,则知其损益,并不专主于“从周”也。信如章氏所之说,则孔子未尝为卜,不得系《易》;未尝为鲁史,亦不得修《春秋》矣。
《十翼》之文,广大悉备,太卜专掌卜筮,岂足以知之;笔削之旨,游、夏莫赞,亦断非鲁史所能与也。“以吏为师”,秦之弊法,章氏必为回护,以为三代之遗,是诚何心!
今人言思想自由,犹为合理。秦法“以古非今者族”,乃是极端遏制自由思想,极为无道,亦是至愚。经济可以统制,思想云何由汝统制?曾谓三王之治世而又统制思想之事邪?惟《庄子天下篇》则云:“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说之。
”乃是思想自由自然之果。所言“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各为其所欲以自为方”,“道术将为天下裂”,乃以“不该不遍”为病,故庄礼道术、方术二名。(非如后世言方术当方伎也。
)是以道术为该遍之称,而方术则为一家之学。谓方术出于道术,胜于九流出于王官之说多矣。与其信刘歆,不如信庄子。实斋之论甚卑而专,固亦与公羊家孔子改制之说同一谬误。且《汉志》出于王官之说,但指九家,其叙六艺,本无此言,实斋乃以六艺亦为王官所守,并非刘歆之意也。
略为辨正于此,学者当知。)不通六艺,不名为儒,此不待言。墨家统于《礼》,名、法亦统于《礼》,道家统于《易》。判其得失,分为四句:一,得多失多。
二,得多失少。三,得少失多。四,得少失少。例如道家体大,观变最深,故老子得于《易》为多,而流为阴谋,其失亦多,“《易》之失贼”也。(贼训害。)庄子《齐物》,好为无端厓之辞,以天下不可与庄语,得于《乐》之意为多,而不免流荡,亦是得多失多,“《乐》之失奢”也。
(奢是侈大之意。)墨子虽非乐,而《兼爱》《尚同》实出于《乐》,《节用》《尊天》《明鬼》出于《礼》,而《短丧》又与《礼》悖。墨经难读,又兼名家亦出于《礼》,如墨子之于《礼》《乐》,是得少失多也。
法家往往兼道家言,如《管子》,《汉志》本在道家,韩非亦有《解老》《喻老》,自托于道。其于《礼》与《易》,亦是得少失多。余如惠施、公孙龙子之流,虽极其辩,无益于道,可谓得少失少。
其得多失少者,独有荀卿。荀本儒家,身通六艺,而言“性恶”“法后王”是其失也。若诬与乱之失,纵横家兼而有之,然其谈王伯皆游辞,实无所得,故不足判。杂家亦是得少失少。农家与阴阳家虽出于《礼》与《易》,末流益卑陋,无足判。
观于五家之得失,可知其学皆统于六艺,而诸子学之名可不立也。 乙、六艺统四部。 何以言六艺统四部?今经部立十三经、四书,而以小学附之,本为未允。六经唯《易》《诗》《春秋》是完书;《尚书》今文不完,古文是依托;《仪礼》仅存士礼;《周礼》亦缺冬官;《乐》经本无其书,《礼记》是传,不当遗大戴而独取小戴;《左氏》《公》《谷》三传亦不得名经;《尔雅》是释群经名物;唯《孝经》独专经名,其文与《礼记》诸篇相类;《论语》出孔门弟子所记;《孟子》本与《荀子》同列儒宗,与二戴所采曾子、子思子、公孙尼子七十子后学之书同科,应在诸子之列,但以其言最醇,故以之配《论语》。
然曾子、子思子、公孙尼子之言亦醇,何以不得与《孟子》并?(二戴所记曾子语独多,后人曾辑为《曾子》十篇。
《中庸》出子思子,《乐记》出公孙尼子,并见《礼记正义》,可信。然《礼记》所采七十子后学之书多醇。《大学》不必定为曾子之遗书,必七十子后学所记则无疑也。
二戴兼采秦汉博士之说,则不尽醇。此须料简。)今定经部之书为宗经论、释经论二部,皆统于经,则秩然矣。(宗经、释经区分,本义学家判佛书名目,然此土与彼土著述大体实相通,此亦门庭施设,自然成此二例,非是强为差排,诸生勿疑为创见。
孔子万而系《易》,《十翼》之文,便开此二例,《象》《彖》《文言》《说卦》是释经,《系传》《序卦》《杂卦》是宗经。寻绎可见。)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是为宗经论。
《孟子》及二戴所采曾子、子思子、公孙尼子诸篇,同为宗经论。《仪礼·丧服传》子夏所作,是为释经论。三传及《尔雅》亦同为释经论。《礼记》不尽是传,有宗有释。《说文》附于《尔雅》,本保氏教国子亦六书之遗。
如是则经学、小学之名可不立也。诸子统于六艺,已见前文。 其次言史。司马迁作《史记》,自附于《春秋》,《班志》因之。纪传虽由史公所创,实兼用编年之法;多录诏令奏议,则亦《尚书》之遗意。
诸志特详典制,则出于《礼》,如《地理志》祖《禹贡》,《职官志》祖《周官》,准此可推。记事本末则左氏之遗则也。史学巨制,莫如《通典》《通志》《通考》,世称“三通”,然当并《通鉴》计之为四通。
编年记事出于《春秋》,多存论议出于《尚书》,记典制者出于《礼》。判其失亦有三:曰诬,曰烦,曰乱。知此,则知诸史悉统于《书》《礼》《春秋》,而史学之名可不立也。 其次言集部。文章体制流别虽繁,皆统于《诗》《书》。
《汉志》犹知此意,故单出“诗赋略”,便已摄尽。六朝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后世复分骈散,并□陋之见。“《诗》以道志,《书》以道事,”文章虽极其变,不出此二门。志有浅深,故言有粗妙;事有得失,故言有纯驳。
思知言不可不知人,知人又当论其世,故观文章之正变而治乱之情可见矣。今言文学,统于《诗》者为多。《诗·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三句便将一切文学判尽。《论语》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可见《诗》教通于政事。“《书》以道事”,《书》教即政事也,故知《诗》教通于《书》教。《诗》教本仁,《书》教本知。
古者教《诗》于南学,教《书》于北学,即表仁知也。《乡饮酒义》曰:“向仁”“背义”“左圣”“右义”。藏即是知。(“知以藏往”,故知是藏义。)教《乐》于东学,表圣;教《礼》于西学,表义。故知、仁、圣、义,即是《诗》《书》《礼》《乐》四教也。
前以六艺流失判诸子,独遗《诗》教。“《诗》之失愚”,唯屈原、杜甫足以当之,所谓“古之愚也直”。六失之中,唯失于愚者不害为仁,故《诗》教之失最少。后世修辞不立其诚,浮伪夸饰,不本于中心之恻怛,是谓“今之愚也诈”。
以此判古今文学,则取舍可知矣。两汉文章近质,辞赋虽沉博极丽,多以讽喻为主,其得于《诗》《书》者最多,故后世莫能及。唐以后,集部之书充栋,其可存者,一代不过数人。
至其流变,不可胜言,今不具讲。但直抉根原,欲使诸生知其体要咸统于《诗》《书》,如是则知一切文学皆《诗》教、《书》教之遗,而集部之名可不立也。 上来所判,言虽简略,欲使诸生于国学得一明白概念,知六艺总摄一切学术,然后可以讲求。
譬如行路,须先有定向,知所向后,循而行之,乃有归趣。不然则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泛泛寻求,真是若涉大海,茫无津涯。吾见有人终身读书,博闻强记而不得要领,绝无受用,只成得一个书库,不能知类旁通。
如是又何益哉?复次当知讲明六艺不是空言,须求实践。今人日常生活,只是汩没在习气中,不知自己性分内本自具足一切义理。故六艺之教,不是圣人安排出来,实是性分中本具之理。《记》曰:“天尊地卑,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
”“礼者,天地之序。”“乐者,天地之和。”故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自性本具仁智,由不见,故日用不知,溺於所习,流为不仁不知。
《礼》《乐》本自粲然,不可须臾离,由于不肯率由,遂至无序不和。今人亦知人类须求合理的生活,亦曰正常生活,须知六艺之教即是人类合理的正常生活,不是偏重考古,徒资言说而于实际生活相远的事。今所举者,真是大椎轮,简略而又简略,然祭海先河,言语之序,亦不得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