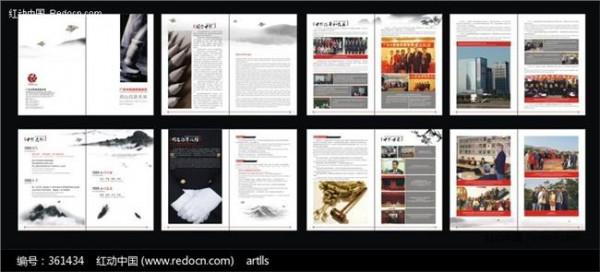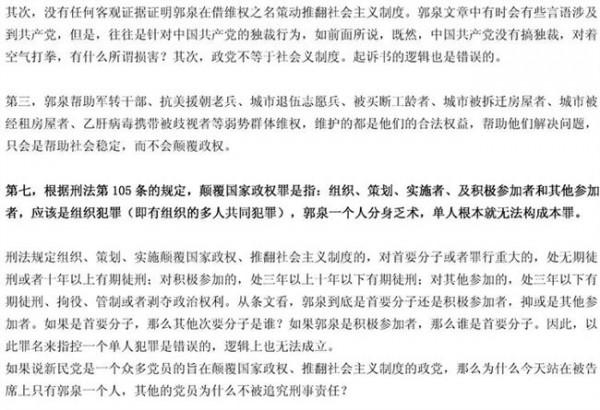邱兴隆辩护词 【素材】邱兴隆律师辩护词选登 实务专栏
受周龙斌亲属的委托并征得周龙斌本人的同意,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指派本律师担任周龙斌涉嫌爆炸罪的一审辩护人。经认真查阅起诉书与全部案卷材料,多次会见周龙斌本人并听取其意见,尤其经参与法庭主持的诉讼活动,本辩护人认为,所控周龙斌爆炸罪名不成立,其充其量只构成故意杀人罪。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本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周龙斌授意苏家利用“药功”的方法搞死周兵元;第二阶段是苏家利与陈建文共同策划爆炸过程;第三阶段是苏家利为杀人灭口而将陈建文连同周兵元一同炸死并造成其他人身、财产损害。
就所控第一阶段的基本事实,周龙斌并不否认。但对第二、三阶段,周龙斌多次供述及其当庭陈述均表明,其并不知情。而且,就第三阶段,起诉书也未对周龙斌单独做出不利指控。鉴此,所控周龙斌犯爆炸罪是否成立,关键取决于在本案第二阶段,周龙斌是否如所控一般地曾授意苏家利以爆炸的方法杀害周兵元。
起诉书指控周龙斌构成爆炸罪的基本事实有四:其一是在“药功”未成的情况下,周授意苏家利以其他方法包括爆炸杀害周兵元;其二是苏家利曾为爆炸索要经费,周龙斌也曾为此支付经费37000元;其三是案发第二天上午苏家利打电话给周龙斌索要酬金;其四是周龙斌授意周辛平分5次送了20万元酬金给苏家利。
然而,现有证据根本不足以认定以上四项所控事实的成立,因而也不足以认定周龙斌构成爆炸罪。现逐一分析如下:
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周龙斌与苏家利有过爆炸杀人的共谋
(一)周龙斌关于其同意苏家利以包括爆炸在内的方法杀害周兵元的供述作为证据既不具有合法性也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根据案卷材料,周龙斌2004年9月18日在郴州市公安局戒毒所的供述中确曾供认其同意苏家利提议的可以用枪、用炸药将周兵元搞死(侦查卷第5卷第48页)。这是最不利于周龙斌的证据之一,也是控方指控周授意苏以包括爆炸在内的任何方法杀害周兵元的主要证据之一。然而,这一供认作为证据,无论是合法性还是真实性均存在重大问题,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1、该供述因取证程序不合法而不具有作为证据的合法性
此次讯问出现在周龙斌被刑事拘留之后。而根据上述讯问笔录记载,讯问的地点为郴州市戒毒所,而并非作为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场所的看守所。根据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讯人犯,除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或者宣判外,一般应当在看守讯问室进行。
”“因侦查工作需要,提人犯出所辨认罪犯、罪证或者起赃的,必须持有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领导的批示,凭加盖看守所公章的《提讯证》或者《提票》,由二名以上办案人员提解。
”本案侦查人员在戒毒所对周龙斌的提讯既不属于辨认罪犯或罪证也不属于起赃,因此在戒毒所对周龙斌讯问笔录因讯问地点不合法而属于非法提讯所得,不具有作为证据的法律效力,依法应予以排除。
至于控方关于此次讯问合法的当庭答辩,主要是基于如此理由:《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35号)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提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填写《提讯证》,在看守所或者公安机关的工作场所进行讯问”。而根据本案专案组的说明,戒毒所是经专案组领导同意的办案场所,也就是公安机关的工作场所,因此,在戒毒所对周龙斌的讯问符合在公安机关的工作场所讯问的规定。
然而,控方的以上主张显然不能成立。一方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六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 第二十三条并不矛盾,因为《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六条关于对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之外的公安机关的工作场所的讯问,无疑是提押出看守所后始可进行。
提押出看守所,首先就得遵守《实施办法》(试行)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而对周龙斌自看守所提押至戒毒所的提讯,并非基于该条所列法定理由,而且也无公安机关领导的批示,因而明显违反了该条规定。
另一方面,即使退一步说,将《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六条与《实施办法》(试行)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理解为存在矛盾,也应该遵循《实施办法》(试行)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因为《程序规定》属于公安部的规定,即部门规章,严格说来并非法律。而《实施办法》(试行)虽然也是由公安部颁布的,但其并非单纯的部门规章而是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五十条“本条例由公安部负责解释,实施办法由公安部制定”.
《实施办法》正是根据这一授权制定与颁布的,其具有授权解释与授权立法的属性,因而与作为行政法规的《条例》本身一样具有法律效力。相应地,《实施办法》的法律效力位阶远高于《程序规定》。假设两者矛盾,自然也不得以符合作为部门规章的《程序规定》为由来否认对周龙斌在戒毒所的讯问不符合《实施办法》的规定的违法性。
既然对周龙斌在戒毒所的讯问不具有作为证据的合法性,对其理当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将其予以排除。控方将周的此次供认作为定案的依据,显然不符合证据采信的法定要求。
2、对周龙斌在戒毒所的讯问因不能排除取证方法的不合法性而无法确认具有作为证据的合法性
一方面,如上所述,在戒毒所对周龙斌的讯问属于典型的非法“提外审”,其是在没有看守所的监督的环境下进行的讯问,本身即无法排除侦查人员利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证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是合法的讯问,有何必要自看守所将周提出至远离看守人员与驻所检察人员的监督的戒毒所进行?另一方面,周龙斌当庭陈述,其当时被自看守所提出至戒毒所后,办案人员曾对其“吊绑8天8夜”,他有关供述是“受逼迫”签的字,“签字的当时他已经看不清楚”,并已经是“生不如死”,不得不在有关不利于他的笔录上签字。
控方仅仅根据办案人员自言自话的所谓没有对周刑讯逼供之类的一纸说明,即断然否定侦查人员取证方法的非法性,显然轻率。
既然对周龙斌在戒毒所的讯问无法排除侦查人员采取了非法取证的手段的可能性,那么,相应的讯问笔录作为证据的合法性自然存疑。控方将合法性存疑的讯问笔录作为定案的依据,显然有违证据的合法性的要求。
3、周龙斌在戒毒所做出的供述真伪难辨,不符合作为证据的真实性的要求
案卷中收录有周龙斌的多次讯问笔录,而供认其同意苏家利用包括爆炸在内的其他方式搞死周兵元的讯问笔录惟有在戒毒所讯问的这一次。周的除此之外的所有其他供述,均未做出如此供认,而是辩称其在“药功”不成之后“说搞不起就算了”,“没有做声就走了”,“就没要苏家利他们去搞了”,“不想搞了”,“搞不起就不要搞”等等内容(见周龙斌多处供述:如侦查卷第2卷第19页、第4卷第36、37、44页,第5卷第36页、45页等)。
这表明周龙斌已放弃杀害周兵元的意念,更遑论转而同意苏家利以包括爆炸在内的方式杀死周兵元。可见,周龙斌仅此一次的不利供述,与其他多次供述相互矛盾。控方在周的不利供认与有利供述并存,而且有利供述多于不利供认的情况下,只采信周惟一一次不利供认,显然是在没有充分根据确定其真实性的情况下,将其作为了定案的依据,因而有违证据的真实性的要求。
(二)苏家利关于周龙斌授意其以包括爆炸在内的方法杀害周兵元的供述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在周龙斌的不利供认既不具有作为证据的合法性也不具有作为证据的真实性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情况下,证明周龙斌曾授意苏家利以包括爆炸在内的方法杀害周兵元的原始证据只有苏家利的供述。然而,一方面,苏家利的这一供述与周龙斌除在戒毒所的讯问笔录之外的所有其他供述不但无法印证,而且截然对立,因而真伪难辨;另一方面,苏家利明知爆炸罪可能被处以极刑,因而不能排除其基于求生的本能而推卸责任,捏造周龙斌授意其以包括爆炸在内的方法杀害周兵元这一事实的可能性。
因此,作为本案重大利害关系人的苏家利关于周龙斌授意其以爆炸等方法杀害周兵元的供述不具有作为证据的合法性,因而也不应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邓春旺等的相关证言不具有不利于周龙斌的独立证明力
邓春旺在2004年9月11日的供述中提到在芙蓉宾馆大厅,苏家利曾告诉他,周龙斌跟他(苏家利)讲,随便用什么方法将周兵元搞死都可以(侦查卷第4卷第57、65页)。然而,邓春旺的供述所证的只是苏家利对其说周龙斌怎么说,而无法直接证明周龙斌确曾如此说过。
其作为传来证据,只有在作为原始证据的苏家利的供述真实的情况下,才具有补强苏家利的供述的证明力,而不具有单独证明周龙斌确曾授意苏家利以爆炸等其他方法杀害周兵元的证明力。然而,如前所述,作为原始证据的苏家利的供述的真实性本身无法确定,相应地,作为传来证据的邓春旺的供述之不利于周龙斌的证明力也就无从谈起。
(四)邓春旺证词与周龙斌的供述反证了周龙斌没有授意爆炸
邓春旺多次供述提到他只了解“药功”的事情,后来发生爆炸的事情他并不知道。而按照周龙斌的供述,实际上从周龙斌最后一次见过苏家利以后直到大半年后,才发生爆炸案,中间周龙斌并未联系苏家利。按照邓春旺的证词,爆炸案发生后,周龙斌对于导致周兵元死亡的爆炸感到非常吃惊,周龙斌“又问是不是苏家利搞的”,后来见了面,周龙斌“再次问我天湖爆炸案是不是苏家利搞的”(侦查卷第4卷第66页)。
也就是说,邓春旺的供述印证了周龙斌一直不知道这次爆炸案是由苏家利实施的。如果说用爆炸的方式是由周龙斌与苏家利商量好的,周龙斌不会感到如此突然和吃惊,更不会需要打电话或者面见邓春旺来求证爆炸是否苏家利所为。
(五)认定周龙斌授意爆炸不合情理
在第一次商定以“药功”的方式致死周兵元后,苏家利不但始终保持与周龙斌的联系,而且索要了经费,在“药功”未能奏效后,苏家利还面见周龙斌对其做出了解释。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爆炸案发生前长达半年时间内,苏家利既未与周龙斌有过联系,更没有索要过任何经费。
这一费解的现象的存在,不得不使人得出认定周龙斌授意爆炸不合情理的结论。因为如果爆炸确系周龙斌授意所为,就无法解释苏家利为“药功”尚且与周龙斌频繁联系、索要经费,而为爆炸这样重大行动却反而与周没有联系以及没有索要经费,同时也无法解释周龙斌为什么在那么长的时间内未做任何过问。
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周龙斌为“药功”之外的其他杀人行动支付过37000元经费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在“药功”未成的情况下,周龙斌因授意苏家利继续以包括爆炸在内的其他方法致死周兵元而分两次共计支付了苏家利37000元费用。然而,关于所控2004年6月第一次支付30000元,周龙斌没有在任何一次讯问中有过供认,其当庭陈述也对此予以断然否认。控方作为认定这一事实的依据的只有作为孤证的苏家利的供述。这显然有违只有被告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辅证的不能定案的法律规定。
至于所控第二次支付7000元,周龙斌虽不否认这一事实,但是,根据其辩解,这是其担心苏家利将“药功”之事泄露给周兵元一方才支付的,而与后来发生的爆炸无关。控方作为认定该7000元是作为以爆炸等方法致死周兵元的经费的依据的,同样只有作为孤证的苏家利的供述,因而同样有违只有被告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辅证的不能定案的法律规定。
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爆炸案发生后苏家利与周龙斌有过直接联系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苏家利在案发后给周龙斌打电话索要过酬金。然而,苏家利多次口供并未提及此事,而只是2004年9月12日在桂阳党校所为的供述中提到“2003年12月24日上午,我用公用电话打电话给周龙斌,讲周兵元被炸死了,他说知道了然后挂了电话,没有讲其他的。
”(侦查卷第5卷第26页,第17卷第147页)。然而,周龙斌的全部供述中并没有他在爆炸发生后接到过苏家利的电话的任何供认,其当庭陈述更是对此断然否定。
而且,案卷材料中也无关于这次公用电话打电话给周龙斌的通话记录之类书证辅证此事。因此,撇开苏家利的前列供述因系在桂阳党校提外审所获得而属于应予排除的非法证据不说,其也只属孤证。控方据此指控苏家利在案发后给周龙斌打电话索要过酬金,显然有违只有被告口供不得定案的法律规定。
四、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周龙斌授意周辛平支付了苏家利酬金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爆炸发生后,周龙斌曾授意周辛平分5次共计支付了苏家利酬金20万元。然而,现有证据同样根本不足以证明这一所控事实的成立。
其一,周龙斌无论是在多次讯问笔录还是在当庭陈述中,不但矢口否认其曾让周辛平支付苏家利酬金,而且,始终辩称其对周辛平是否支付苏家利钱以及给多少钱一无所知。
其二,周辛平虽在原有的供述中供称曾送过一次钱,但是一方面,根据医学鉴定,周辛平属于中度智力减退之人,即使不认定其依法不具有责任能力,其供述的真实性也应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即使是周辛平本人的各次供述也自相矛盾,即其时而供称去送给一个军用挎包给一个不认识的人,里面有1-2万元钱,时而供称其只去送过一个军用挎包,但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钱,而其当庭陈述则是其根本没有去送过钱。
因此,周辛平的供述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应作为证据。
其三,在送钱的次数上,周辛平、邓春旺与苏家利的供述无法互相印证。即使根据周辛平的不利供述,其也只记得送过一次钱;邓春旺供称的是陪同周辛平送过4次钱;只有苏家利本人供称周辛平送过5次钱。既然如此,周辛平究竟是1次、4次还是5次送钱给苏家利便是一个无法确定的事实。起诉书指控周辛平在周龙斌授意下分5次送钱给苏家利,显然依据的只是作为孤证的苏家利本人的供述。
其四,所控所谓酬金金额无法确定。即使根据周辛平的最不利供述,其也只知道第一次送的可能是1-2万元;即使根据邓春旺的不利供述,其也只知道第一送了2万元,后来的3次分别与总共送了多少,其不知情;只有苏家利本人供称爆炸发生后共计收到的是20万元。起诉书指控周辛平送钱的总额为20万元,同样显然依据的只是作为孤证的苏家利本人的供述。
其五,有关苏家利赃款即所谓酬金的去向统计表明,经苏之手支配的金额总计不到5万元。而根据起诉书的指控,周龙斌本人为“药功”及其在爆炸发生经由周辛平支付给苏家利的费用与酬金多达25.7万元。这等于说,苏家利的赃款有20万元左右下落不明,而这恰恰反证了所谓爆炸发生后支付的20万元可能纯属子虚乌有。否则难以解释如此大额的赃款为何会查不清去向。
其六,也是至为重要的是,即使退一万步,强行认定周辛平曾送钱给苏家利,现有证据也根本无法证明其是基于周龙斌的授意而送的钱。因为只有周龙斌与周辛平的供述可以证明周龙斌是否授意周辛平送钱,而周龙斌始终否认其曾授意周辛平送钱,即使采信周辛平的最不利供述,其关于周龙斌曾让其送钱的指证也系孤证,不足以成为认定周龙斌授意其送钱的充分依据,更何况其供述的真实性如前所述的无法确定呢?
鉴于所控全部4项与爆炸有关的事实,如上所述的均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无法认定,而控方关于周龙斌构成爆炸罪的指控以该4项事实成立为前提,相应地,所控周龙斌参与爆炸的整个事实自然也因前提不成立而无法成立,所控周龙斌爆炸罪名不成立也就是一个自然而必然的结论。
五、周龙斌充其量只能构成故意杀人罪
在所控爆炸罪名如前所述的不成立的情况下,周龙斌是否应就本案的第一阶段即授意苏家利去以“药功”的方式致死周兵元承担刑事责任,成为对周龙斌是否应该定罪量刑的关键。鉴于案卷中并无关于“药功”的具体含意的证据,首先得对“药功”是否可能致死人有一明确的认识。
如果将“药功”理解为当地农村流行的一种巫术,则其与迷信无异,所谓以“药功”杀人便属刑法理论上所言的“迷信犯”,当属绝对不能犯的范畴,对周龙斌自然也就应当宣告无罪。
但是,如果“药功”系以药物功击他人,致其慢性死亡,则以此等方法杀人具有致人死亡的现实可能性,依法应当承担杀人罪责。相应地,周龙斌授意他人寻找“药功师傅”、为“药功”支付经费等便属于为杀人创造条件的行为,对其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预备,并依法以预备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应该郑重指出的是,即使退一万步,假定所控事实全部成立,对周龙斌也应当认定为杀人罪,而不得定性为爆炸罪。因为即使根据起诉书,周龙斌也只有以爆炸的方法杀死作为特定的人的周兵元的故意,而无以爆炸的方法造成不特定的人身与财产损害的故意,其犯罪故意不包括危害公共安全的内容,因而不符合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一的爆炸罪的本质特征。
事实上,即使根据指控,周龙斌也没有参与苏家利和陈建文就爆炸所为的共谋,对后者所议定的爆炸方式、爆炸地点等全然不知,更无法预料苏家利会为杀人灭口而将陈建文与周兵元一同炸死。
因此,即使认定周龙斌有以包括爆炸在内的方法杀害周兵元的故意,其也因只有杀人的故意而无危害公共安全的爆炸的故意而只构成杀人罪,至于随后发生的爆炸事件,属于苏家利与陈建文以及苏家利个人超出周龙斌的杀人故意而引发的,亦即刑法理论上所谓的实行过限行为,对于由此引发的除周兵元死亡之外的其他人身与财产损害尤其是陈建文的死亡,周龙斌不应承担任何刑事责任。
综上,所控周龙斌爆炸的事实严重不清、证据明显不足,对其不应以爆炸罪而充其量只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恳请法庭充分考虑、慎重采纳以上辩护意见,依法对周龙斌做出合理合法而实事求是的判决。
此致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邱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