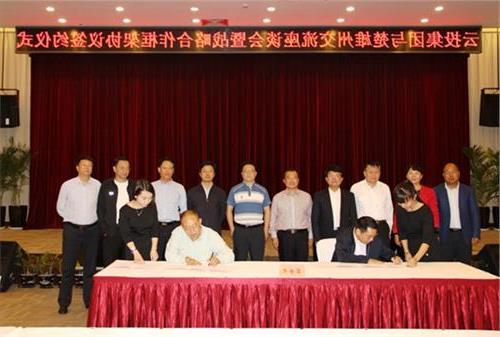张东荪为什么投反对票 萧象:特立独行——投反对票的张东荪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活跃在中国思想文化与政治社会领域众多名动一时、影响广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张东荪无疑是独具个性、色彩斑斓而引人注目的一位。这不仅是在国共和谈破裂、国家前途未卜的危难时机,他提出调合两党纷争、建立“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给后人读史留下一方可以想像的空间,也不仅是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却又非属“亲共的左派”这一不偏不倚的独立角色,以及这一独立角色使他得以因缘际会,在国共之间充当使者,居中斡旋,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潮流中,在摧枯拉朽般改朝换代的历史旋转舞台上,他那颇具戏剧性的身份变化,以及这变化所带来的命运沉浮,尤让人感慨而叹惜——共和国开国之际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接着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不久便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以“出卖情报”“叛国罪行”被解除职务,打入另册,在公众视线中销声匿迹。
张东荪是49年以后第一个罹罪的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被伟大领袖斥为“坏分子”而遭贬黜的学者。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人们总难免心有疑惑:一位在抗战中为掩护进步学生被日军逮捕入狱而威武不屈的爱国教授,一位在内战中为保全五朝古都文明,使平民百姓免遭兵燹祸害而做出贡献的民主志士,何以转眼间就变为千夫所指的坏分子与叛国者呢?
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身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对五十年代曾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的同事如今的中科院院士张宗烨也就是张东荪的女儿有过这样一段说话:
“这么些年都没告诉你,当时我们可是大大地保护了你。你到所里一直是内部使用。……我们给你说了好多好话。……刚刚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选举毛泽东当主席……结果这里面居然有一张反对票。当时他们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干的。虽然不能肯定,但他们猜除了他不会有别人。”“那时刚刚解放呀,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有人投反对票——敌人这么快就钻到这么小的圈子里边来了。”
何说的是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投票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经过三年势如破竹的解放战争、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革命奋斗,中国共产党终于从偏僻的乡村走进了象征宰制国家权力的紫禁城。作为党的领袖,革命的胜利者,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一样在这开国立朝的欢腾时刻自有一种江山一定、万方来朝的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用分说是众望所归。选举结果,毛泽东以575票高票当选,只差一票就是满票。对这缺少的一票,代表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毛主席自己没投自己,是一种伟大的谦逊表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并没有像代表们想象的那样谦逊,他把票投给了自己。投反对票的另有其人——他就是燕大教授、刚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张东荪。
几十年过去,这一张反对票曾经掀起怎样的惊天波澜,又是怎样的被猜测、追查、最后锁定投票人,对今天的人们仍具有相当的吸引,但更具吸引且有追问价值的当是,张东荪何以要投反对票?他是怎样的心理动机?在毛泽东率领中共打下江山,威望如日中天之时,在张自己充当和平使者又亲往西柏坡,与毛有过晤面之后,在他还刚刚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际,他为什么做出与与众不同的选择?以常人逻辑,他应该感恩戴德,投桃报李,却为什么偏偏不吃敬酒,要逆水行舟?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个党人或党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他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他喜欢独来独往,特立独行,而不受任何拘束的。”
这是民国报人、张东荪老友的俞颂华四十年代对张的评说,也是帮助解读东荪张投反对票的一扇视窗。稍对张东荪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言行表现做一浏览,就不难得出这一印象:张东荪的确是一位“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的“特立独行”者。例如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组建国民党,凡在南京政府任过事的一律作为党员,张亦名入其列,其时国民党“声光一跃千丈”,而张自己非但未加承认,且抽身远避。又如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南北对峙,“他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词抨击,又同时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既认为“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又对两派均表失望,寄望于“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再如为坚持“权力制衡”的政治理念,拒绝参加没有中共参加的“国民大会”,不惜与情同手足的张君劢分道扬镳。至于在国共纷争中独立不倚,主张“中间路线”更是名噪一时的众所周知。
这种不趋炎附势、不投机取巧,唯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行为其实不独表现在张东荪一人之身上,这是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整体的自觉追求和人格理想。看看同时期的那些响当当的人文知识分子代表,胡适、傅斯年、梁漱溟、罗隆基、张奚若等等,面对政治社会思想文化诸多重大问题,那个不是秉持自由的理念,基于民主的立场,独抒己见,勇于发声,以正义为原则,以批评为能事,以思想独立为标榜,以真理服膺为高尚,表现出现代知识人卓然独立的伟岸。只是这种宝贵而普遍的如同空气一般流动在那个时代的独立人格精神,随着后来的江山易帜、思想一统而走向式微,以至不识“自由”、“独立”为何物的今人在历史故事中猛一见之而兴奋莫名。
张东荪是自由主义的,对国民党一党专制深恶痛绝,一度被毛泽东目为资产阶级的“左派”。他又是民主主义的,对共产主义持反对态度,但对共产党人的救国主张和抗日行为又表示赞同和同情。他早期留学日本,政治理念认同英美,同时怀有浓厚而传统的天下情怀和忧患意识。因此,在炮火连天兵临城下之际,他被选为中立的和平使者,并接受邀请前往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访问。
然而,正是这次访问令他心中因为北平和平解放献力而刚刚升起的关于国家前途的一些兴奋遭当头棒喝。关于国家前景,张东荪一向怀想的是,“在政治方面比较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而对外关系则在美苏两个超级强国之间抱持中立的平衡。很难说这种张东荪在书斋中观天下念苍生而提出的政治设想,与中共重庆《新华日报》报头上所经常刊登的民主自由的主张完全是南辕北辙,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有此行西柏坡了。
西柏坡之行诚然是接受毛泽东邀请,有对即将夺取江山的中共作进一步了解的愿望,又何尝没有借机说项,顺势向毛鼓动张氏“中间路线”的意图。所以,兴冲冲的张东荪在西柏坡撞上了决意向苏联“一边倒”的中共领袖毛泽东这面南墙,实出张的意料。西柏坡之行张东荪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仅从归来对家人所言“话不投机”四字就可看出他心情的抑郁。这位政治学出身、对政治理论有着精深研究、对政治现实有着敏锐观察的燕大教授,不会不清楚苏联斯大林政治的实质,因此,当毛泽东托出中国取象苏联的棋盘时,张东荪生出心灰意冷的失望,则不难想见。
此事发生在1949年1月中下旬。半年之后,要他选举刚给他心里留下阴影和失望的人为未来国家的最高领导,他会怎样地选择,也就不难推知矣!
想来张东荪不是第一次参加重大选举,在他看来,投反对票不过是正常行使自己被赋予的权利而已,所以,此事在其一生中没有对包括家人在内的任何人有过任何提及(当选人民政府委员,也丝毫不会影响他选举的心态,因为做官对他不是吸引,也就没有感激与投报之说,在西柏坡曾他婉拒过北大校长的许愿,何况他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自己形成的主见和看法,不会受任何外来的干扰)。只不过,这一回他错了,他没想到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人们选举的对象已不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蒋介石,而是雄视九州睥睨天下的毛泽东。就在他投下这一票的这一天起,他的命运注定因此而改变。
正如何祚庥所言“没有想到会有人投反对票——敌人这么快就钻到这么小的圈子里边来了。”既然投反对票被认为是敌人,当然就要把他拿下,就要进行控制。于是公安机关奉旨立案,采取秘密措施,暗中进行调查。这个有着悠久人治而非法治历史的国度,一出 “何患无辞”的“欲加之罪”传统剧遂再度上演。一举一动“在如来佛手掌之中”的张东荪,被卷入一件间谍案中,被认定“出卖情报”,犯下“叛国罪行”,而淡出公共视线。
这个历经清、民两朝、一向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者,绝对不会想到才入共和就为自己的一次投票选择付出代价。屈指数来,他与中共相互间的交往实在不算短暂,不说中共建立之初双方即有的接触与“社会主义论战”的交手,也不说张与中共第一任领袖陈独秀的交知,就从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张率先撰文予以欢呼评论算起,武汉与周恩来的晤谈,北平对中共地下党员的掩护,重庆与中共代表团的切磋,以至于充当和平使者,前后凡十五六年,其间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彼此的政治理念、言行主张与行事方式,岂不早已了然于胸?
事实证明,不仅中共并不了解真正的张东荪,张东荪也未必了解真实的中共。中共看到的是作为燕大著名教授和民盟常委这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这一政治态度的张东荪,而没看到自由主义者的和基于民主政治理念针对任何一党专制的张东荪;只看到不卑不亢、可以不买委员长账的张东荪,没看到宠辱不惊、同样可以不领主席情的张东荪。同样,张东荪对中共也认识肤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知中共的民主主张之其一,不知民主主张为统战口号之其二;只知中共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之其一,不知反倒彼一党专制而再起此一党专制之其二。概言之,中共没看出不为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张东荪,张东荪也没看出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中共。
不过,话说回来,从另一角度看,中共未必不清楚张东荪的政治倾向,不知道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只是基于建国之初广纳贤良、予世人以新政府为民主政府印象的统战考量,中共需要招纳这么一般有一定群众基础与社会影响力的民主人士参与政府工作,只要他们归顺、赞同、拥护新政府,对其先前的言论主张,可以既往不咎,过而不问。但是,如果这般人物不识时务,我行我素,一如既往,把昨天的行为带入今天的社会,把昨天的是非标准视为今天的是非标准,以为昨天可以行而无妨的今天照样可以行而无事,那么,对不起,就没有客气可讲,除了清除出局,还得新账旧账一起算,而且变本加厉地算。所以,在接踵而至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所有张东荪四九年前的言论被底朝天地翻了过遍,被当做反动思想受尽批判,是顺理成章的秋后算账。
“中国之运兴也,不在有万能之政府,而在有健全自由之社会,而健全自由之社会,唯有人民之人格优秀以成之。此优秀之人格,苟政府去其压制,使社会得以自由竞争,因而自由淘汰,则可养成也。易言之,中国之存亡,唯在人民人格之充实与健全,而此人格则有撤去干涉而自由竞争,即得之矣。于诸自由之中,尤以思想自由及思想竞争为最也。”
这是张东荪早年的言论。张是知行合一的,他投反对票,不过就是一种他自己所倡导的这种“人格之充实与健全”实践的延续。在知道了张东荪投了反对票事相的今天,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入罪”落难,与其说是因“叛国罪行”而受罚,实在是因“独立人格”而挨整,因“自由思想”而被肃。且目的指向明确,意味周深绵长,这就是借助于罚一儆百,由此及彼,由点到面,开始知识分子被脱胎换骨与洗心革面的思想改造之第一步,最终达致社会彻底改造这一共产主义宏伟之蓝图。
张东荪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叶,一叶知秋,在其之后,那些无论同情或批判过张的同仁们,如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叶笃义等等,以及遍及神州无以数计的知识人,如秋风落叶,在随之而来接连不断的运动中,纷纷凋零飘落,无不与张一样落得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宿命。
张东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生活之初没受太大影响,这固然有张案本身是“欲加之罪”这一因素裁量,也未必不是共和之初施仁政安天下策略的必要施行。随着政权的稳固和秩序的安定,权力膨胀至肆无忌惮,仁政逐渐走向暴政。风烛残年的张东荪也处境日蹙,每况愈下,挨至文革终于关进监狱,清算的仍是近二十年前因“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犯下罪孽的这本旧账。
“还是我对”,张在狱中对亲属这样说。此时已是1973年,中美关系开始改善,他说的是当初“一边倒”的事。可是他为此已付出了包括失去自由在内的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