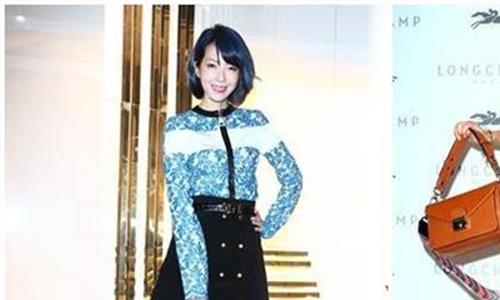反对教材恶意抵触同性恋 真爱不分性别同性恋没有错

回想起两年前,我还是那个在图书馆看到教材说同性恋是精神疾病后胆战心惊的少女(捂脸…)。然而不知是什么力量,推着我向前走了那么远,已超出自己曾经对于生活的想象。2015年,我第一次鼓起勇气走向街头举牌来表达自己的态度,第一次走向教育厅的信访办公室递交举报信,第一次走进法院的立案大厅排队等候并在法院门口扬彩虹旗;也第一次并成为了第一个与教育部官员们坐在法庭上谈同性恋问题的同志……这一切就那么确确实实发生在我的生活中,真实而激动人心。

是什么让我踏出那一步,又成为现在的自己?可能有对错误及污名的气愤,有对自己没有“错”和“病”的坚信,有骨子里性格的反叛,有对不公和霸权的愤怒。

2014年中,我在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GLCAC)参与调查错误教科书负面影响调查。一位被访谈的某高校医学生告诉我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却至今仍然希望科技可以发展到改变他的性取向,让他变得和绝大多人那样“正常”。同年,他在学校的医学教材上看到同性恋被描述为变态和艾滋病的高危人群,这加重了他的抑郁症。他甚至不敢和自己的抑郁症医生提到他是同性恋的事实。

那是怎样的一种恐惧,我无法感受到。只是通过他身边的朋友多次辗转联系,他才愿意接受电话访谈,我强烈感受到那份压抑。过去的两年,当我站出来之后,越来越多的朋友向我倾诉他们在校园里被欺凌、老师在课堂上发表“恐同”言论的经历。我越来越明白,我们所做的远比我们应该做的少。将愤怒、叛逆转化为爱和非暴力的行动去推动改变,这也许才是出路。

正是如此,2014年的教科书污名化调查结束后,我仍继续参与这方面的工作。这一路上一点也不轻松。我纠结过,迟疑过。在担心对父母的伤害和“一定要做”的迟疑间,最终我还是迈出起诉教育部的那一步。该来的终要来。而这也是我开始为人所知的开端。死磕“教科书同性恋去污名化”,这当初简单而执着的想法,想着想着就成真了,做着做着就坚持下来了。

当然,紧随而来的是,第一次被校方约谈,第一次被“威胁”,第一次遇到“恐同”教师的当面指责,第一次在性取向问题上直面家人,第一次看到母亲那般无力,第一次被带去医院“就诊”……

过去的一年,我便是在这样的力量与冲突下前行。当看到妈妈的眼泪和无力时,我也变得脆弱起来。当我看到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傲慢的回复和收到天河法院“不予立案”的通知时,不知何去何从的迷茫感和压抑涌上心头。

当我收到新闻总局“不归我管”的电话回复时,半天说不出话来。与教科书狠狠死磕的这两年,好像改变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能改变。曾经好几次内心的压抑不断积累,常常好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停留、歇息,或者静静地一哭为快。然而事情一茬接一茬,学习作业一轮接一轮,由不得我反应过来又要“战斗”了。

每当我感到无力时,被好基友们的行动温暖到。当我看到华中科技大学的朋友在调查图书馆错误教材并要求下架举行校内呼吁时、当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崔乐老师公开写文章“出柜撑秋白状告教育部”时,当有记者朋友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时,当我的微信公众后台收到各路好心人的关心和鼓励时,我又充满了力量和勇气。你们的这些一举一动,都在提醒我同行的人一直都在。

你们知道吗,我在北京中院与教育部“庭前对话”前身边好几位朋友收到了妈妈“感谢你们一直陪着她”的短信和《朋友》这首歌。那一刻,我的心都化了。正是朋友的支持和妈妈逐渐的理解,让我看到一切都在改变。虽然有时改变来得很慢,虽然有时前进一步退三步,我总是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过去的一年,我就是在不断“碰壁”、冲突和被温暖、鼓励的张力中前进,走到今天。我想,这是所有想参与改变,呼唤正义的行动者的共同心境吧。

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一些人。2015年我组建了一支小团队。飞飞、楠楠、小新、情书、仑仑、忽忽,她们在我“被出柜”最灰暗的时候替我分担工作,每个人平时都忙得晕天暗地还帮我管理平台、写东西、邮寄资料、做街头行动,每周从很偏远的地方赶车过来只为讨论半小时的行动进展。

现在,飞飞与楠在工作、生活与参与同志公益的纠缠中逐渐掌握了方向,仑仑的毕业论文打算写写青少年同志在校园政策权益保障上的现状。前段时间,小新妹纸组建了广州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彩虹社,她很久之前说过,她的梦想是在毕业之前成立属于广大的彩虹社。感谢在行动中结识的这群亲密战友们,秋白身后其实有很多个“秋白”在付出。

2014年,少有媒体关注教科书中的同性恋污名问题,到2015年关于秋白和教科书的媒体原创报道已超过了400多篇,从几十个到几万人在持续关注这一切。这难道不是改变么?

2015年,我与教育部的对话被媒体和朋友称为“中国LGBT群体与政府部门首次公开平等地对话”。就在今天,媒体刚刚报道“因教材污名同性恋起诉教育部及其类似案件”入选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办的“2015中国十大宪法事例”。同性恋群体通过法律和非暴力的社会行动来维护权益被认定为宪法事件,这难道不是改变吗?

前段时间,暨大一名抑郁症学生因性取向担心无法为父母传宗接代等精神压力自杀后,又再次爆出由暨南大学心理健康中心编写,暨大出版社出版的2013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材,描述“同性恋是性指向障碍”。之后,好几位朋友来信告诉我他们愿意成为“当事人”公开起诉暨南大学出版社。这难道不是改变吗?
但如果我们将“改变”设定在今年教育部承诺什么,或是错误的教材一年内全部消失,这些期待无疑是要落空了。

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那一刻,全世界欢欣鼓舞,我们也许在叹息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可权利从来不是等来的,自1969年美国石墙暴动发生后,千千万万性少数开始站出来,为争取ta们的合法权益上街呼喊。当宗教活动领导人Anita Bryant号召全国性运动来阻止同性恋维权时ta们愤怒呐喊,当警察在街头暴打同性恋时ta们游行示威,当美国不允许同性恋加入部队时ta们举牌抗议。

(Harvey Milk,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选任政府职位的公开同性恋倾向的政治人物。他为了争取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而选择从政,但最终被保守派刺杀。他说,假如子弹穿过我的头,也让它打破每一扇紧闭的柜门。)

美国人民用鲜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坚持抗争50年,才换来今天全美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我在教科书去污名化议题上坚持的这两年,与美国五十年同运平权历史相比只是一个小零头,我们有理由不坚持吗?今天争取的每一点进步,都在为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做铺垫。而且哪怕某一天我朝允许同性结婚也不意味着所有歧视与不公就能够消除,平权没有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