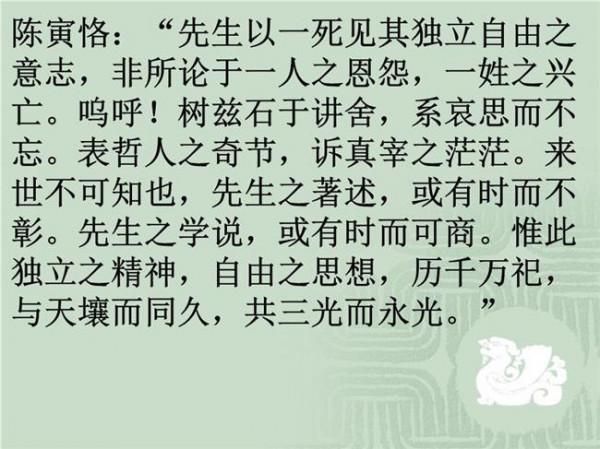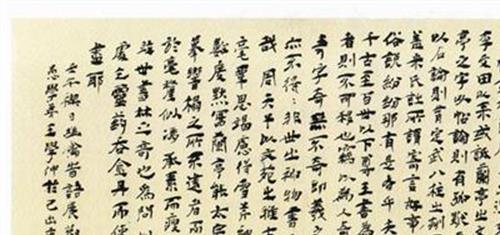张岚红楼梦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佛家底蕴
1904年,王国维发表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篇研究古典小说的论文——《红楼梦评论》。这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深远影响的跨文化研究个案。王国维之写作《红楼梦评论》诚有多方面因素,但与他究心佛学,留恋佛境,由此探索人生真义有密切之关系。至今对《红楼梦评论》尚未有专文从佛教的角度加以阐释,本文对此聊陈管见,敬祈方家教正。
一、王国维早年的人生困惑与佛教情结
王国维并没有专门研究佛教的论文,但这并不说明他对佛教与宗教没有研究。真正的学术大师多不喜自炫博学,率尔操觚。王国维亦然。钱钟书尝赞王国维“博极群书”,“深藏若虚”。①这可以说是对王国维学术风格的经典概括。王国维之佛教与宗教修养,也宜作如是观。
王国维对佛教与宗教的论述散见于他的有关论着中,如1905年发表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云:“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
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同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而稍带出能动之性质者也。
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②如此高屋建瓴纵论佛教与中国古代思想嬗变轨迹,既简要,又甚为精当,信是大家风采。特别是他把西洋思想看成“第二之佛教”,更是别具会心,非全局在胸,目光巨大,会通佛教与中西思想,决不能下此断语。
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将西洋思想看成“第二之佛教”,实说明他对东来之佛教的特别青睐。王国维同主张学无中西,然于佛教则实不无偏嗜。
王国维在总体上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1906年,王国维作《去毒篇》,论述“宗教之所以不可废”,这主要是因为宗教能够“偿现世之失望以来世之希望,慰此岸之苦痛以彼岸之快乐”,而此实即佛教之精义。
王国维并非不知“今日之佛教已达腐败之极点”,基督教亦然,但它们能带给国民“希望”与“慰藉”,故宗教不宜废。在该文中他还阐述宗教与美术的关系。他说:“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也”,“宗教之慰藉,理想的,而美术之慰藉,现实的也。
而美术之慰籍中,尤以文学为大”。王围维早年对宗教的认识,是与人生、与美术如文学等联系在一起来认识的。王国维并不信宗教,他之看重宗教与美术如文学,是因为它们有“慰藉”的功用。在王国维那里,美术如文学,就有宗教化或者说佛教化的倾向。
早年王国维是个多思多虑、深于忧患的人。这除了他所处的生活环境之外,与他的天性及身体的健康状况颇有关系。他在《静庵文集》之《自序(一)》中,回顾辛丑(1901年)后从日本回来以后的治学经历时说:“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
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其《欲觅》诗则云:“欲觅吾心已自难,更从何处 把心安。诗缘病辍弥无赖,忧与生来讵有端?”王国维有一段时间醉心于西方哲学,其根本的目的乃在于解决“人生之问题”。
他在《静庵文集自序》中就说自己“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在这 篇很短的自序中,他对叔本华的其他学说不作任何评判,“然于其人生哲学观”,“未尝不心怡而神释”。
这说明早年王国维,的确一直思考着人生的真义,因为找不到满意的答案,遂走进了形而上的困惑,即他后来在《红楼梦评论》中对叔本华的哲学提出了绝大的疑问,也是他追问人生的一种重要思想标记。
王国维对人生的困惑,从他早年的诗词作品中也可以找到显着的精神印记。他企求解脱。这种人生烦恼的最重要的途径,乃是时时向佛家境地攀缘。前述王国维论佛教与宗教的文字,固然是写于《红楼梦评论》发表之后的1905、1906年,但他潜心佛学、企羡佛境其实早就开始了。
如1901年,王国维作《杂诗》,中云:“侧身天地苦拘挛,姑射神人未可攀”,“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即表明此种精神祈向。从王国维早年的思想轨迹看,《红楼梦评论》是他上述诗作精神祈向的自然延伸与继续发展。
概括地说,述说人生的苦痛与企求此种苦痛之解脱及不能,乃是早年王国维内心生活的基本精神结构。我们仍以其诗词作品为证。前者如:“我生三十载,役役苦不平”(《端居》);“苦觉秋风欺病骨,不堪宵梦续尘劳”(《尘劳》);“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游通州湖心亭》);“蓬莱只合今时浅,哀乐偏于我辈深”(《登狼山支云塔》);“因病废书增寂寞,强颜入世苦支离”(《病中即事》);“网罟一朝作,鱼鸟失宁居”(《偶成二首》之一)。
后者如:“欢场只是增萧瑟,人海何由慰寂寥”(《拼飞》);“君看岭外嚣尘上,讵有吾侪息影区?”(《重游狼山寺》);“江上痴云犹易散,胸中妄念苦难除” (《五月十五夜坐雨赋此》);“蝉蜕人间世,兀然人泥洹”(《偶成二首》之一);“啕濡视遗卵,怡然即泥滓”(《蚕》);“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书古书中故纸》);“我力既云痛,哲人倘见度。
瞻望弗可及,求之缣与素”(《来日二首》);“拟随桑户游方外,未免杨朱泣路歧”(《病中即事》)。
如此等等,不胜繁举。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的诗句中颇多佛教词汇,如前举“乐土”、“何乡”即是。又“妄念”、“度”、“泥洹”、“泥滓”、“桑户”、“人间”等无不是。
“妄念”、“度”是佛教词语容易理解。“泥洹”、“桑门”,乃梵文Sramana的异译,专指佛教僧 侣,泛指出家者。“人间”一词在王国维那里也多有佛教色彩,因为在他看来,人间与地狱是没有差别的。
此下有申说。如果我们通读王国维的全部着述,会发现更多这样的佛教词汇。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显示王国维的博学,如他的诗作中如此好用佛教语词,实昭示着他企求人生苦痛的解脱。故王国维未必真信佛教,但佛家出家、祈盼解脱人生苦难之思想,乃是早年王国维挥之不去的情结。
王国维诗作中最典型的表达他早年此种基本精神结构的应该是《红楼梦评论》中所引用的一首《平生》诗:“生平颇忆挈卢敖,东过蓬莱浴海涛。何处云中闻犬吠,至今湖畔尚乌号。人间地狱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终古众生无度日,世尊只合老尘嚣。
”这便是一首有关人生痛苦及企求解脱而实不能的诗歌,充满佛家气息,与前所述王国维诗歌精神命脉相接通。“人间”、“地狱”各为佛教五道之一。所谓“五道”,乃是佛教所说的众生根据其生前善恶行为有五种轮回转生的趋向,这就是:地狱、饿鬼、畜生、人、天。
王国维视人间为地狱,两者了无差异,而人死去也不得解脱、超度,所谓“终古众生无度日”是也,这包括释迦牟尼在内。世尊乃是对释迦牟尼的尊称。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引用这首诗歌是想说明“释迦、基督自身之解脱与否,也尚在不可知之数”。
这是《红楼梦评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这可以说也是前述《病中即事》——较其《平生》诗略早——诗句“拟随桑户游方外,未免杨朱泣路歧”的另一种表述。
可见在王国维评论《红楼梦》以前,他早有了《红楼梦评论》中的许多看法——《红楼梦评论》不过是它们的全面展开而已。因为这种精神命脉上的重大关联,王国维的这首诗,也可以说是《红楼梦评论》之具佛家底蕴的重要内证之一。
二、“天眼"中的人生与《红楼梦》
在王国维早年的心灵史上,《红楼梦评论》乃是其上述人生苦痛与企求此种苦痛之解脱及不能的这种精神结构的一次全方位求证。如果我们不了解王国维早年的人生困惑与佛教情结,很容易认为他写《红楼梦评论》仅仅是受了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启发。
叔本华此种人生哲学对王国维研究《红楼梦》的确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在《静安文集》之《自序》中也说,这篇论文的“立脚地”“全在叔氏”。但事实上正如俞晓红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该文并非全以叔氏理论为依据”,①王国维早有别的精神养料;《红楼梦评论》一开始就引用了老子与庄子关于人生忧患与劳苦的话,说明老庄哲学对王国维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最重要的乃是佛家有关人生苦痛与解脱之义谛;即王国维撰写这篇论文最初的精神触机,乃与佛教有着极大之关联。
前引钱钟书先生语谓王国维“博极群书”,“深藏若虚”,则佛家义谛乃是这篇论文“深藏若虚”的幽灵。鲁迅先生在《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中曾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
”②王国维若没有早就有的对佛家人生观的体察与默认,即佛家人生哲学这根“弦索”,他所说的西洋思想此“第二之佛教”如叔本华这种人生哲学,就不会在他那里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概乎言之,王国维是用佛家眼光或者说“天眼”去看待人生与艺术的。
“天眼”也是个佛教词汇,“天眼通”乃佛教所说的五“神通”之一。后秦鸠摩罗什译佛教论书《大智度论》卷五有云:“于眼得色界四大造清静色,是名天眼。天眼所见,自地及下地六道中众生诸物,若近若远,若粗若细诸色,无不能照。
”王国维在其着述中颇喜欢用“天眼”一词。如其《浣溪沙》词云:“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其《红楼梦评论》中云:“若开天眼而观之(按:指贾宝玉),则彼同可谓干父之蛊者也。”而王国维所作《叔本华像赞》,盛赞 他“天眼所观,万物一身”。
而一般人的眼乃“肉眼”,其《来日诗二首》中云:“吾侪皆肉眼。”如此等等,可见,王国维审视人生与世上万象不作一般观察,而每执佛家视野。王国维的确主要是用“天眼”看待人生与艺术,包括《红楼梦》。
这就是说,王国维实想通过解读《红楼梦》解决如何慰藉人类现世失望,如《红楼梦评论》第二章中所谓“苦海之流”,亦即人生此岸之苦痛,而企求终解脱此种痛苦,亦如此文第二章所说“引磴彼岸”,此非佛家根本问题而何?《红楼梦评论》之具佛家底蕴,其最基本的学理依据即在此。
诚然,王国维在文中也偶然提及其他宗教,如他说“印度之婆罗门教及佛教,希伯来之基督教,皆以解脱为唯一之宗旨”,但事实上印度婆罗门教与基督教所说的“解脱”与佛教所说的是不一样的。
婆罗门教之“解脱”指轮回业报,也即轮回解脱,而基督教之所谓“解脱”,主要是指“救赎”,即基督如何拯救世人。显然,《红楼梦评论》没有在这方面展开阐述,其立意并不在此。从严格的宗教意义上说,“解脱”是佛教词汇,而非印度之婆罗门教与基督教用语。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所用“解脱”一词,正是佛教核心词汇,而非泛指。
与此相关,即以所涉及的基督教语词极少——婆罗门教是更不用说,而佛教甚多而论,也可见佛教在王国维心目中的地位远非基督教 所能比。《红楼梦评论》所见基督教词汇唯“上帝”等二三词而已,而佛教词汇则甚众,如“地 狱”、“人间地狱”、“拔舌地狱”、“示寂”、“涅盘”、“绮语”、“梦幻泡影”、“苦海”、“彼岸”、“解脱”、“恶魔”、“大士”、“执着”、“精进”、“挂碍”、“菩提萨缍”、“《佛国记》”、“若不尽度众生,誓不成佛”,如此等等。
海德格尔曾说,语言乃是存在的家园。联系前引诗作,王国维 之好用佛教语词,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精神“家园”中“佛”之存在与常在,《红楼梦评论》是有深深的“佛”的印记。
而王国维之所以选择《红楼梦》作为评论的对象,这是因为,从表面看,《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其他古典小说不同,的确有浓重的佛家色空与虚无的人生观念,而贾宝玉最后也确乎“解脱”了人生的苦痛出家去了。《红楼梦评论》第二章有云:“读者观自九十八回以至百二十回之事实,其(按:指贾宝玉)解脱之行程,精进之历史,明了真切何如哉!
”佛教论书《成实论》卷一八云:“精进者,行者若行正勤,断不善法,修集善法,是中勤行,故名精进。”王国维当时还没有认识到《红楼梦》后四十回并非曹雪芹所作,但用“解脱”、“精进”这样典型的佛教词汇描写《红楼梦》主人公的精神轨迹,说明他确乎专注于用佛家眼光审视这部书的价值。
《红楼梦评论》第一章为《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王国维认为生活的本质为“欲”,而“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一欲既偿,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因此,人生在本质上是痛苦的。
他进一步引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发挥此说:“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厌倦之间者也,夫厌倦同可视为苦痛之一种”;甚至认同这种实来自叔本华的颇为荒谬的观点:“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盛故也”,其意无非是证说人生之本质为苦痛。
因此,他总结性地说《叔本华像赞》,中有“吠陀之教,施于佛屠”之语。钱钟书《谈艺录》谈到叔本华时说他“好诵 说天竺古籍”,“姑以佛典为之张目”,①是皆从不同侧面可见叔本华哲学与佛教之因缘——诚然,叔本华的文化视野不全在佛家,但确也有用“天眼”观察人生的一面。
故王国维之上述论述,虽不见一“佛”字,而实际深契佛家人生哲学之要义。但若王国维没有叔本华那样的“天眼”,他就难以理解并认同叔本华“天眼”中的人生。王国维不过是借叔本华接受过佛家影响的文化视野,系统地、理论地阐发他心头早已有的佛家情结,宣泄其有关人生的苦痛意识与解脱意识。
王国维看待美术也是如此。他所说的美术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大致相同。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能认识到文学是描写人生的:“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前述王国维把文学几乎看成是宗教或者说佛教,则显然有失偏颇。
本着此种核心的文学观念,他在《红楼梦评论》中如此阐发美术(当然包括文学)的职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王国维这种文学观,显然是把文学看成“上流社会之宗教”,即是前述文学宗教化或者说佛教化的具体展开。诚然,前述王国维之作《去毒篇》是在他写作《红楼梦评论》稍后,这只是说明王国维早有了文学宗教化的观念,他在《去毒篇》中只是加以总结、提升罢了。
毫无疑问,文学或者说美术之务,当然并不仅仅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文学是描写整个社会人生的,人生的本质也不全是痛苦。文学的确能带给人们精神上的 慰藉,但与宗教或者说佛教并不一样,它自有独立于宗教或者说佛教的自身价值。
王国维这种文学观,显然是把文学看得太褊狭了。可以说,王国维受宗教——主要是佛教影响而形成的狭隘的人生观,导致他同样狭隘的文学观。叔本华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只是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人生观与文学观的这种倾向而已。
王国维便采用上述人生观与文学观审视《红楼梦》的价值。《红楼梦评论》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谓“《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 自己求之者也”。在第四章中他更明确地指出:《红楼梦》“其精神”“存于解脱”。
在他看来,这是《红楼梦》的真精神,即《红楼梦》的伟大精神与不朽价值似乎就在于告诉人们人生的苦痛是自己造成的,人们应该如何去解脱这种人生的苦痛。这显然并没有真正把握《红楼梦》的真精神,而将之宗教化或者说佛教化了。
《红楼梦评论》第三章《(红楼梦)美学上之价值》则云:“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
在第四章中他说得更为明白:“《红楼梦》者,悲剧中之悲剧也。其美学上之价值即存乎此。”王国维把《红楼梦》看成中国文学中悲剧之悲剧,这是很有见地的。但他的失误在于,他 这样去评价《红楼梦》的时候,是从《红楼梦》的“厌世解脱之精神”这种佛家眼光去评判的,而《红楼梦》的真精神事实上并不在此。
这就是说,他的个别结论是对的,但他论述的“立脚地”却是错误的。这样,王国维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认识《红楼梦》的悲剧价值。
《红楼梦评论》第四章为《(红楼梦)伦理学上之价值》。王国维论述《红楼梦》的伦理学价值也是与解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解脱是伦理学上的最高理想。他的疑惑只是:“解脱之足以为伦理上最高之理想与否,实存于解脱之可能与否。
”据他的论证,“解脱之事,终不可能”。这是因为,即使在“释迦示寂以后,基督尸十字以来”,人类及万物的痛苦“不异于昔”并且,“释迦、基督自身之解脱与否,亦尚在不可知之 数”。
既然如此,“则《红楼梦》之以解脱为理想者,果可菲薄也欤?”不然。这是因为“人生忧患之如彼,而劳苦之如此,苟有血气者,未有不渴慕救济者也。不求之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王国维认为“美术”能解脱人生的苦痛已如前所论,而《红楼梦》正是这样的“美术”,且不是一般的“美术”,是“美术”中的顶峰之作,即“宇宙之大着述”。
因此,除了那些自绝于救济的人之外,对《红楼梦》这样“宇宙之大着述”,应该“企踪而欢迎”。王国维片面地认为《红楼梦》以“解脱”为理想,由此充分肯定《红楼梦》在伦理学上的价值,几乎把《红楼梦》当成了宗教读本或者说佛教读本。
三、余论
综上所论,王国维用“天眼”看待人生与文学如《红楼梦》,并不如《大智度论》所说“诸色无不能照”.即王国维固然深契佛家要旨,却并没有真正把握住人生与文学的底色。探究人生的本质及《红楼梦》的价值,并非不可以用“天眼”即佛家视野去观察,但若仅仅局限于这种佛家的眼光,则对人生与文学如《红楼梦》的认识自然是不全面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