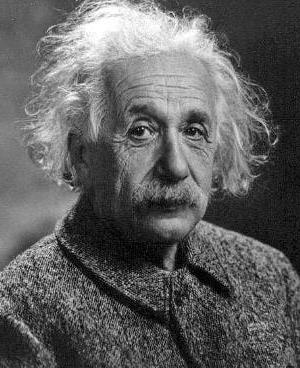飞沙飞沙满天飞 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
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 在“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08.11.15 首先感谢中山大学“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也感谢王雁(沙飞之女)和会务组周到的接待。
我对沙飞的摄影思想不熟悉,但是把它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里面再看他的作品,我也还有一些感想。我知道沙飞这个名字比较迟,虽然比较早的就看到沙飞的作品,其中一张就是《鲁迅与青年木刻家》,但是这些照片都没有署名,不知道是沙飞拍的。
80年代中期我知道沙飞了,对他的结局感到很惋惜,但对他的事情还是了解不多。我对沙飞熟悉起来是到21世纪了,前几年,小彦、冯原、我们一起到珠三角去,在开平,他们两位给我介绍在当地非常有影响的司徒家族,他们也谈到沙飞。
随后杨小彦送给我一本《沙飞摄影全集》。经过杨小彦和冯原的介绍,我又翻开了那本厚厚的《沙飞摄影全集》,我脑海中的沙飞影像就逐渐清晰起来了,似乎有一根线把我去过的延安和我从来没有去过,但在我脑海里有一种想象的晋察冀边区联系在一起了,让我对沙飞有了一些感想,今天我谈几点。
我对沙飞的基本看法是沙飞一生有两个高峰,成就了他非常杰出的,极具鲜明个性的左翼艺术家的事业。
我先说一个的看法,我认为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左翼和组织化的革命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左翼可以革命,也可以是“一个人的左翼”或者“书院里的左翼”,1930年代的李达等人,他们都是左翼,可是他们大多不跟中共发生组织联系,他们是“一个人的左翼”或者叫“个体左翼”。
左翼不一定革命,但是革命一定是左翼的。
左翼是多种选择中的一种,革命则是一种组织化的行为。沙飞的第一段阶段是1936年—1937年,我称之为沙飞的“个人化左翼”的阶段,这个时期沙飞的作品,刚才几位先生都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鲁迅,再一个是他的人道主义的情怀、对底层的关注。
1936年 8月-11 月,这对沙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他到了上海和鲁迅接触,拍了一组关于鲁迅的照片。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出来,沙飞非常敬仰鲁迅,这组照片完美地表达了沙飞对鲁迅的的尊崇。
到了1937年,沙飞还有一些关注底层的照片,但就我看,我觉得这种关注还没有到尖锐化或者直白化的程度,也就是他的这个左翼还是一种温和性的左翼。 从这个时期沙飞的代表性作品《老国民》、《人力车夫》、《码头工人》、《摆小摊的人》,还有一个老太太在缝衣服等影像,我们更多的感受是一种日常生活,或者是一般性的人道主义。
这种一般性的人道主义实际就是“五四”以后“为人生的文学”在更广泛的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
关注底层、关注社会,这些主题从“五四”就出现了,比如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温和左翼”和“激进左翼”是有区别的,激进左翼有一些重要的标志,首先要反映底层的苦难,再一个要反映底层的反抗。
这两个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化的左翼最鲜明的标志,而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展示底层的日常生活。还有一点,作为一种整体现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艺术是集团化的,是一个有组织的、有纲领的行动。
1930年成立的左联,有左翼文学、左翼戏剧、左翼电影、左翼音乐、左翼新闻等等八大类,全都是有组织,有纲领的。沙飞显然不在这个左翼组织化的队伍中间。他参加的“黑白社”跟“左联”完全没有关系。
我还要补充,这个时期的左翼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它一定要直白地表达对“伟大苏俄”的向往,热爱苏俄,向往苏俄,是中国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艺术的特征。可是反观这个时期的沙飞,他的作品里没有这个主题。
他就是个人化的左翼,或者叫温和左翼。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看法,这就是左翼和中共是划等号的,离开中共就没有左翼。但事实上,情况可能更复杂一些,在中共之外确有左翼,把这种个人化左翼联系和聚集在一起的就是鲁迅。
这就是我对1936、1937年沙飞作品的感受。 沙飞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大家都在讨论的晋察冀13年。这是沙飞作为个体的的左翼艺术家汇入到组织化的抗日革命洪流,成为了一个革命宣传战士。
沙飞是作为一个战地摄影记者去华北根据地的,当时还有一个青年记者陆诒也去了,陆诒很快就离开了,沙飞却留了下来。晋察冀是八路军和侵华日军最接近的地区,八路军的抗日和沙飞的抗日叠合在一起,在这里沙飞达到了他一生里创作最高峰。
在晋察冀13年里间,他置身在高度组织化革命战争的体制之下,“抗日”、“革命”、“自由”都在他的身上体现,使这个时期的作品形成了一种张力。但是我还有一个看法,那就是沙飞很特别,他没有能够如同大多数前往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一样都实现的左翼知识分子的两次转型:第一步,从左翼艺术家转变成革命宣传战士,这一步他跨过来了;但下一步,他没能够再向成熟的党的工作者转变。
晋察冀的革命知识分子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邓拓,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张春桥,他们和沙飞都是前后同事。邓拓、沙飞、张春桥是左翼知识分子前往晋察冀的三种类型,他们这三个人长期在晋察冀工作和战斗,但在这之前,这三人都曾不同程度地涉足上海左翼文化运动。
邓拓去上海最早,他在1929年就去了,1930年他参加了中共,是左翼科学家联盟的成员,1933年离开上海, 1937以邓云特的名字在上海出版了一本学术界都认可的专著《中国救荒史》。
沙飞去上海很迟,也就是在上海呆了三、四个月,但因为沙飞拍了鲁迅的照片,他在当时影响就比较大。张春桥是1935年 5月去上海的,这年他18岁,是通过朋友的介绍投奔左翼作家陈白尘的,还和陈白尘一同在上海的西爱咸斯路的一个阁楼上住了两个月(陈白尘:《我这样走来》,第74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 6月出版)。
张春桥在上海待的时间比较长,1935年10月参加了“左联”,他自称是1936年春夏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但在建国后“审干”运动中,上海市委确认的他的入党时间是1937年春。张春桥在上海的几年,虽然写了不少杂文和小说,但除了用笔名“狄克”写过被鲁迅批评过的一篇文章,在左翼文坛上名气不大,人们很少知道他。
这三个人就左翼的自觉意识而言,邓拓最高,张春桥次之,沙飞最低,但是这三个人在上海特殊环境下都没有被高度组织化。
1932年12月,邓拓被国民党逮捕,被押往苏州反省院,后经他的家庭营救出狱后回到了家乡福州,和共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再转到开封读河南大学,成为一个“个体左翼”。
张春桥是另一种情况,在国民党的严酷打压下,1935年后的上海共产党组织基本被打散,张春桥在上海接触较多的就是这样一些被打散,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沙飞、邓拓、张春桥都是一种松散状态下的左翼分子,或者说他们都是左翼的散兵游勇。
从上海到晋察冀,他们都经历了一个从个体化的左翼分子被纳入到军事一元化战争体制的转变过程。这三个人都抗日,都追求革命,我不专门研究张春桥,但我想,他在1938年 1月去延安,再转去晋察冀根据地,应是追求抗日和革命去了。
邓拓去晋察冀,他是归队,他是老党员,但因失去组织联系,有关情况有待调查,因而在1937年末重新入党。
张春桥也是归队,但是没有人能证明他在1936年入了党,故而在1938年 8月在延安重新入党。沙飞不一样,他去的主要原由是抗日,但也不能排除有追求左翼革命思想的成分在里边。因为这个时期国民党也抗日,1938年的武汉是全国爱国知识分子都想去的地方,在那儿有非常活跃的影响全国的革命文化活动。
沙飞为什么不去武汉而去了共产党的根据地?我认为这和他有一种左翼的追求,即响往共产党所强调的社会平等、社会革命的理想有关。
三个人去晋察冀之前,思想不完全一致,去了以后差异就显现出来了,当他们被汇入到共产革命洪流之后,邓拓和张春桥很快就被革命组织所规驯,就是被改造、融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了。今天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反映张春桥在这个时期有什么痛苦和苦恼的历史资料,邓拓还有一点,在 1944-1945年整风审干运动中,他写的个别的诗,抒发了某种苦闷的情绪。
沙飞是很早去晋察冀的,他是1937年下半年就去的,比张春桥早,可是他入党是在1942年。
我们知道1938年和1939年是中共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只要你有一点入党意愿,历史比较清楚,大致就能够入党。到了1939年下半年才有一个巩固党的决定,就是停止大发展。
在这个党员大发展的阶段,为什么沙飞不入党或者入不了党?我们通过王雁提供的资料知道有两个原因:一是组织上对他的经历有一些怀疑,这主要是沙飞是李公朴介绍去根据地的,而不是中共地下党介绍,也不是八路军办事处介绍的。
在当时的中共党人看,李公朴是一个“灰色政客”,这样就对沙飞起怀疑了;另外一个原因是沙飞对入党没有什么积极性,这在当时绝对是少数。当然类似的情况在延安也有:一个就是肖军,他到延安也是很早,当他最后确定想入党已是1945年,彭真也同意了,但是他去东北不久就被认为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于是就入不了党了;还有一个老同志也是革命艺术家,他就是塞克,他也是很早到延安,却是一个“异类”,始终没有入党。
我想沙飞在1942年之前,他是作为一个很有成就的专业人士被党重用的。应该属于“统战对象”;1942年之后,他是共产党内的“民主人士”。为什么呢?因为他太个性化,他保留了比较多的艺术家的知性、感性的方面。
他的个性化的左翼色彩到晋察冀以后还没有完全消失。我们的沙飞同志对体制化不敏感,他居然对长期保护他、重用他的聂荣臻司令员还有意见,甚至发展到要给在延安的毛泽东写一封信告聂的状,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事,是完全违反组织纪律的,也是非常奇怪的。
这件事,王雁的书上写了,我觉得写下这一段史实很重要。 第二点是在1945年 8月,八路军快到张家口的时候,他居然要写信给毛泽东,还是血书,他要和毛泽东讨论党的重大战略问题。
他是不是神经失常?我觉得他头脑还是清楚的,他就是充满一种疯狂、癫狂的革命激情,他身上的个体化左翼色彩还保留着。张春桥肯定就不会这么做,所以沙飞虽然也入了党,也作了大量革命工作,但他身上还多多少少保留着自由的思想。
昨天也谈到,沙飞非常认同,并身体力行了“革命艺术是一种战斗的武器”的思想。其实主张革命艺术是战斗的武器,这个概念在1929年就有了。
在延安的丁玲、肖军、王实味等,都认同革命文学艺术是宣传真理的战斗武器,所以持“战斗武器说”并不说明什么,我看来看去,总觉得沙飞有一点王实味的影子。 依我看这里有两点:一个是他对聂荣臻司令员的态度;第二是他要和毛泽东讨论问题这件事,这些都属于“非常不合时宜”。
我们知道有一个高长虹先生,他曾经和鲁迅打过笔仗。高长虹1941年来到延安,他也是写信要和毛泽东讨论重大战略问题,本来还很好,把他作为民主人士,请他吃饭,也请他讲话。
在高长虹和毛谈过话以后,组织上就不理他了,把他边缘化。到1945年他随着八路军到东北,高长虹也算是一个老同志了,就长期由东北局的宣传部把他养着,高老先生最后不知所踪,到哪儿去了人们也不知道。
他是一个思想奔放的老先生,他们都对革命组织缺少很认真的体会。 我的意思是沙飞的聪明才智和聂荣臻对他保护成就了他在晋察冀的13年。
前边讲了,沙飞有所谓“历史问题”,今天我们看这个根本不是问题。但在当时这是很严重的事,第一,他参加了国民革命第一军的北伐,这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在国民党反共的时候,没有看到沙飞的反抗。
第二,1931—1936年,沙飞在汕头当了国民党军队电台的一个报务员。放在1942年的晋察冀,这两点绝对是大问题。我看沙飞在激情和癫狂之下,有一种清醒在里面,他没有糊涂,他没有向组织上汇报交代这段历史。
他知道如果交代了这段历史,他就非常危险,因为当时情况下,党组织没有办法去“外调”,到汕头去了解他的历史。这样,轻则把他“挂起来”,重则如果是在陕甘宁边区,那就要送到边区保卫处的。沙飞是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的,他不会不知道他的同事和朋友邓拓,尽管在《晋察冀日报》的工作岗位上做出重要的贡献,但就是因为历史上曾两次被国民党逮捕,还进过苏州反省院,在1944年夏—1945年春的整风审干运动中,被集中到边区党校,在那儿接受了长时间的严厉审查。
所以沙飞啥也不说,而聂荣臻则是坚信他没有问题,对他很是重用,让他当了《抗敌报》的主任、科长、《晋察冀画报》的主任,这都叫破格重用。我认为,沙飞遇到聂荣臻,是他的人生的机遇,成就了他的创作高峰。
聂荣臻是摄影爱好者,很喜欢照相。他念念不忘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照的一些相片,这些照片以后都遗失了,他和沙飞既是上下级的关系,也是一种知音的关系。 当然沙飞也拍了很多珍贵的聂荣臻的照片。
这个时期还没有经过整风运动,这些照片都刊登在《晋察冀画报》上,送到延安,延安不太高兴。其实毛泽东对摄影还是喜欢的。1938年秋,延安摄影团成立后,毛亲自接见工作人员,对他们的工作更是給予大力支持,“每当摄影团给他拍摄电影和照片时,室内光线不够,又没有照明设备,毛便愉快地接受他们的安排,搬到室外去拍摄”。
电影团负责人吴印咸“是被专门请来延安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的,每月给他老家 120块大洋的生活费,供其家用。
党为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考虑得很全面,在经济上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参见吴筑清、张岱:《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1939年斯大林派了一个苏联摄影队来延安,领头的就是著名的记录片摄影家罗曼·卡门(Roman Karmen),斯大林要他们拍一部反映中国抗战和革命的电影,罗曼·卡门拍了《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在延安也给毛拍了不少镜头,毛对他们的工作,也很配合。
有一组镜头,时间是1939年,毛拿了一本书,就是刚刚出版的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从窑洞里走出来然后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这样翻看。这组镜头究竟是延安摄影团还是罗曼。卡门拍的,现在已不易说清了,如果是罗曼。
卡门拍摄的话,斯大林是一定要看的。罗曼。卡门还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过通讯《毛泽东会见记》。我是倾向于相信是罗曼。卡门拍摄的,因为延安摄影团此时已去了华北根据地, 《联共党史》在1938年还没有中文本,而此前延安摄影团拍摄的《延安与八路军》,在1940年袁牧之带胶片去苏联冲洗时,因卫国战争很快爆发而遗失了。
这是我看到沙飞作品时的联想,想到了毛。 沙飞摄影理念是“武器论”,在这种思路下,他确实是拍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充满战斗性和鼓动性的,当然有一些是“摆拍”。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叫“观念摄影”的说法?对这个“观念摄影”,我认为要放在一个大背景下来看。
当时我们的老百姓不认识世界,照片的作用就太重要了,至于以后“观念摄影”怎么发展,责任不在他。我们中国传统讲究“文以载道”,写小说要有“思想”在里边,要“启蒙民众”。他这个摄影也是“文以载道”,他要表达一种观念,表达一种思想,至于以后怎么变成“高、大、全”,那是以后的事,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环节。
那主要是革命胜利以后领袖要建立文化新秩序,沙飞则是在抗战时期,我的意思是要分开。我看到沙飞拍摄的《战斗在古长城》那几幅照片,有很深的感动。
在民族战争的大背景下,显现出中华民族的崇高和壮丽。 第二,沙飞也很重视“即时”,他拍鲁迅时捕捉的一瞬间,非常感动人,这些保留下来的东西都是非常动人的。
作为学历史的,我还特别重视沙飞拍过的那些反映晋察冀边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照片。这些照片在以后的历史叙述中全都被遮蔽了,比如晋察冀开一些重要会议,会场上既有毛的照片,也有蒋介石的照片,所以沙飞拍的这些照片都是很有历史价值的。
在我看,摄影的纪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都重要,当然还有一个时代性,以及作品中的人文内涵、这就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沙飞在晋察冀这13年中的作品,都包涵了这些重要的原素。
陈瑞林先生和王璜生先生都提到沙飞的结局,我觉得沙飞的个性对他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在革命的体制内,张春桥完全不说话,或是非常听话,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所以他以后步步高升。
1949年在革命胜利的前夜,沙飞的紧张、焦虑和疾病,还有那种无名的恐惧感,可能使他精神崩溃,也可能使他做出非常极端的行为。我有些怀疑,那段没有交代的历史成了沙飞的一个心病。
如果我们置身在当时的党的集体中间,在那种环境下,才能体会到沙飞内心中所承受的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共产党员任何事情都要跟组织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说,1942年入党时不说,1944-1945 年的整风时也不说(晋察冀在 1942-1943年处于日寇严酷的“扫荡”,整风运动推迟至 1944-1945年进行),1947年、1948年还不说,包袱越背越重。
沙飞的“不说”很严重。因为建国以后马上就可以“外调”,别人的交代也会把你扯出来,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他在1948年整党的时候坚持把其他同志打成“反革命特务”,这说明什么呢?可能是他的精神高度紧张,也可能是他“以攻为守”吧。到了1949年10月的开国大典,他居然无动于衷,这时已是权力再分配的时候,我觉得与他的心病有关。
我非常同意王雁的看法,以沙飞的个性,沙飞过不了建国以后政治运动一道一道的“关”的。 最后我讲一点,革命是破坏一切秩序,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沙飞成长在这个年代,他的激情和癫狂,他的敏感和偏执都和它有关。
沙飞的结局是不幸的,他永远定格在38岁,在即将革命胜利的时候倒下,使他没有成为领导干部,这看起来遗憾,其实也没什么,这使得沙飞永远是一位本色的人。
1949年前邓拓最大的贡献还不是编《晋察冀日报》,而是在全党首编《毛泽东选集》,可是邓拓如果不编的话,别人肯定也会编。张春桥在这个时期不露山,不露水,没有留下任何个性化的东西。
沙飞却留下了大量的东西,他的这种东西是不能复制的和取代的。沙飞那些非常著名的照片:《鲁迅先生最后的时刻》、《白求恩大夫做手术》等等,其意义已经超出了摄影,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最生动的影像记忆。
从这个意义上讲,沙飞具有永恒性,他真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成为一颗在祖国的天空中永远自由飞舞的沙粒”。 这就是我对沙飞的一些感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