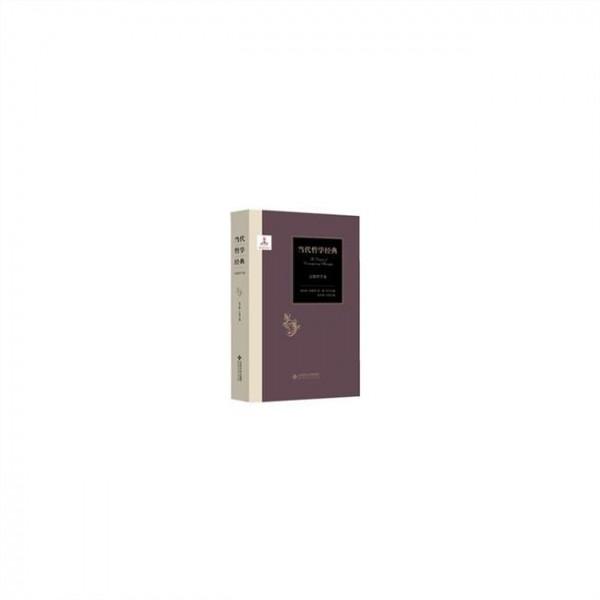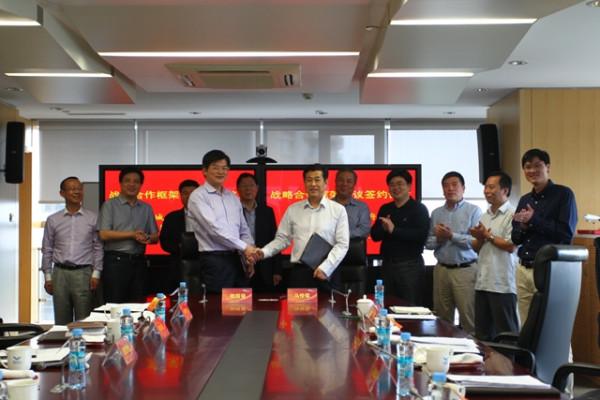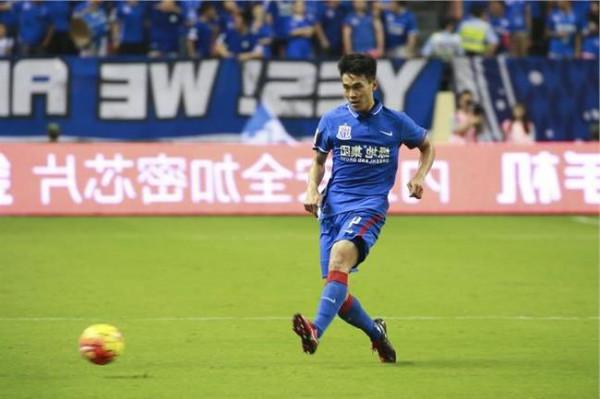俞吾金吴晓明 他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中的出类拔萃者——吴晓明教授沉痛悼念俞吾金老师
可能在所有同学、同事当中,我跟俞吾金的渊源是最深的,从1978年3月一起考入复旦,我们一直在一起学习、共事,我们本科、硕士、博士一直是同学。
俞吾金刚到复旦时,和我住一个宿舍,他喜好文学,而我们这代人恐怕对文学都有种天生的爱好,所以我与他多谈文学,我们关系非常好。国家留学基金刚刚设立时,我和他一起申请第一届基金,他申请哈佛哲学系,我申请去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与哲学系,因为都在波士顿,我们就坐同一个航班过去。后来我又注册了哈佛哲学系,跟他一起在杜维明的哈佛燕京学社。1984年12月我们一起留校,交往非常多。
对俞吾金总评价应该包括学术和教学两方面,这是他和上一辈学人有区别之处。每一代学人都面临自己的任务。刚过世不久的汤一介教授属于更早一代;俞吾金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批大学生,我比俞吾金小9岁,但我们还是一代人。老一辈学者的任务和我们不太一样,他们有很好的旧学功底,五四后又接受新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点,学问都成长在旧学的基础上。
“文革”后那批学人,承担的任务主要为:第一,快速学习,特别是对外学习;第二,使哲学领域迅速学术化,哲学以往主要被理解为意识形态领域,是阶级斗争的战场,往往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简单化处理。我们这一代要使这个研究领域迅速学术化;第三,在学习和学术化的基础上开始思考我们时代所面临的问题。
从这几方面讲,俞吾金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中出其类而拔其萃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评价。
第一方面,快速对外学习方面,他是我们这代人中的榜样。因为“文革”耽误,他一到班里学习就非常刻苦。他原来学俄语,刚进大学时外语比我还差,他的英语是从ABCD开始学,但是快速地掌握了,后来又学德语,所以他英语德语都很好。他当时对文学非常感兴趣,阅读量惊人。
他每天早上非常早起来,因为穿的是硬拖鞋,所以只要在宿舍里一走,就“咵嗒咵嗒”非常响,把我们都弄醒了。莎士比亚全集,每天看一本,如果一本没看完,他就到外面走道里继续看。他最喜欢法兰西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当然中国传统的文学也喜欢。他身体也特别好,体育课上拉单杠,其他同学能拉一下两下就不得了了,他上去能拉十几下,穿着一身洗白的军装,是我们班公认的帅哥。
俞吾金学习的内容非常广泛。印象比较深的是,他搞哲学理论,却也常喜欢写诗歌和小说,这大概是他后来学术上能够比较广博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他后来的研究领域的确非常广泛。他一开始对西方哲学感兴趣,写的第一篇文章是《“蜡块说”小考》。后来对美学也有很大兴趣,也做过研究。
在哈佛的时候,他跟我说想花一段时间研究中国哲学,因为中国传统的学问,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在我们哲学领域,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哲学恐怕也不能完全分开。俞吾金学习的量和速度确实让人惊讶,确实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中非常突出的。
第二方面,哲学研究原来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学术意义上恐怕很少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我们这代人开始学习,后来开始做研究,将哲学领域学术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俞吾金硕士时研究西方哲学,是尹大贻先生的学生,后来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是胡曲园先生的学生。他花了很多精力,使得我们的哲学研究能够学术化。这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工作,而是我们这代人的基本任务。
俞吾金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一个是他的博士论文《意识形态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长时期内有依傍于意识形态的倾向,改革开放后需要在学术上开展出来。当时我跟他一起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答辩主席是华东师大的冯契先生,他对俞吾金的论文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的这篇论文“长袖善舞”,意为他在这个领域中达到自如的境地。
能做出这样的研究,是与他的刻苦,包括他对德语的把握是分不开的。直到现在,如果做意识形态理论,恐怕都要回溯到他这篇论文。
他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关注德国古典哲学,他在西方哲学方面也是德国古典哲学做得特别强。过去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都是教科书上最基本的内容,这些内容不能说错,但是如果没有和哲学史、和哲学方面其他丰富的学养相结合,恐怕就有严重问题。
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包括着它的学术架构,这一点我们在以往是把疏忽了。事实上列宁曾经讲过,如果你不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恐怕很难真正读懂《资本论》。所以俞吾金一方面研究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另外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能够和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结合在一起。
所以,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使复旦大学哲学学科在全国占有非常高的地位。
因为我们后来申请的211基地、创新平台,都是综合了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外,复旦的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加上后来增补的中国哲学,使复旦哲学学科成为全国仅有的有三个国家重点学科的一级学科,这跟他的研究都分不开。
所以,俞吾金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界的重要贡献,也是他身体力行的一个方面,便是使这个研究领域迅速学术化,从而支撑这个学科今天能在学术界、理论界和大学中立足。
第三方面,俞吾金的整个研究,不仅仅是纯学术的研究,他特别强调思想方面。我们经常讲,学术上有一种是纯学术的做法,类似于经院哲学,但是我们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确实面临许多重大问题。俞吾金在这方面的思考非常突出。
他早期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影响也跟他有这样一种想法、有这样的一种向度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当时在收获了哲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实际上提出了,要影响大众,要影响我们国家能够在发展过程中有健全的思考。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包括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和影响很大的一些著作,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在思想、理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思考与超越》,还有《问题域外的问题》,这些都不仅是学术研究,而同时是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应答。他在学习研究中不断思考问题,这一点对同事和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他的思考也不仅仅是去影响大众,而且要能够使得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化的。俞吾金在较早时谈到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源和组成部分问题。列宁讲的主要是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俞吾金提出马克思理论和组成部分方面还应该包括人类学研究。
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中有一部分是跟19世纪发展起来的人类学,或者叫民族学研究,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在马克思的学术中,事实上有形无形包含了这个部分。从现在来看,俞吾金当时的想法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马克思的学术从建立时来看,主要有几个方面:英国的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哲学,但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后来马克思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即它所阐述的资本逻辑如何在历史现实中具体化,在不同民族的发展经历中得到体现。
这个问题对于今天中国而言更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它牵涉到对中国道路的深入理解。马克思给出的历史道路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那么简单。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一卷时,就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当时俄国的《祖国纪事》刊物也向他征询过类似的问题。所以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过:马克思在当时是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是对资本逻辑、对资本在这个时候拥有的绝对权力进行了阐述;另一方面,这个绝对权力如何在整个世界历史过程中具体化,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俞吾金很早就开始思考马克思学术中包含的人类学的来源,所以他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是认真思考的。
因此,对俞吾金的整体评价,是建立在我们这一代学人所面临的任务中,在上述这些任务中,我认为俞吾金每一个方面都是走在前面,都是出类拔萃的。他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突出代表,也是我们复旦大学人文学术研究的突出代表,尤其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突出的代表——我们在国内哲学界的优势和研究特点,都和俞吾金的努力分不开。
另外,他的许多工作上、生活上的事情,确实给我们留下非常多的印象,包括他的为人方面。我跟俞吾金关系非常好,我们一直在一起,他像大哥一样。我们关系好到什么程度?现在外面有一个说法,说俞吾金当时工作很忙,非常勤奋地写作,因为怕别人打扰他,他在外面贴一个纸条,好像是说星期二下午大家可以来聊聊,平时就谢绝来访。
唯一的一个例外是,吴晓明可以随便去的,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他确实贴了这样的条子,既然这是他立的规则,我们不能破坏,但是我认为我跟他已经关系好到这个程度,所以我拿出笔写了“(吴晓明例外)”,然后就推门进去了,这就没有破坏他的规则。
文学上我跟俞吾金谈得非常多,包括俞吾金写的诗歌我们都一起读。只是他后来的兴趣跟我有点不同,他后来对所谓后现代的文学感兴趣,而我对中国传统的文学更感兴趣,总之,我们之间有非常多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