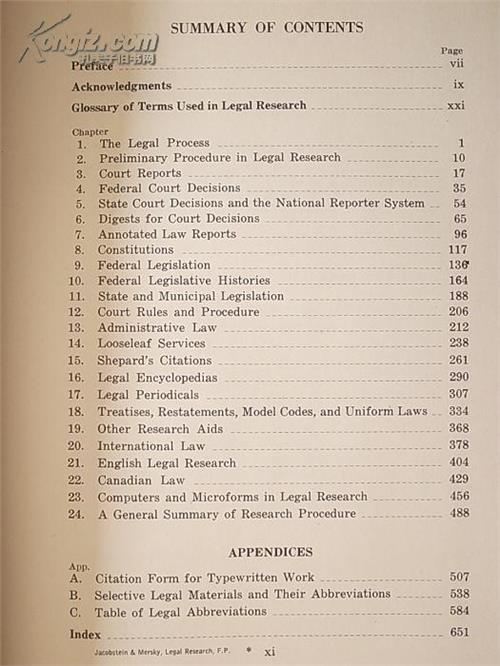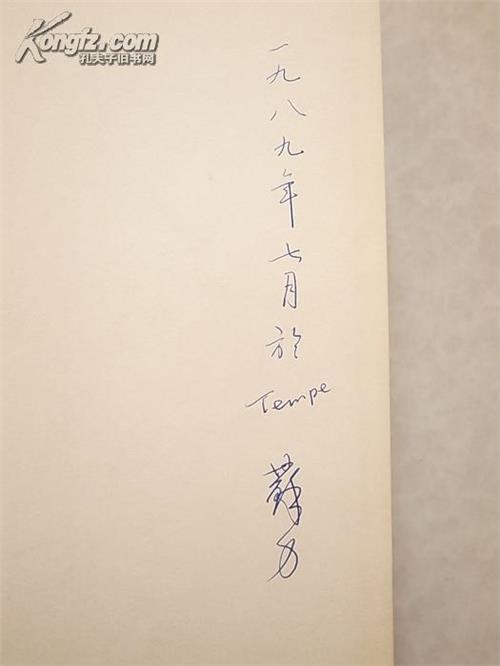朱苏力语言 朱苏力: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
对于一种相对长期存在、据此可以认定获得了特定时代人们之认可的法律制度或法律规则,应如何理解?应如何考查其历史的意义以及更重要的是如何恰当地审视这些制度或规则与我们当下生活世界的相关性?这个问题是当代转型时期中国法学研究中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一般性问题。
它涉及的问题不仅是应如何理解和考察我们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应以及能如何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创新和改革;它也还涉及到如何理解外国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我们正试图借鉴的工业上先进的国家(这是我们目前比较关注的),以及在我们看来那些发展中乃至最不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尽管这往往进入不了当代中国法学家的视野)。
法条主义无法承担这一任务,尽管法条主义(或概念法学或形式主义)的进路对法律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训练并对常规时期法律的运作具有重要的、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意义。[注释1:这三者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一个东西,只是在中国一般称其为“法条主义”或“概念法学”,而在美国,至少是在波斯纳那里被归结为形式主义。
波斯纳曾对形式主义法学以及——更广阔地——对一般的形式主义进行了细致地讲道理的分析,指出了其弊端以及优点。见Richard A.
Posner,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法条主义将法条作为不可质疑的权威,要求社会生活都服从法条。
这种方法往往适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正处于变革时期,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规制社会生活的法律制度都处于——有时是急剧的——变动之中,并且作为社会生活系统内部一个组成部分的法治也必须同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相互协调。
当代中国的法律制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法条主义,这并非学术本身的逻辑要求,而是学术所附着的生活世界使然。同时,中国法学如果要想真正形成学术研究的传统,也必须超越法条主义,因为学术发展本身不可能来自学术资料本身。
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界一直在进行着这种超越法条主义的努力,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和社会变迁,已使得许多法学家不再满意法条主义,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一种新的研究法律制度的进路和方法。
但是,现有的中外传统的法理学著作对法律研究方法一直缺乏足够的系统关注和理论分析。传统的法理学著作很少提及方法问题(更不用说讨论了),偶尔提及,也往往非常粗略和概括;既没有结合具体实例的细致分析,也未能提出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系统表述,只是笼统地提一些方法甚或是命题。
[注释2:博登海默的《法理学》著作副标题虽为“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但是打开书一看,几乎没有任何方法论的讨论;而中国目前通用的名为《法理学》或《法学基础理论》的教材或著作虽然常常有一节讨论法学的研究方法,但是其中除了提及一些“方法”的名号和原则外,对读者既无方法论上的思维训练,也无法作为方法予以应用。
参见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沈宗灵主编、张文显副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近年来,在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为基础,法律经济学分析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规范且卓有成效的方法论论述,但是法律经济学分析对数据要求的标准很高,对经济学素养要求也很高,其方法难以在传统的法律研究中普遍沿用,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法律界。
广义的法律社会学实际是由多个交叉学科构成的,无法形成或尚未形成统一的、便利法官和其它法律人运用的研究进路和方法。
而狭义上的法律社会学(sociology of law)更多借助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实证调查方法,尽管有助于理解特定社会中的法律和制度,可供法学家参考,但对于大批受传统法学教育的、强调操作的法律人来说,出于学科传统和研究时间的限制,实证研究的方法似乎也缺乏足够的相关性。
要寻求一种与法律人有更多相关性的研究进路和方法,因此,在放开眼界的同时,又不能不重视法律界已经形成的、哪怕是有明显弊端的学科传统。
本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努力,它试图提出一种我暂且称为“语境论”的进路。这一进路坚持以法律制度和规则为中心关注(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职业法律人偏好的法律形式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力求语境化地(设身处地地、历史地)理解任何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规则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因此它又与法律社会学、哲学阐释学具有一致之处)。
就态度而言,这种语境化一方面拥有法条主义一般说来容易表现出来的尊重既定具体法律制度的特点,同时又要求或至少是隐含了对任何具体法律制度的学术的而不仅仅是政治的批判态度;并且,也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学术的强调,这种进路在一定意义上也隐含了某种建构的因素,而并非完全是批判法学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战略。
就总体而言,这一进路反对以抽象的、所谓代表了永恒价值的大词来评价法律制度和规则,而是切实注重特定社会中人的生物性禀赋的以及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把法律制度和规则都视为在诸多相对稳定的制约条件下对于常规社会问题做出的一种比较经济且常规化的回应。
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当从宏观上考察时,这种语境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是一致的,但它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命题或原则的简单搬用或重复;它有哲学的因素,但它本身不是哲学,也不强调哲学,而是强调细致、具体地考查和发现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受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法律制度的塑造和制约。
必须对本文标题中的一些关键词加以强调和说明。首先,本文强调的是法律制度层面的研究进路,在这一层面上,法律往往是相对长期稳定的社会规范,与法律条文并不等同,有时甚至完全没有或无需正式条文的规定(习惯)。因此,这一研究进路关注的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也不是个别的司法活动,而是一个社会制度化处置社会常规性问题的方式。
其次,希望读者注意,本文强调语境论是法律制度研究的一种进路,而不是唯一的或最佳的进路。因此,这一进路并不意味着对其它研究进路(包括法条主义进路)的否定和排斥,相反,它欢迎法律研究的其它进路和视角,只要能有效地说明和解决问题。
但这并不因此意味着本文作者采取的是一种简单到没有原则的“兼容并蓄”的态度,笼统地谈“兼容并蓄”,如果不是因为言者缺乏智识能力(分不清理论之是非),就是因为媚俗、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也正是基于此,本文将在对目前中国法学界比较流行的、同样旨在超越法条主义的两种主要法学研究进路提出理论上的分析批评。
第三,尽管有种种危险,本文还是试图对语境论的进路提出一种略为“公式化”或“程式化”的表述,以求这一进路不停留于一般命题,使之有可能更操作化、程序化或具体化,成为一种方法或类似于方法的东西。
但我必须承认,这种努力不仅有可能失败,这种公式化的表述也有完全可能成为一种新教条。因此,我提醒读者,本文对这一进路所作的方法论概括,只是试图帮助读者在其它法律制度问题研究上运用这一进路,是为了获取这种研究能力的一种联系或训练,而并非获得恰当或真确结论的保证;它更多是一种入门指南,而不是一种操作手册。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上,真正有洞见的研究成果,至少是很难(如果不是完全不能的话)严格依据某一操作规则而获得。因此,读者只应把这种方法论表述作为获得“语境论”和思考问题方式的一个或许有但不必定有帮助的过程;做人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做学问过河拆桥则是提升自己能力之必须。
为避免方法论的讨论“玄学化”或过分“概念化”(这常常是难免的),讨论必须有所附着。为此,本文特别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作为展示这种研究进路和方法的范例。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那些在今天看来具有法律意味的制度,我希望展现这种分析进路和方法的有效性和解说力。
但是,由于本文的中心论题是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因此我又必须提醒读者,不要过分注重本文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分析结论,而是这种分析的“路数”;有关婚姻制度的分析结论仍然是一座过后就可以拆的“桥”。
但是这并不意味本文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分析完全是虚构的,没有经验材料支持,因此是没有意义的。的确,本文中谈及的中国传统婚姻制度是“理想型”的构建,即它不等于某个朝代或某个地区的具体的婚姻制度,但是,它是有一定的经验材料支撑的。
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对这一“理想型”的某些细节提出质疑,但是一般说来,这既不影响这一理想型的构建,因此并不影响本文的方法论讨论的意义。
本文的结构如下:附着于理想型的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我将首先对法律制度研究的“价值论”进路和“文化论”进路进行分析,指出其理论解释力的弱点(本文将不对法条主义的进路展开讨论)。然后,我展开本文主张的“语境论”进路对这一制度的分析和理解,力求比较细致展示这一制度的历史正当性。
第三节将对这一进路作进一步的理论解说,回答人们可能对这一进路提出的批评。第四节试图根据上两节的分析提出一种显然很不完善但有必要予以追求的理论化、公式化的表述,力求它可能作为一种制度研究的方法或指南。第五节,我将进一步展示这种进路和方法对于理解西方法律制度的适用性以及对我们今天法治建设的部分相关性。最后是一个小结。
大致说来,在中国传统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的诸多特点中,具有法律意义的[注释3:由于中国古代法制的特点,因此婚姻制度中究竟有那些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制度,这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如果从法条主义的视角出发,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很少有法律制度的因素,因此过窄;如果从国家行为说,则可能将一些具体官员非规范性行为都视为法律,因此过宽。
因此,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法律”。我在确定这些“具有法律意义”的制度特点时,主要考虑了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中国学者习惯作为法律制度来处理的婚姻常规,例如同性不婚、婚龄、七出三不去等,另一方面,我考虑了我认为比较恰当的哈特的独特的功能性法律界定,“法律的存在指的是某些人类行为不再是选择性的,而是在某些意义上是义务性的”。
H.L.A.Hart,The Concept of Law,2nd ed., Clarendon Press,1994,p.6.因此,同性不婚、父母包办、媒妁之言这种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当时的人们具有义务性的习惯或常规就被视为法律的特点,相反,一般的重男轻女则在本文不作为法律来处理。
]大致有早婚、父母包办、媒妁之言、同性不婚、七出三不去等。[注释4: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可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特别是第2章;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书店,1992年;郭建等:《中国文化通志·法律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特别是第3章。
]对于这种传统的婚姻制度应如何理解和分析,就与当下法律的相关性而言,目前大致有两种进路,我分别称其为“价值论”进路和“文化论”进路。[注释5:当然,这里的概括并不涵盖一切。至少在法律制度史的研究上,还有一种“史实”的进路,这种进路特别强调发现和引证法律制度和规则的本来面目,不追求对制度或规则本身做出解释,力求保持一种“价值无涉”的立场。
但是,这种研究进路和本文的关切相关性较少,我将在其他地方对这一进路做出分析和评价。]
从“价值论”的进路切入,大致说来,对上述婚姻制度的种种特点(也许“同性不婚”除外)都采取了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这些特点都反映了一种家族主义的、父权主义的价值,反映了对妇女以及其它弱者(子女)的歧视和压迫,反映了传统小农经济社会或中国封建社会无视人权、压制个人自由的主流价值取向,因而传统法律制度是必须批判、彻底废弃的;在这一话语中,传统婚姻制度的全部作用只是证明我们(特别是作者)的伟大、我们祖先的愚昧。
作为一个现代的个体来说,我当然赞同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批判,并且认为传统婚姻制度的这些特点在现代条件下是应当并可以废弃的(事实上也正在被废弃)。但是,法律的学术研究并不是要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表示一种不共戴天的革命态度,更重要的是要解说为什么这些制度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得以产生并长期延续,并进而理解我们的今天的制度。
如果传统的婚姻制度真的是那样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就只能——如果激进一点——从一种非常简单化的“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