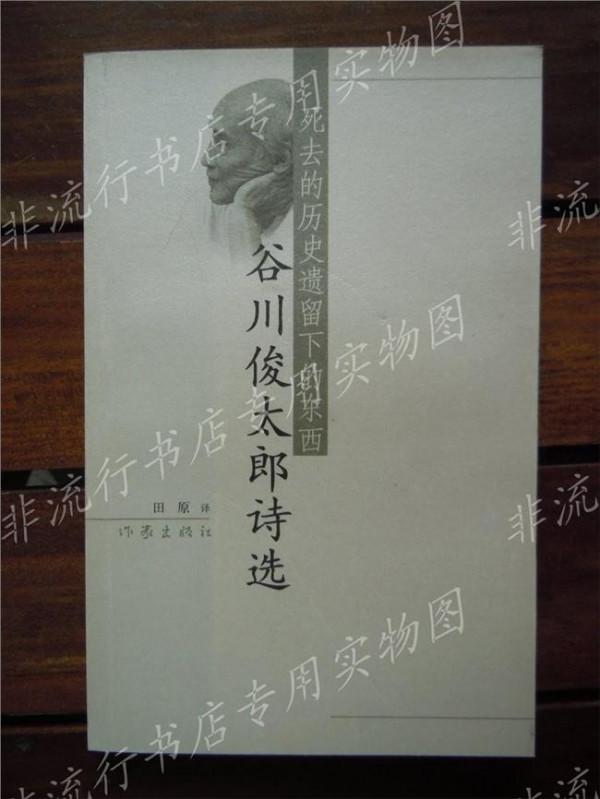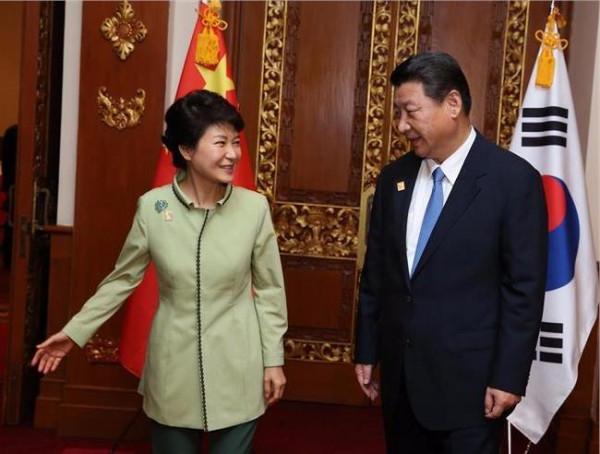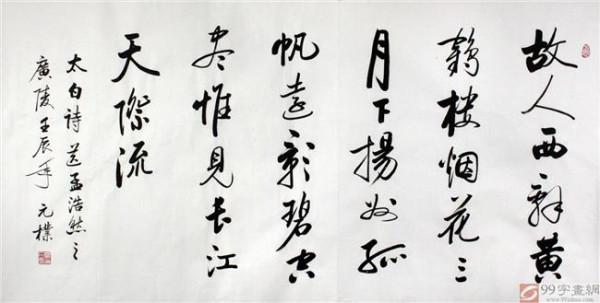田原俊彦 田原评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跨越世纪的天才
如果我们勉强把谷川的作品用年代划分开,将是这样的情景:上世纪50年代为创作的本能性爆发;60年代为纯诗写作;70年代为变化的萌发;80年代为语言的变迁;90年代是对生命和现实的直视与回归;21世纪是经验的升华和文学性的结晶。
谷川俊太郎不仅在当代日本诗坛是最重要、最有影响力和家喻户晓的诗人,而且在国际文坛上也是被公认的最生动和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这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即使对于100年甚至是500年以后的读者,我们都可以断言:那时的他(她)们一定会从他的作品里找到依据——即谷川俊太郎是一位跨越世纪的天才。
在众多的诗人逐渐被读者和时间淘汰时,谷川俊太郎的作品却在时间和读者中为诗歌赢得尊严,他创作于半个多世纪前的作品,至今仍被广泛持续地阅读,他的一本诗选集数十年来可以重印到50多版次,累积销售到80余万册。
我想这样的诗人在哪个语种里都是不多见的。这也是我曾经在一篇日语文章称他是亚洲的“普列维尔”的理由之所在。时间、读者和谷川俊太郎自身的诗歌都已经证明:他的诗篇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黯淡和老朽,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时间的深处获得新生,散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10数年前,在日本关西一所私立大学学习日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借助词典翻译谷川俊太郎的作品。至今我仍对起初在灯下阅读他诗歌作品时的兴奋记忆犹新。10数年前的中国诗人和读者对日本现代诗的认识是模糊的,也是带有歧视性的。
就是说到谷川俊太郎为止,没有一位日本现代诗人的诗歌文本能真正赢得中国当代诗人和读者的信任——即伟大的日本现代诗人在中国读者中是缺席的(造成日本现代诗在中国的文化空白尽管与翻译和历史文化以及政治背景不无关联)。
以至于使中国诗人和读者误认为日本是现代诗的沙漠。二十世纪末,谷川俊太郎的诗歌作品大量登陆中国,改变了中国诗人对日本现代诗的印象,也改变了日本现代诗在中国的命运,从而使日本现代诗因他在中国诗人和读者中建立了权威。
谷川俊太郎的诗歌在中国读者中引起的强烈共鸣绝不是偶然的,除了与他深奥和广阔的诗歌精神和生动性有直接关联外,也与其作品个性的强韧度和独创性以及艺术上的完整性密不可分。可以说,谷川俊太郎是当代国际诗坛少见的具有广泛意义素质和富有普遍精神价值的诗人,也是具有思想深度的诗人,只是他的思想和深奥的诗意不动声色地隐藏在他平易、简约、朴素和透明的诗句当中。
至今,我时常还在为自己与谷川诗歌的邂逅而暗自庆幸。令我感慨的是,谷川俊太郎的诗歌引导我捷足先登,通过他多彩的文学世界使我跨进了日本现代诗的门槛。如果没有与谷川作品邂逅的契机,如果他不是被作为重要对象、而还是被轻描淡写地译介到中国,日本现代诗在中国是一张什么的残缺面孔实在难以想象。
谷川的作品使我知道诗歌不是孤立的。在他的母语里,他拥有着不同年龄层和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学龄前的儿童、少男少女、青壮年人、老人甚至家庭主妇以及文化精英和大学教授等等。因此他被冠以“国民诗人”,同时还被称为“宇宙诗人”和“教科书诗人”。
因为他的作品几十年如一日,被日本每年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高、中小学课本和大学教材采用。谷川用他的诗歌再次验证了四个字:“易读”和“耐读”。在他的母语之外,他的作品也在与域外不同语言的读者产生着共鸣。
这当然是他诗歌自身魅力所致。这种结果来自于他与众不同的语言感觉和感性质量;来自于他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想象;也来自于他对世界和他人至高无上的人文情怀和对弱者的巨大同情。与更多一生只是以一种创作手法结束自己写作生涯的诗人相比,同时尝试多种写法的谷川俊太郎似乎具有超人的一面,从整体作品看,他的诗歌可以笼统地分类为两种写作倾向——即语言本位和人间本位。
童诗、语言游戏之歌系列、歌词和讽刺诗我们可以把它们理解为面向大众的人间本位型作品。
其他的则可以统称为纯诗写作的语言本位型。在这两大类型的作品中,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达达主义、现实主义和实验性等等网罗其中,变幻无常。
他的作品你很难用学术上既定的什么主义、流派和思潮来为他命名和界定,谷川不是什么主义的追随者,而是什么主义的创造者。从他多元多样的文本情调和纯粹丰盈的诗性特质,我们不难看出,谷川仿佛自始至终在做着这样的努力——在不断变化中的自我蜕变里,始终警惕和抵抗着被一种主义(或曰写作手法)的束缚和固定。
这是谷川不断在变化中否定自我、在超越自我中前进的原动力之一,也是使得他的作品在变化的哲学里升华到更高的诗学层面,进入到更高的艺术境界的根源之所在。
谷川俊太郎的诗歌主题庞杂有序。半个多世纪以来,谷川的写作几乎是围绕人生和人间性、生命和生活、宇宙与孤独展开的,他忠实于自己内心沉默的力量,对宇宙和历史的想象独一无二。他在东京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作为人有两种存在:社会存在和宇宙存在。
诗人的情况稍有不同,对我而言,宇宙存在更为重要。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我更看重宇宙存在呢?因为当一个诗人建立一种宇宙观时,他才能够超越这个时代的局限性。
然后诗人的眼光也许会放得更远,能够看到更遥远的未来,或者眺望到更遥远的过去。我的第一本诗集的书名叫《二十亿光年的孤独》,从这个书名你可以看出,我是作为一个宇宙中存在的诗人出发的,而不仅仅是在某一个特定社会和时代生存的诗人。”或许正如他所言,他才用“诗歌这种无政府语言”(谷川俊太郎语)跟现实生活和时代政治保持着适当的微妙距离,超越这个时代并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语言和诗情。
谷川俊太郎不愧是一位语言的巨匠,自然风景在内心的投射,对爱情反思和对生死的思考,对个体意识和身体性的张扬等都在他的诗篇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感动(包括同情)、世界(宇宙)、沉默(孤独)、自省(反思)像是被无形的音乐之线串联一起贯穿在他的作品里。
谷川不同时期的作品告诉我们,他从未动摇过这种创作理念。在日本战后现代诗发展的历程里,谷川的写作并没有受到太多时代潮流和理论导向的干预,甚至也很难从他的作品看出其他诗歌流派影响的痕迹。
这种对自己写作理念的自信和坚守可以说是一位大诗人的显著标志。从不满20岁步入诗坛至今,谷川可以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写作状态。我曾在我的日语论文里称:他不是那种由“量变到质变”过渡的努力型和勤奋型的诗人,不属于那种在瞬间将才气发挥殆尽的“闪电型”的“短命”诗人,更不是江郎才尽型的那种越写越糟糕的诗人。
若单从谷川俊太郎不满17岁在《丰多摩》和《金平糖》上开始发表作品、和在21岁出版处女诗集《二十亿光年的孤独》来看,玄乎一点讲,他在未来要成为诗人似乎是在前世就已注定过的——即他是一位与生俱来的诗人。
这类诗人为诗天分的先天性总是大于后天的,这种先天性我们不妨把谷川理解为灵感型的诗人。
如果我们勉强把谷川的作品用年代划分开,将是这样的情景:上世纪50年代为创作的本能性爆发;60年代为纯诗写作;70年代为变化的萌发;80年代为语言的变迁;90年代是对生命和现实的直视与回归;21世纪是经验的升华和文学性的结晶。
他的整体作品也可归纳为以下几点:a、自然、文化和精神三种风景的相映重叠;b、平面抒情和立体抒情的交替,语言空间与抒情空间、内在节奏与外在韵律的整合;c、抒情感和叙事性的融合;d、哲学、思想、感性和理性的均衡处理;e、文本的四元局面——儿童诗、娱乐作品及面向一般读者和专业诗人的作品。
即使用世界的目光来衡量,谷川俊太郎也是国际诗坛的巨擘。他的创作涉猎诗歌、散文、童话、剧本和翻译。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历程中,写下了许多重要作品。在日本现代诗坛,谷川俊太郎一直走在尝试和探索诗歌的最前列,他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中成长。
娴熟的表现技巧和对日语的巧妙运用和发挥、人类的悲欢离合、孤独与生死、存在与虚无、宇宙与想象在他的诗篇里被表现到了极致。他的诗一边扎根日本本土文化的土壤,一边深得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化精髓。
他在悖论中表达肯定,在肯定中表达质疑。从抽象中抽取具象,又从具象中呈现抽象。他以平易的语言表达深刻,以简洁的语言表达复杂,呈现出人类精神生活的共同困惑,并体现出精湛的文学品质。因此,来自不同语种的读者,我相信都能从谷川俊太郎的作品中得到慰藉。
谷川俊太郎是注重感觉的诗人,也是“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对爱尔兰诗人和批评家希尼的授奖辞)的诗人。他的感觉更多是构筑在他无意识的流动之上,他的想象来自他的生存经验和生命感受。
他有不少诗篇“是因为想象力而说出的一种语言”(帕斯)。读他的作品,能够从他的诗歌语言感受到日语的丰饶。谷川的诗歌文本使我再次确信:“诗歌的魅力来自感性”。谷川不仅已用他的诗歌语言创造了一个诗歌传统,而且也形成了“谷川流”的日语。这是一个值得日后研究的文学和语言学现象。
时间是诗人的大敌。任何诗人都必须接受时间的审查,也都休想逃出时间的检验。在时间面前,诗人的命运只有两种:要么被时间的尘埃埋葬,成为时间的牺牲品;要么征服时间,成为支配时间的主人。谷川俊太郎显然属于后者,他在时间面前还原出自己的本色。
在我的眼里,谷川俊太郎不会老去,因为死亡对他已经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即使有一天他的肉体消失,他诗歌的灵魂之声也会在大地上回荡。他的诗歌文本不仅影响现在和未来,而且注定也将会影响过去和历史。
阅读谷川俊太郎的作品,其实是我们经受一场灵魂的洗礼,是在与这位跨越世纪的天才对话,也是在感受掩藏在诗人内心的巨大沉默。他诗歌中的感伤就是我们自身的感伤,他诗歌中的亢奋就是我们自身的亢奋。如果把诗歌比作灯盏,谷川俊太郎的诗歌之光将照亮自然之光无法抵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