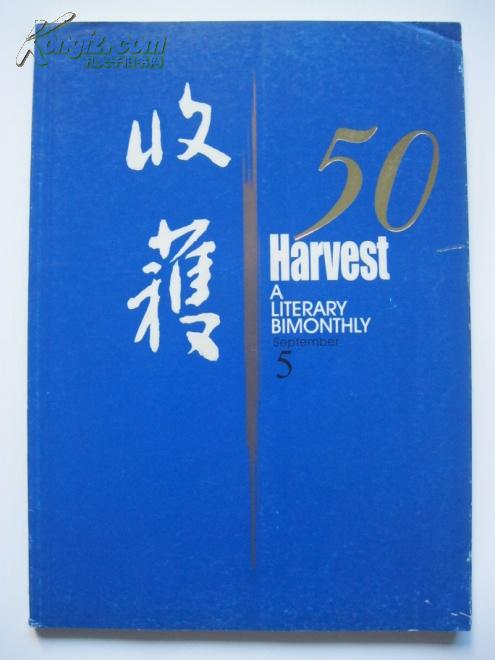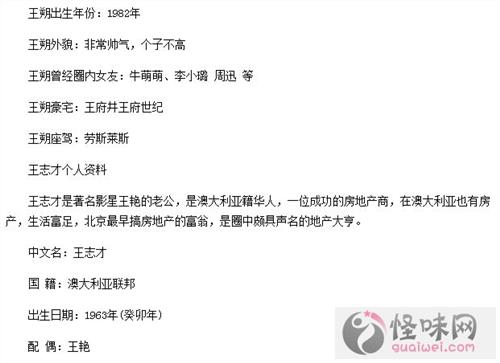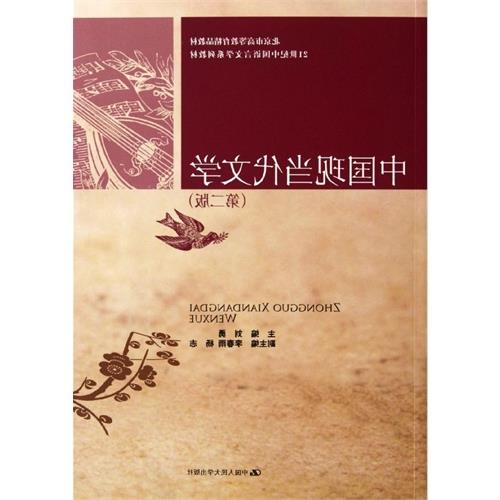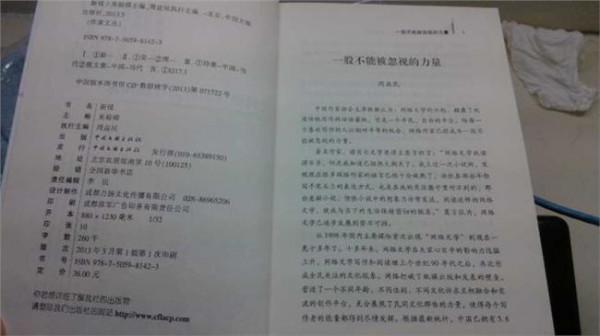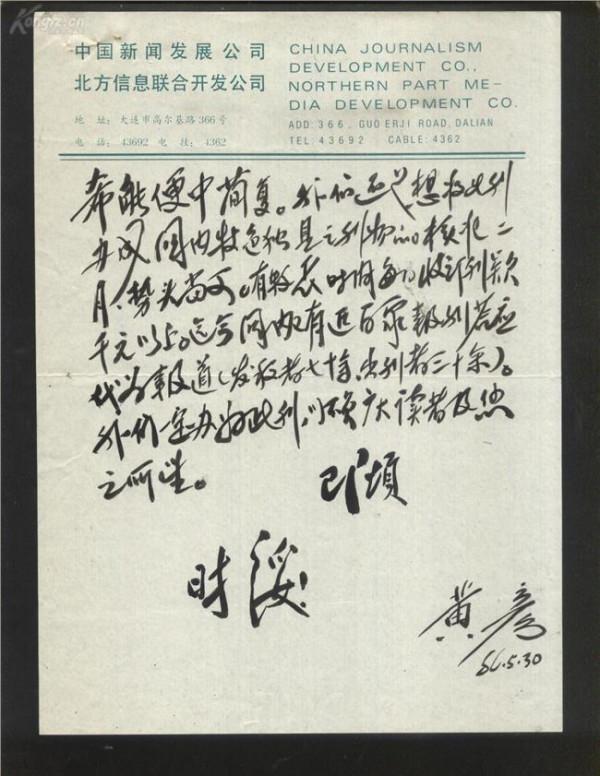王安忆与张承志 王安忆:我非常尊敬张承志 和他相比我是个匠人
他后来不大写小说了,写的都是散文。我觉得他,怎么讲,现在说这话不要紧了,他已经对我有免疫力了,不会再生误会。我觉得他太没有匠气了,太不像匠人了,而我是个匠人。就是他对做活这件事情太不满意了,他是个诗人,他一定要直抒胸臆,他一定要抒发情感。我觉得完全没有匠气的话很难做成活的呀,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后来写的散文写得非常好,有一篇散文叫《公社的青史》是我最喜欢的散文了。
“张承志的语言像在刀锋上走”
张:陈村的《走出大渡河》,和你们这个男子汉讨论有没有什么关系?
王:男子汉讨论基本上是来自《北方的河》,甚至来自张承志本人。《北方的河》塑造的男性是那么的魁伟,有力量,理想那么高。
张:而且他还是沉默的、不说话的人。
王:对,无论怎么接近他,都不能够理解他一点点。尤其是对女性的拒斥,这简直让天下女性绝望,他的魅力似乎专针对女性,可却偏偏不让女性了解。
张:对这部作品,当时我是很感动的,还是上高中的时候读到的。后来考上大学,坐火车,我背包里就放了两部队建设作品,一部是《北方的河》,一部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北方的河》是1984年的,《你别无选择》是1985年的。1985年来上海上学,当时包里就放了这两部作品。
王:张承志也是个很有趣的人,他和他喜欢的人在一起就没脾气了。张炜和他关系很好,张炜就敢去撩他。他脾气很大,但是和张炜在一起就不大发脾气的,现在对我也不大发了,他也晓得我对他真的是没有一点恶意。有一个场面特别有意思,就是张炜说,其实啊张承志,你就像个大姑娘,很腼腆的。
你看他的表情,他确是很腼腆的一个人。张承志说,你没看到我发脾气的样子。然后张炜就说,你发脾气还是个大姑娘。和这些同辈人相处,现在回想起来都蛮好的,首先都是很健康的,蛮纯洁的,也互相受益,也非常真挚。
张:张承志的语言有些特别。
王:他的语言呢,是一种很“做”的语言,就像在刀锋上走,“做”得好就好,“做”得不好啪的一下就掉下去了。“做”得不好的话就实在是造作,“做”得好的话,也实在是好。
张:他的作品,包括他的文字,和他学的专业有没有什么关系?
王:他曾经公开地讲,他学的是考古,就是历史,学了历史他好像积蓄了很多感情,这个专业已经容纳不下他的这么多感情。我觉得这么讲是对的,而且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也觉得他不是很适合考古,因为考古需要的是一种科学的严谨态度,他太浪漫了,他是个感情很泛滥的人,考古实际上太严格了,每一个东西都要反反复复地证明,而感情是无边无际的。
张:他对历史是有感情的,这也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很多作家对历史没有感情。
王:历史里面的诗意都被他攫取了。比如他学的民族史里面有迁徙,这个迁徙就能够展开很多想象;然后战争,这种东西就是能使人激情澎湃的。
张:你看他写的小说,不管是写新疆,还是蒙古草原,还是宁夏,他小说里面的那些人物,也不仅仅是人物那样的生活整体,总是会给你历史感的。他不是要写历史,但是就是给人这个感觉,这也是我觉得他特别的一个地方。
王:中国历史那么漫长,版图那么辽阔,时间和空间的含量都特别大,就特别能满足他的悲情。还有一点我觉得他比较宝贵的就是,对人民苦难的一种反应。
张:而且特别是对少数民族。
王:他在宁夏调查,准备写《心灵史》的时候,给房东带的礼物我们都不能想象。我们能够想象的不外是给他们带点糖果食物啊,最多带点被子、粮食,他买了头牛,六百块钱。他怀着很美好的感情讲房东家媳妇,将清苦的生活过得很有意境,比如面条,就会擀得又细又长,摆成一个十字,然后中间点一点红的辣椒油,就成一朵花了。
张:他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人。他不写小说也有点可惜。你说的那个很对的,就是他是一个诗人,他不是一个做活的人。
张炜身上最文学的东西就是诗意
张:你刚才说到张炜和张承志关系很好,你怎么看张炜呢?
王:谈到张炜,我觉得他写得最好的还是《九月寓言》。虽然你可以看出他很多地方是学《百年孤独》,但是学得好,它完整,他自己重新塑造了一个村庄。
张:当然这样理解会比较简单,可我觉得他身上有两种性质,一种是《九月寓言》这种,一种是《古船》那种。你看他有的时候讲话也是这样,很幽默的,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他特别可爱;到他绷紧的时候,是那种批评啊、愤怒啊。他一旦松弛下来,就特别有意思。
王:他身上最文学的东西,就是诗意,他也是一个抒情诗人。我特别喜欢他写那些果园里的、海边的小女孩。我和张炜说,我发现你写的小女孩,都是那种小小的、乖乖的、特别美好的女孩子。一旦他写到这种情形下,文笔也流利了,情绪也变得非常的轻松快乐。
《九月寓言》是他最好的小说,将他的诗情最大规模地表现出来,《外省书》也不错。《外省书》还是在《九月寓言》那个系统下面的。《外省书》里面,他要批判的东西太多,有个批判其实很好,可是似乎资源不足,很有意思的是关于“普通话”的批判,可惜没有充分表达。
他很想把生活当中现实的细节诗意化,在《九月寓言》里做得非常自如,到《外省书》就做得有点生硬。但是无疑,他是我认为的正面的作家,有美好的情感。“美好的情感”这个话现在已经被批判得没什么价值了,可事实上作品的好和坏一定是这上面来见分晓的。
史铁生是那种思想很有光彩的人
张:还有什么人对你很重要呢?
王:史铁生。我说我第一次是在讲习所看见他,后来我上门去看他。我是非常勤快地往史铁生家去的,大概都超过了史铁生自己的预想。到他家去特别放松。
张:为什么要去呢?
王:首先他是一个不大方便出来的人,你要见他就要上门去,他有很严格的作息制度。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吧,他父亲出来就挡我们,不让我们进,今天不是接见时间,这时候史铁生在里面大概听到我说话的口音了,他晓得我是从上海来的,他就给他爸爸一个暗号,敲敲玻璃窗,他爸爸就放我进去了。那时候冬天么,我就看史铁生的家里也没有暖气,烧的是炉子,他那时还没结婚,还没女朋友,穿得挺单薄的,我回到上海就给他织了件毛衣。
张:那是哪一年?应该是比较早的。
王:八十年代中期吧。我就觉得要讨好讨好他,从此以后他爸爸就不拦我了。他父亲连我叫什么名字都搞不清楚,只知道我是上海来的,给史铁生织毛衣的。有一次,我和史铁生还有他爸爸三个人在吃晚饭,那时刚好是奥运会,三个人就看奥运会,他们家的电视机破得不得了,必须要有一个可乐罐钉在上面,还要用手扶着它才有图像。
张:哦,那是1988年的时候。
王:1988年,吃饭时候,杨文意得了一个奖,正好从游泳池里钻出来,他爸爸就说你看她,和你名字一样。史铁生说人家叫王安忆,不是杨文意,名字都没搞清楚。他爸爸那个时候已经对我大开绿灯了。我爱上他家有很多原因:第一我觉得到他家去真的很放松;还有我就觉得与他个人的魅力很有关系,你渴望和一个人接触,这个人肯定是有魅力的。
张:什么魅力呢?
王:他是那种思想很有光彩的人。他也是可以谈话的,可是和他谈话要辛苦得多,他会进入一个玄思的世界,因为他是没有什么外部生活的,他的外部生活非常非常简单,所以你和他谈话很快就到形而上去了,你就跟着他形而上,很辛苦的,就像看他某些小说一样,但是很有乐趣,真的很有乐趣。像有的时候他讲一些比较现实的事情吧,倒觉得挺没意思的。
张:他是一个内心想事情的人,想得很多、很深。
王:2003年我到北京开政协会,我到北京第一天晚上就跑他们家去,一起出来吃晚饭,他突然之间要给我们讲笑话,这个笑话讲得又长又没味道,他就自己一个人在那笑,我们也不好意思不笑。我就觉得他讲一个比较现实的事情反而就很无味,但如果他要给你讲他的思想,就会讲得非常有意思。
他有很多看法就和我们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他所有的看法都是他自己思想的果实,不是说看哪本书啊,都是他自己挖掘出来的,他自己慢慢推理推出来的。他的思想和别人的那么不一样,但你晓得是他自己独立思想的结果,独立搞这种东西。
史铁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有的时候你和他在一起会觉得他很健康,觉得他很健全,你不觉得他有什么缺陷,他有一种思想上可以不断激发人的力量。史铁生就是一个偶像,你觉得不能和他有过多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