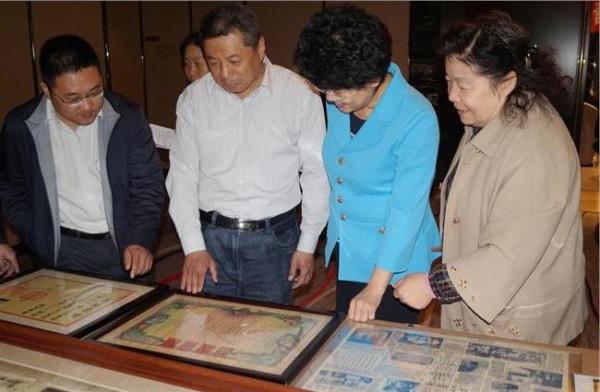周宇驰子孙 周宇驰之女回想录:四十年有感
向红,退休干部。周宇驰(九一三作业之前的空军司令部党委单位副主任)之女,1970年入伍,九一三作业发作时未满17岁,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读书(工农兵学员)。
“十年存亡两苍茫。不思量,自难忘。”
如今四个十年曩昔了。每年的这个日子,我会和许多受九一三作业牵连的人相同,浮想联翩。在40年前,我就现已了解:政治上的我,现已跟着我爸爸死去了。
关于“九一三”,的确是一个令我难以逃避又难以掌握的出题。鉴于我爸爸在作业后现已被官方的广泛宣扬、批判而为全我国众所周知,40年来我一贯在探寻爸爸怎样会走到那一步的心路历程,我想测验一下谈谈自个的所知、所感、所想。
我对前史知之甚少。我认为:研讨前史即是要细,由于通常细节致使拐点或骤变,所以点点滴滴,都要记录下来。作为自个回顾前史,又不能只看到一家一户的悲欢离散。尤其在这个作业上,要学着站得高一点,离自个的利益远一点,去看国家、民众的利益。
听我奶奶说,咱们的爷爷很早即是地下党,后来参与了八路军,一穿戎衣即是干部;曾任四野某部的后勤干部,一贯跟着四野打到广东。我爸爸从小当过孩童团长,在XX中学毕业,入伍的前一年就入了党;他是搞宣扬身世,入伍后不久在四野某部曾任干事并兼职战地记者,身上有两处辽沈战役中弹片留下的伤痕;组成空军时他地点的那个团去了空军榜首航校,仍是搞宣扬。
他是个政治上很坚决,作业上很有才干,性情上很活泼,很恳求进步的人,所以才被挑去给刘亚楼司令员做了几年秘书。
我的小学阅历,由于爸爸的作业调动被分红了三段——从一年级下学期刚开学,咱们家就从北京搬到了上海的空4军,住在4军军部对面门诊部的宅院里;四年级暑假前,又搬回了北京空军司令部大院。
去上海是1963年头,走的时分恰是北京最冷的时节,大人的脸上也没有笑脸,我模模糊糊听见啥“刘司令发火了”之类的话,给我的感受,我爸爸是犯了啥过错。
记住刚刚到上海,咱们都住校,奶奶在家,母亲在门诊部上班,爸爸却去了一个很远、很艰苦的当地,很少回家,回来了也是露宿风餐,带着股乡村的稻草滋味,人又瘦又黑,但心情丰满,他一回来就讲许多和兵士在一同的趣事给咱们听。
咱们就又能听见爱洁净的母亲数说他脚臭,把他的粗陋行李拎到门外,要消毒。他看着母亲那仔细样儿,还成心逗她。有爸爸在,家里老是充溢了高兴。后来爸爸不再去外地了,他和母亲在虹桥机场的空二师作业,在那里又安了个家。
大约是19XX年,咱们上的部队后辈小学接纳当地生源今后,咱们开端走读。但是周末都会坐着部队的大卡车回虹桥机场,从江湾邻近的校园到虹桥机场,要穿过全部上海市区,孩子们一路上说说笑笑,一路高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咱们高举XX的火把,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
XX前辈挥血汗,创立了咱们的好江山,咱们继往开来,建造这夸姣的乐土……”十分高兴,母亲也觉得在上海的那段作业日子,是她最轻松惬意的。
再回北京时,大约是1966年5月下旬。“五一六通知”现已传达,在快要脱离上海的日子里,有一次我跟着爸爸在空2师的干部食堂就餐,广播里正在广播《人民日报》的啥社论。爸爸停下了筷子,侧耳倾听,一脸严厉。
咱们到了北京,还在车站等着获取行李时,我觉得口干舌燥,鼻子就俄然流血了,母亲说是气候太枯燥了的因素。在上海市通常话竞赛得过奖的我,拿着钱去买冷饮,一点点没想到当我习惯地说“棒冰”时,却遭到了讪笑:啥呀?这叫冰棍!这两件事使我对北京顿失好感,如今想想,几乎像是不祥之兆。
如同是王飞伯伯和何汝珍叔叔来接的咱们。我对何叔叔很感兴趣,由于在上海时我看到他写给爸爸母亲的信,字写的十分规矩秀美,因而记住了他的姓名。关于为何要回北京我很不解,我现已习惯了上海的日子,对校园很不舍。后来我跟王飞伯伯提起此事,他说我爸爸脱离空司今后,他们俩一贯坚持通讯联络,前后长达三年多;后来爸爸调回北京,也是通过他们劝说才赞同的。
我了解爸爸参与XX以来一贯对XX作业抱有极大的热忱,赤胆忠心,活泼尽力,体现优良,才会被挑选去司令员身边作业。爸爸很正派,他不想回北京,是悲伤了。后来我总算了解了爸爸为何调来调去。
他给刘亚楼当秘书时,有一次上午到的大开本“参阅音讯”,他下午才送给刘司令看。刘批判了他。他解说,这仅仅一本参阅音讯,不是文件,并没耽搁作业,遂不愿认错。刘的性情很出名,他岂能容许他人辩驳和贰言,尤其是自个的秘书!
就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再次批判我爸爸,如同说他作业“踢皮球”。但我爸爸也很倔,有些不识时变,坚持不认错,刘亚楼大为光火!我爸爸那时是少校,刘为此在空军就出台了一条新政:但凡少校军衔没有担任过指导员或教导员等职务的,一概下放一年,补课。这即是我爸爸后来下放到江苏盐城高炮某部,担任了一年营教导员的要素。
据我哥哥向阳了解,文革前我爸爸从前被借去上海党校讲过课。我也记住他在空2师五大队当政委的时分,五大队这方面的宣扬搞得绘声绘色,我爸爸和飞翔员的联系极好,常常谈心。爸爸还有副好喉咙,他喜爱唱《XX人永久是年青》、《咱们走在大路上》这一类激扬、向上的歌曲。
文革时期他被评为空军的“学习毛主席作品活泼分子”,在大院里讲心得。他身体很棒,在一航校时拿过东北军区速滑的名次,刚回大院还在灯火球场打过篮球,那应当是树立果还没到空军的事了。
于新野叔叔的爸爸母亲都是新四军,是ge命老干部;解放后他爸爸是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的创办人,后来担任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理论修改部的领导,1958年支边调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作业。
我也还明晰地记住树立果刚到空军时,穿戴新戎衣,寡言少语地坐在我家床边上看着我进来,一副不知所措的姿态。后来他老练了,也胖了,一瞬间像个干部的姿态了,到哪儿都能听见讴歌他爸爸和赞许他的话,每当此刻,他只微微一笑,点头致意,应付自如,并不张狂,平常仍然寡言少语,如同老是有事可做,从未见过他懒散的姿态。
记住是1970年5月20号,那时我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医疗系读书,那天早上程洪珍开车到校园,把我接去度周末,“调研小组”的人其时都驻在广州白云山机场招待所。
由于他们那里能够看到香港报纸和许多的外国杂志,我去了就会翻看,对报纸上连载的言情小说很痴迷。一个上午,他人都各自繁忙着,洗衣机放在陈伦和房间的清洁间里,轰隆轰隆地响,我猎奇地去看,趁便帮助。
他们住的楼层上有一个大饭厅,里边有部电视机架在那里,平常咱们能够聚在里边看电视。那天我看见饭厅没有人,椅子都折叠好靠在墙边,只留了一把椅子正对着电视机摆放着,不知是几点钟了,电视里开端转播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办的毛宣布“五二〇”声明那个大会,我坐在椅子上看了看,就走开了。
一瞬间,该林彪说话了,树立果从房间里出来了,有人很默契地开了瓶桔子汽水递给他,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专心致志,边喝边看,他人都走开了。
我见咱们都不进入,也欠好轻率进入,就在门口看了一瞬间,记住了林彪代读那篇毛声明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个“助”字的湖北口音特色。林彪讲完话,大会还没完毕,树立果就站了起来,仍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回房间了。我目击了这一切,就自个一自个想入非非起来——不是说干部后辈应当谦善吗?他只听自个爸爸的说话,算啥呢?但是他爸爸是林副统帅呀!……
要是我爸爸在台上说话,我好欠好意思听呢?后来跟树立果碰头次数许多,也没数过,但仍然彻底不能把他和《“571工程”纪要》联络起来。所以咱们一贯在想:是啥让我爸爸从当年一个学习毛选、宣讲毛选的“活泼分子”,和那些空军党办的高手们,成为了后来的他们?能够说他们都现已有家有业,也有必定权势,他们还想干啥?怎样就情愿冒死跟着树立果干出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作业来呢?莫非是贪心更多的权益?莫非是脑子一热、自我胀大,或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树立果折腾啥呀?林彪不是现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吗?
我了解地记住1971年的9月5号,是个周日。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我像平常相同,和要好的几个同学去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家里玩,首要为了能解解馋。校园把咱们部队学员的膳食费和当地同学平摊在一同,所以膳食欠好,咱们这帮孩子正在长身体,食欲大得吓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惯广东的大食堂。
忘了是饭前仍是饭后,女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聚在客厅说笑着,顾伯伯把我独自叫到客厅外面的走廊,脸上还挂着和咱们谈地利的笑脸,四顾无人,很亲热又奥秘地压低了声响,说:你爸爸12号就要到广州来了!
到时分我派人去校园接你!我不太了解他为何这么,但由于他一贯很关怀我,跟树立果他们联系又好,在那时“亲不亲,线上分”的政治观念里,他和我爸爸是一条“线”上的,也许是想逃避不让别的同学听见;所以我很有礼貌地应合着,容许了,但心里仍然感到少许疑问——广州是爸爸常来常往的当地,这有啥好奥秘的?也就认为他是一片好意,了解咱们父女的豪情,所以当成个好信息通知我。
过后才知道,本来就在那两天的前后,刘兴元(广州军区政委)给广州军区传达了毛南巡“吹风”的内容。12日我没有请假外出,怕来人找不到我,一贯在校园等音讯。但并没有人来找我,也没有电话来,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格外古怪,由于我现已习惯了树立果和爸爸他们奥秘、机动的作业特色,横竖我也没啥作业要办,恰好歇息一天。
我在校园只接过母亲打来的长途电话,但我打不了,所以我也没打电话给任何人。
大约过了一星期摆布,同学汪京群(汪d兴的女儿)吃完晚饭和我在校园里漫步。她悄悄地通知我:一个大官坐飞机跑了,不知所终。咱们俩就放言高论地猜测,会是谁呢?本来我底子无从猜起,都是听她说。终究她说,也许是许世友!
这自个最不听招待了!我底子对“跑了”没有任何概念,对基地的作业更是一头雾水,所以听了京群的剖析,就觉得有道理,风闻许世友的脾气很大,谁也不服,随身老带着枪,文革时期就从前跑到山里躲了起来;所以这次“跑”的很也许是他。
当年在广州听完传达“九一三”的基地文件,我和全国人民相同,没有一点思想预备,更不会想到此事和自个有关,尤其是文件说他们都死了,我底子不信任,听文件的时分感受头晕耳鸣,全身麻痹,脑子里榜首个想到的是:“这是‘笔杆子’在搞鬼!
”我周围坐的是校园里睡我下铺的广空副参谋长的女儿,她悄悄地问了我一句:那个周啥的女儿是谁呀?我挣扎着答复:是我……声响极低,极粗,极哑,底子不像我平常。她必定是被我吓着了,立刻搬着凳子往周围挪了一下。
听完传达文件,李X念接见咱们这些爸爸在文件上被点了名的子孙。他特意点了我的名,他问我:你能不能像树立衡那样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啊?你要是知道了他们的诡计,你会怎样办呢?向谁告发啊?我底子答复不了这种疑问,但全场的人都在盯着我看,我牵强站起来,眼冒金星,感受喘不上气来,眼前黑漆漆地一片人头,我跳过了前两个疑问,朝着两步远的李X念,对他提出的“向谁告发”这一疑问,哑着喉咙说了三个字——吴法宪。
然这个答案令他很不满足,他也不让我坐下,就转过脸跟别的一个方向的子孙们讲起话来。我既严重又十分为难,也不知道自个错在哪里。方才听文件的时分模糊感到吴司令这次也要垮台了,但我说的是真话,谁让我听见树立果他们背后跟吴法宪叫啥“吴胖子”呢?谁让我啥都不知道呢?不向他告发向谁告发?空军大院最大的干部即是他嘛!
况且我在广州上学,更不知道该怎样告发;就算我去过几回毛家湾,但都是坐车去的,底子不知道地址,再说这次连林彪也死了呀……
广州军区托付广东省军区把咱们这些子孙留下办学习班,而这四天我自闭了,像张春桥在格外法庭上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学习班完毕的总结会上,别的子孙代表都表了态、标明紧跟、要划清界限等等。我则被广州军区政治部于主任点了名,“风闻这四天学习你没说过话,你是怎样想的?今日你要表个态。”我一咬牙站起来,倔倔地说了两句——
基地文件是机器印的!
我要看温都尔汗的相片。
这两句和其时会议氛围截然不同、彻底逆反的话,让于主任措手不及、极为不满,成果可想而知。从此,就给组织上留下了我“心情欠好”的史话。
以至于1974年我复员后被空军流放到南苑空司生产队去,时任空军司令员马宁去那里劳作遇见了我。一开端认为我是哪个空军招待所去南苑轮番劳作的效劳员,吃午饭时还专门坐过来,和蔼可亲地跟我谈天,问东问西。
但是,我忧虑的作业仍是发作了——生产队长在一旁陪坐,几经犹疑,仍是很为难地当着我的面把我的身份通知了他。这个马司令当即把碗往桌子上一放,对我争吵了!大声呵斥道:你要划清界限,好好改造!
我也把脸一绷,二话没说站起来,把没吃完的饭菜往碗里一扣。在世人的凝视中凛然离去。死后的食堂里一片幽静,万籁俱寂。过后我越想越失望:我到底是谁?我代表我爸爸吗?我竟如此之臭名昭著?空军司令竟如此没有水平?“党的政策”竟如此之悠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