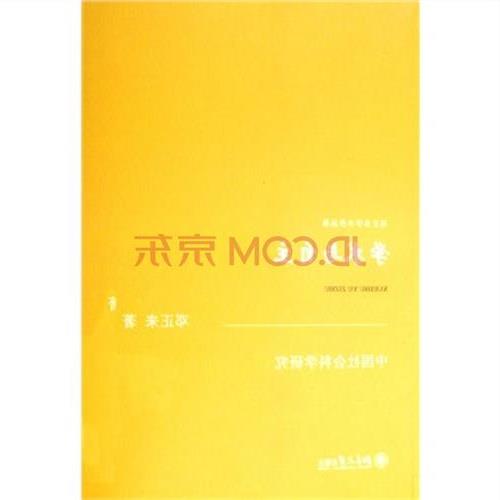倪鑫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张立波:找准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的交汇点
20世纪以来,通过参照现代西方的哲学和史学构架,“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脱颖而出。然而从一开始,就有学者认识到作为现代产物的“中国哲学史”的局限和不足,因而坚持“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中国思想史”的这一取向较多地接续了传统历史研究的方式,思想史因而得以作为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而存身,但也由于其不合乎现代史学的科学规范而在较长时期内被边缘化。
相形之下,“中国哲学史”自20世纪以来就一直作为“显学”而存在。然而,近十多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成为学界讨论的问题,从属于哲学学科的“中国哲学史”也引起了一系列争论。应当承认,“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过程,的确存在用各式各样的西方哲学范式剪裁中国思想史料的行为,但并不能由此彻底否认“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否认“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事实上,只要坚持本土化的立场和中国学术的民族性、主体性,我们仍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这样的概念,致力于探索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和治学之道,以及传统哲学在近代的转型过程。
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思想史研究近年来愈益兴盛,颇有涵盖哲学史之势。无论是作为概念还是范式,“中国思想史”都比“中国哲学史”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本土性,充分彰显了中国学术思想话语对独特性的吁求。但哲学史的观照依然有其必要,因为哲学史的角度比思想史更具穿透力,更能洞见思想历程背后的民族文化精神。
这样看来,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都是构建中国本土哲学学科与历史学学科的内在动力。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用一个否定另一个,而是找准二者的交汇点,促进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对话沟通。
思想史与哲学史研究,在思路与写法上完全可以互相嵌入、交相辉映。如果说“思想史”大体可以等同于“观念史”,那么进一步分解,“观念史”可以等同于“理念 生活”,以提炼“理念”为宗旨是哲学的特点,以显现“生活”为旨趣是历史的特点。
哲学重在“说理”,但离不开以“讲故事”为手段;而历史重在“讲故事”,但也需要借事说理。因而,哲学史可以具备历史的形式,展现严密的思想史考证与清晰的叙述脉络;思想史亦可以体现抽象思辨与哲学关怀。
例如,在笔者看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名为“哲学史”,其内容和研究方法实际上更像是“思想史”,这也意味着,冯友兰是以哲学的方式来写作思想史。其实,思想史与哲学史完全可以互相开放,产生“哲学的思想史”或“思想的哲学史”。
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另一个交汇,就是它们最终都归结到民族精神这一主题。中国哲学与中国史学从根本上讨论的都是民族精神问题。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在根本上就是讨论中国哲学之精神的历史。同样,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史,在根本上就是讨论中国史学之精神的历史。
无论中国哲学之精神还是中国史学之精神,都关乎中华民族之精神。即我们这个民族是从哪里来的?一步步怎么走过来的?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未来又当何去何从?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所思考的、所回答的,也就是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哲学史也好,中国思想史也好,无不是在重构的意义上接续传统、创造新知。例如,在中国思想史的书写中,“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相辅相成。所谓“我注六经”,是指一个活生生的“我”在诠释“六经”,“六经”由于不断的重释而愈益丰富;所谓“六经注我”,意指“我”是“六经”的产物,经由“六经”不断的疏导,“我”这个主体不断完善。
“六经”的丰富和“我”的完善,就是民族精神的宏阔和民族本身的圆满。
思想史所体现的文化自觉深刻影响哲学史。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传统史观具有崇古、怀古和信古的特点,因尊重远古而记载和保存历史与先哲论述,因为坚信鉴往能知来而殚精竭虑地爬梳史实。20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虽然并非简单的回溯式、还原式研究,但却具有明显的守成和持重的质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化自觉起步的征兆。
这种变化,势必影响到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与哲学史的写作。在这种文化反思的自觉中,应当越来越多地包含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对中心和边缘的清醒,以及对碎片重组的探求。
思想史与哲学史都具有开放性。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的旨趣,不在于形成一个封闭的、完美无缺的体系,而是力求面向未来、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基于这样的思路,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研究的拓展,将有赖于中国哲学和史学研究的拓展。哲学研究上的返本开新,史学研究上的革故鼎新,都将有力地参与和助推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