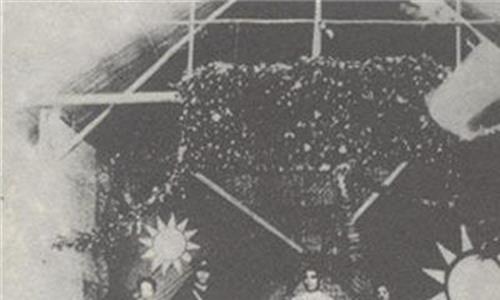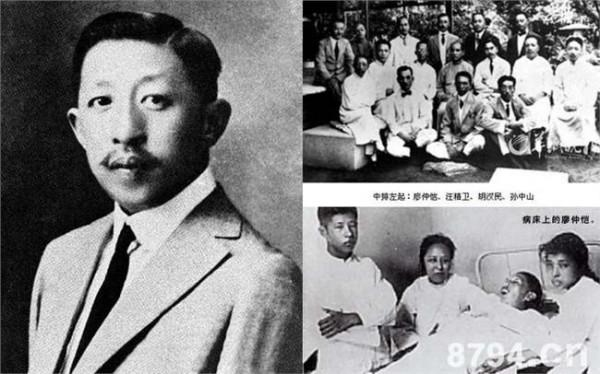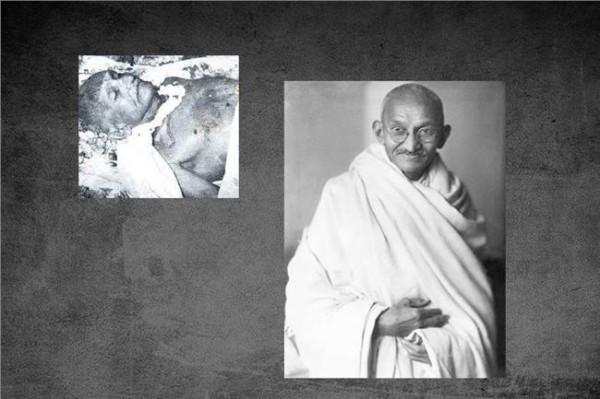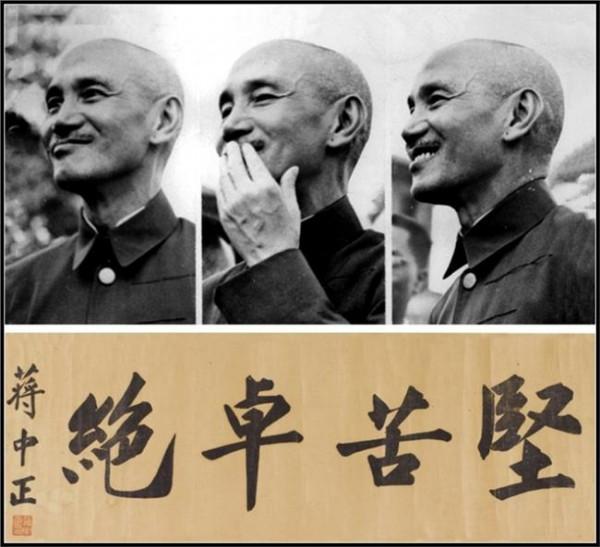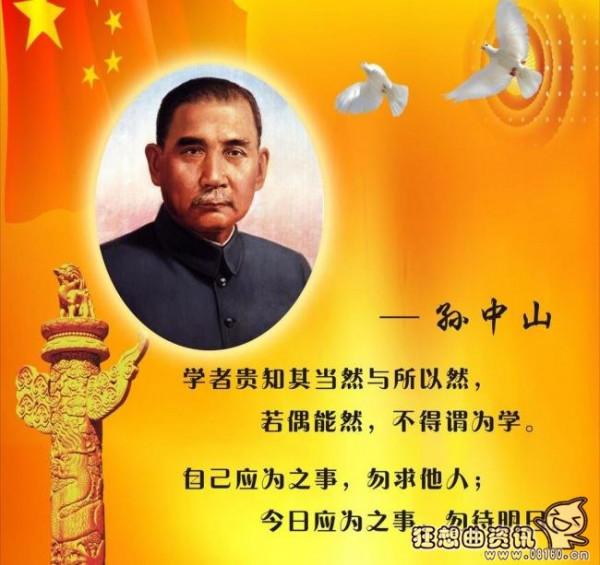蒋介石如何评价张治中 张学良如何看待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专用奴才
原标题:张学良如何看待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专用奴才
国民政府内部的高官们只是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中原大战之后,张学良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但他因军务在身、下野出洋和身体等原因较少出席会议。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段经历。
在此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说:“我不会外交辞令。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国民政府军队的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的老政客更腐败。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张学良通过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看清了国民党中央高官们的真实面目: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尽在那儿做打油诗。”“我不晓得谁做的了:‘一生猪狗熊,两眼财权势,三是吹拍骗,四为礼义廉。’”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层如何可想而知。
在南京期间,发生了中央党部事件,即汪精卫遇刺事件,这件事对张学良刺激尤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幕式那天,与会人员集体照相,“本来大家在外面等着蒋先生出来照相,后来说他不来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开始照相了。
相照完了,大家正要离开时,刚转身,枪响了。这一打枪,大家‘哗’的一下子都散了。”“都吓跑了,连警察都跑了,什么警卫,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张溥泉(张继)两个人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那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
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警察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
’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那都吓得……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张学良从这件事当中,看到了国民党失败的影子:“要紧的时候人都没了”,“一遇危险,聋子放炮仗——散了”,连中央委员的证件都不敢要了。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战争年代,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民党政策不公,军队分成亲儿子和干儿子,把杂牌军都挤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众所周知,在整个民国绝大多数时间里,国民党军队从人数、装备、控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等方面来看,都远远优于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可就是消灭不了。原因在哪里?除了国民党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还丧失了军心。
国民党是怎么丧失军心的?张学良以自己为例,他说:“当年我开始时,我现在可以说,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
第一,当东北军在“剿共”战场上被吃掉两个师之后,张学良发现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的政策是不一样的。1935年末,张学良在南京参加会议期间,陕西前线传来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他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
“我那两个师整个被共产党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剿共’时受了伤,他说一句话,把我伤心透了。
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只能流亡要饭去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后来,我也公开说了,那个时候中央啊,实在是处置事情不太恰当,完全是一种推诿。因为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起了怨望……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这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比方说那时候中央的事情,后来我发现的,我非常难过。我打仗损失了两个师,政府啊,不容许我们杂牌军队招兵,因为军队太多了嘛,他用这种只减不增的方法就不用裁呀。
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我们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离我们那么近,我们不会不知道的嘛。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张学良发现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张学良说:“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这话我今天可以说,但我不希望记录下来,他就是借刀杀人嘛。
”“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借刀杀人。那为什么还打?没起来反抗,已经很客气了。”“那孟子说的话一点不错:‘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怎么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待你……所以这种待人的法子不会成功,只会失败。”
第三,张学良发现不仅他发现了,几乎所有杂牌军,包括共产党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那时中央不是我说,不公平啊!对人家不公平,谁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时两广是陈济棠,青海是马步芳,宁夏是马鸿逵,新疆那会儿是盛世才,华北是宋哲元、韩复榘,陕西是杨虎城。
他们都不打呀!谁也不打,我打什么?谁都明白了,这等于用外头的力量来消灭我们。打,你不给我钱,你也不给我弹药;人打没了,你也不给我补充,又不许我自个儿招兵,这干什么呢?”“谁也不是傻瓜。
中央军可以招兵,我们不可以,枪械损失也不给补充。你政府用这种手段,等于让杂牌军自消自灭,一箭射三鸟,他怎么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咧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国民党中央政策不公,导致“剿共”内战谁也不真打。“我一想起这内战,就难过呀。所以西安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那就是叛变呐。”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产党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
国民党的失败,在张学良看来,败于党员信仰的缺失,也败于民心和军心的丧失,更败于党内的腐化及蒋介石的独裁。
张学良在晚年做口述历史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王新衡对奴才的理解是:“奴才就是听他话的,让他高兴的人。”张学良对奴才的理解与王新衡略有不同:“我说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不一定给你当奴才。
奴才最大特点就是我要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他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
’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去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
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呐。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张学良说蒋介石心胸狭窄,不仅用人专用奴才,而且把自己的权力看得过重。西安事变前,“我和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
……他和我的出发点不同,从个人出发点说,先说我啦,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即使共产党跟我们争,他还是中国人。他(蒋)认为日本人可以跟他合作,共产党是他真正的敌人。……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
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这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在肤施(今延安)会谈,“周恩来有一段话说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呀,固然蒋中正他有他的短处,我们对他不是十分赞成,但是我们为抗日非拥护他不行。所以共产党这些地方我佩服,他是为了大局呀。他说,蒋先生如果不‘剿共’,领导全国抗日,还得是他”。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张学良的意思是说,蒋介石没有大局观念,只用奴才不用人才。(王海晨 杨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