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菲菲出家 杨菲菲:我眼中的客家人
内容提要:他曾是一个非常洒脱和叛逆的青年,以前我一直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能忍受庸俗,以他以前的性格他定然能超然脱身而去的,我看到他痛苦,有时我甚至认为他软弱了,要知道哥的形象从小在我心目中一直是最完美最高大的,所以后来慢慢的他不再是我的偶象,不再是我的英雄了。
直到长大后,我也成家,我也得像成年人一样背负责任背负仁义背负等等无形却沉重无比的包袱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哥,尤其当我深深体会到自己是客家人的时候,我能想像他身上的沉重即使倾千分之一到我身上,我都会累趴的。我才明白,我之所以轻松,因为有哥担着。
(昨天看了雪漠老师的那篇“甘肃的‘杂种’文化”一文,不知道是因为看到了一种陌生文化的新鲜感挑引起了我对地方文化思考的链条,还是因其文中浓浓的既亲切又熟悉的地域情感而激荡起我对自己家乡文化的比较和反思,我突然有了写下自己作为一个客家人对“客家”的理解和感受的冲动。这是我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念头。)
我是一个客家人,虽然从小在城市里长大,被侵入了满身的城市气息和习气,但我明明知道自己骨子里还是个客家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在外表看来我和身边的朋友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我知道客家人的信息埋藏在我的DNA里面,它只会在我的生活细节、世界观、思想的深处像暗流一样涌动,一般是不会浮出水面的,甚至我极少在外人面前讲客家话,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因此判断我,端详我或窥视我。
对于外界,我总觉得知道我的信息越少越好,这样我就能更安心地建筑自己的世界,它才能更隐匿更牢固更缤纷。
在城市长大,我从小就远离家乡,而且因为是女儿,全家三兄弟姐妹中我排最小,我总在各种客家传统礼仪和礼节上被忽略和排除在外,所以其实我对客家大部分文化风俗等等传承都一知半解,了解甚少,但尽管如此,我却清清楚楚自己和别人的区别,清清楚楚那客家人的基因在我身上继承了下来,所以,我知道,我便是客家,客家文化不在于礼节,不在于风俗,而在于某种观念,某种品质以及某种难以言说的情感的代代相传。
我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客家人家庭,父母都是典型的客家人,他们的家乡是很近的两个客家乡村,以前客家人很讲究,客家男人都要娶客家的女人,但客家的女人是不是一定要嫁客家男人,也许就没那么严格的要求了。
总之我哥哥当年谈恋爱时,听说他女朋友是广西的,再贤惠再漂亮,爸妈就是不喜欢,结果哥真的放弃了那女孩,选择了跟我们同一个家乡的女孩,爸妈便马上同意婚事了。而对于我,爸妈似乎倒无所谓了,他们从没跟我灌输要嫁哪里人,因此我长大后对婚姻的观念非常自我非常独立,由此可见,客家人因为重男轻女,重传宗接代而对于女儿的婚姻是相对没那么重视的。
嫂子虽然是客家人,对家里的操持能力也是异常强,但是跟我们家里的相处却不是很好,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全家跟嫂子的关系是极其恶劣的,哥就像处在拔河绳的中央,偏向我们,他的日子始终是跟嫂子过的,若偏向嫂子,我知道他对父母的孝心会让他深受折磨。
哥就在这种矛盾中把他人生中最黄金的时期全耗尽了,由热血沸腾的青年直奔庸碌的中年。他曾是一个非常洒脱和叛逆的青年,以前我一直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能忍受庸俗,以他以前的性格他定然能超然脱身而去的,我看到他痛苦,有时我甚至认为他软弱了,要知道哥的形象从小在我心目中一直是最完美最高大的,所以后来慢慢的他不再是我的偶象,不再是我的英雄了。
直到长大后,我也成家,我也得像成年人一样背负责任背负仁义背负等等无形却沉重无比的包袱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哥,尤其当我深深体会到自己是客家人的时候,我能想像他身上的沉重即使倾千分之一到我身上,我都会累趴的。
我才明白,我之所以轻松,因为有哥担着。
在客家人的观念中,最重的是家。客家人是为家而生存的,家就是生存的理由,我妈如是,我爸如是,我哥也如是,我想我也如是。为了家的完整和延续,客家人能放弃一切,包括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追求,自己的一切,为的只有一个目的——让“家”延续繁衍下去。
因此,我们非常注重传统的节日和传统的礼节,因为这些传统节日和礼节是熏陶家庭气氛,浓重家庭气息的重要依托,一个客家人,无论是长年漂泊都一定不能淡泊家的观念,所以尽管嫂子跟我们关系不好,仍然得恪守逢年过节回来团聚及其它传统的礼节。所以,其实很多所谓的礼节和礼仪根本不是重要的,它们都是为了客家人的最终目的服务的形式而已。
说到家,客家人对家的概念可能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我们有“小家”,即是自己最直接的家庭成员,但小家之上还有一个“大家”——即同族,那是由家族血缘关系延伸出来的千丝万缕的说不清的亲戚关系,而且对于客家人来说,好像所有亲戚都是相当亲近的血脉,即使绕得跟打了死结的绳头一样,最终只要能揪出在某一代同宗,就列入自己的同族,也就成一家人了。
客家人只有男丁才能入族谱,而且祖宗祭祀也只要求儿子或男孙,我长这么大了,至今都没到过祖宗的祠堂,所以所有的祭祀仪式,同族血缘的亲人关系链等我几乎是一概不知,就好像跟这个家族毫无关系一样,但除此以外,家里人包括其它亲戚对我和姐都是十分痛爱的。
所以这也是我了解哥难以脱身脱俗的原因之一,他不但是男丁,而且是家里的长子长孙,在一个像蜘蛛网一样精密及粘连的辈分尊卑分明的家族体系中必然是众矢之的,肩负家族传宗、承上启下的所有重任。
作为一个客家人,我常常对自己是女性感到庆幸。
“大家”由男性背负,“小家”则由女性来承担。这“小家”的负荷同样无形无影无迹,其重力不异于一座小山,传统的观念以耳濡目染、口耳相传的方式一代接一代传递给客家的女性,因此客家女性也总具备了常人所不能的坚韧和独立性。
在客家女性眼中,她通常把世界划分得相当清楚:第一层是“小家”的家人,她的生命为之而生为之而灭;第二层是“大家”,虽然她在这家族网络地位卑微,但这似乎是直接关乎其声誉与个人价值评判的最直接最权威的小社会体系;第三层是外部没有血缘的外部世界,这一层对于传统客家女性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据我了解,传统的客家女性是很少外交的,因为家族及家头事务几乎不容有外交的时间和空间。
所以在这层面来看,我肯定不属于传统的类别,这也肯定跟我没有跟客家男人结婚的原因有关。
在我看来,客家人的大多优秀品质包括吃苦耐劳、勤俭朴实、仁义孝道以及其风俗礼节、饮食习惯等等很大成分都源自于对“家”的观念,然而成就客家人品质的观念、思想也成为了他们的无形枷锁,男人套大枷锁,女人套小枷锁。
我不是男性,对于大枷锁只能意会和体解,但对于小枷锁,我想我的感受是充分而实切的,因为我妈是典型且传统的客家女人,而我是在她的言传身教下成长的,当然,在我家族里我接触到的女性都有非常接近的特质,所以更确切地说我是在一群客家女性的言传身教下成长,只不过妈是对我影响尤其深重的女性其一。
我们家里,爸主要负责我们的智力培育,而妈则侧重德育的培养,小如礼节礼貌,大如做人的品格及道德等等,妈总像挤牙膏一样在每个生活细节中捉住机会就把她一生所吸收的一切优良品质和教育挤出来给我们,当然与此同时,她还得做好自身的榜样,在生活上忍辱负重,一步一艰辛地咬紧牙关。
小时候我常常听妈叹气,说来世千万不要做人了,做人太累太累,最好能做只小鸟做条鱼,天高海阔的自由自在,我那时小,常常不解,只隐隐约约觉得伤感,但妈仍常说。
客家人是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很贴切的菜可以形容,那就是盆菜:口味重,像我们的人情味一样重;大杂烩,但复杂得来却和谐又统一,相互的味道互相交融;最后还有高度概括的一个特性:同生共死,同甘共苦——这是盆菜给我的主观感觉,正如客家人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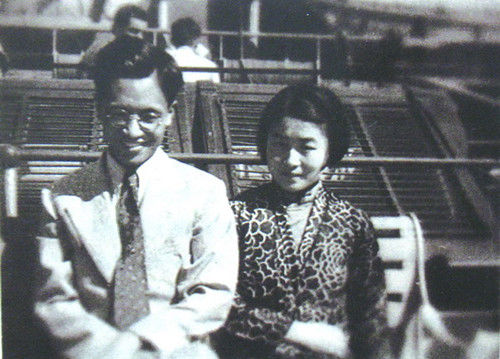


![演员杨清 【演员杨青】杨青[喜剧演员]:杨青[喜剧演员]](https://pic.bilezu.com/upload/b/1b/b1b106919bd6b5fa1a1c37bdc7562836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