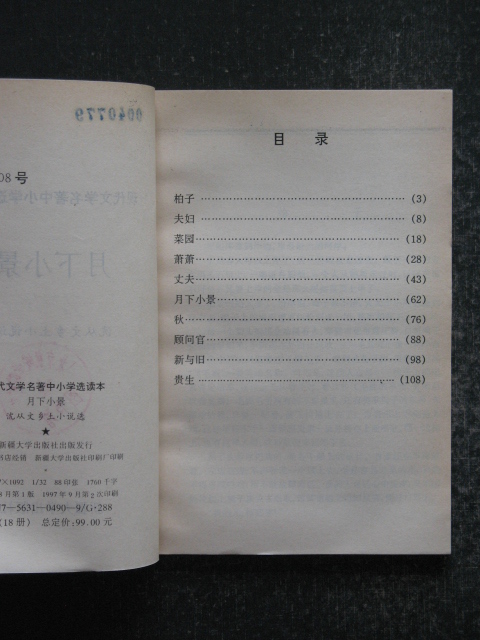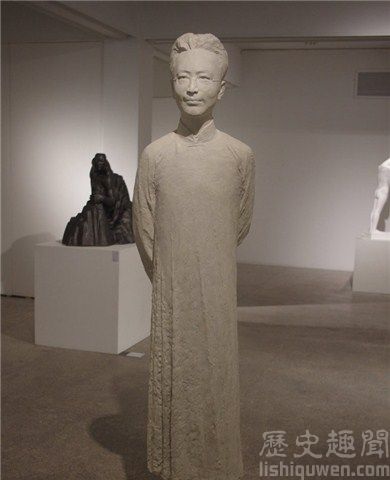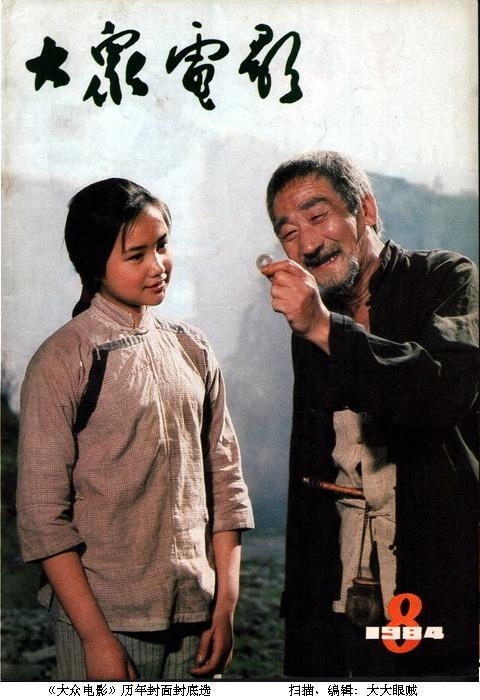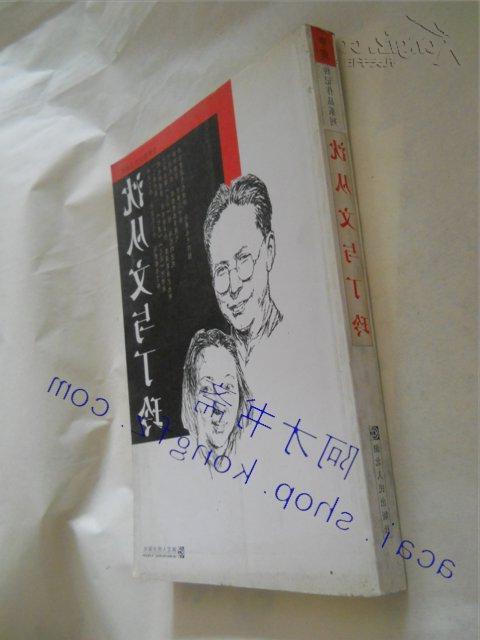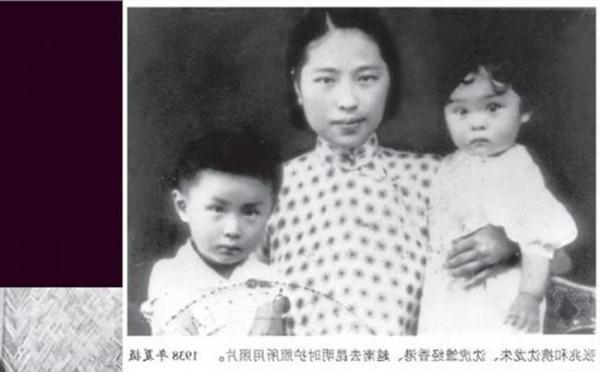师陀散文 沈从文与师陀乡土小说中故乡情结的比较
沈从文与师陀乡土小说中乡下人的比较
沈从文和师陀虽然风格迥异,却都以“乡下人”自居。作为都市里的“乡下人”,“怀乡”是其无法逃避的文化宿命,所不同的是,沈从文一心一意地建构“人性的希腊小庙”,而师陀则始终无法回避故乡衰败与凋零的现实;沈从文寄托他对中国社会人生未来的构想,而师陀则从对故乡丑恶人事的揭露和批判出发,转向了深沉的文化思考,将个体生命的感受与体验与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融为一体。
1.同是对故土的眷恋,沈从文与师陀的情感却不尽相同。于沈从文而言,他在精神上与城市格格不入,故乡始终是他心中最为柔软与纯净的精神栖息地。沈从文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的早期创作多为抒写自我的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
其主人公多为客居北京的穷困潦倒的青年人,他们挨饿、受冻,更没有什么朋友,在都市社会的实利主义中饱受凌辱和歧 视,精神上异常苦闷,我们从中不难想象出沈从文初来北京时的情形。都市的喧嚣、躁动、冷漠无疑使沈从文感到深深的隔膜。
在20年代初期,他写下了一批生动的乡土文学作品,如《玫瑰与九妹》、《腊八粥》、《炉边》等。他写故乡的风俗与美食,回忆儿时的快乐时光,抒发对亲人的怀念,他正是借此满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情感需求,“一条温情脉脉的情感溪流在这些回忆里流动——一种对孤独的、为人情冷漠挫伤的都市生活经历的心理反应现象”。
师陀也批判都市,正是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失望激起了师陀对故乡的诗意怀念,那文明未曾侵染的田园式的宁静始终是师陀文学想象中凝固的华彩。但师陀无法像沈从文一样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一心一意地建构“人性的希腊小庙”,每当他提笔怀念故乡时,那破败萧条的景象便如挥之不去的梦魇萦绕在他心头。
对故乡的衰败与凋零,他感到了难以忍受的失望、压抑和憎恨。新文学的文化怀乡,集中呈现为对于城市的异己感和对于乡村的情感回归,然而师陀却持有双重的批判视角,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喜欢我的家乡,可是怀念着那他对待故乡的情感是极为复杂的,他厌恶这片土地,永不能扎根于其中,却又留恋着这片土地,同情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如果说都市令师陀厌恶,那么故乡同样也不是师陀的精神归属之地。
蛰居在沦陷区的师陀将想象中的“果园城”写得那样美丽而富有诗意,但那仍然不是他可以栖居的“精神家园”。师陀渴望回返故乡,但“无家”却常常成为他笔下主人公的命运。
《狩猎》里的孟安卿回到阔别十二年之久的果园城,却已没有人认得他,昔日爱慕的姨表妹也早已嫁作他人妇;《结婚》里的胡去恶离开了乡村的纯朴爱情,一脚陷入都市的泥淖,他既不可能再回归乡村,也不能继续在都市的冒险;《荒原》里的顾二顺和娇姐于乱世之中渴求一个安宁的家而不得⋯⋯在师陀那里, “ 故乡”与精神栖息之地——“家”是两个概念。
正因为如此,师陀更像是一个人生路上的跋涉者,他更多地感受到的是时光的流逝和生命的寂寞。
2.对于故乡的人民
在沈从文笔下,湘西山民的生命以雄强、热情与野蛮的形式出现,他们“能吃、能做、能喝、能打架”,勇敢、结实、精悍而性情欢乐。沈从文写湘西土匪的奇特经历,表扬他家里那些勇武好战、光明磊落、正直打仗的汉子;写男女之间自由、蓬勃、充满活力的爱情,“把男女爱慕写成是太阳和暖引起的自然反应,那时雨后新晴,蕨草冒出了卷曲的新芽”
师陀最初写乡土,更多地是源于对中原大地灾难深重、痼疾难复的切实感受。他在思想上倾向于左翼,痛恨现实社会的黑暗不公,同情挣扎在痛苦与血泪之中的老百姓。现实丑恶的暴露、人事的荒谬与无意义、生活的阴暗与丑陋,这一切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师陀笔下乡土的全部内容。
以持审视反思的眼光,对乡野村夫愚昧麻木的精神病象进行讽刺和批判,思 考着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人的生存的境遇。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故乡:“在那里,永远计算着小钱度日,被一条无形的锁链纠缠住,人是苦恼的。要发泄化不开的积郁,于是互相殴打,父与子,夫与妻,同兄弟,同邻舍,同不相干的人;脑袋流了血,掩创口上一把烟丝:这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