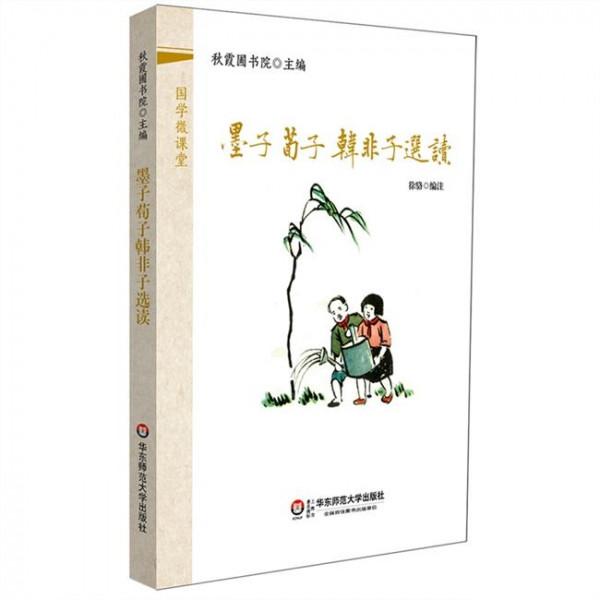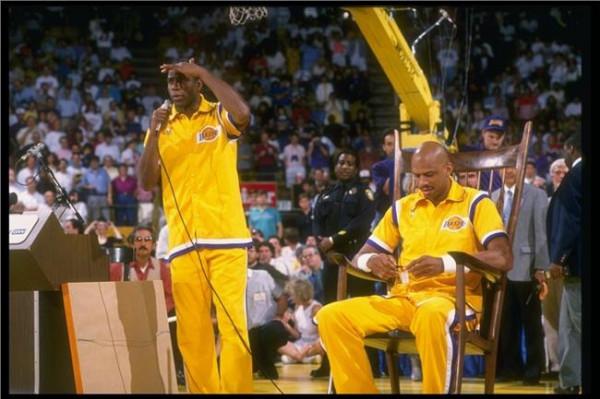郭齐勇的学界地位 郭齐勇:试谈荀子的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
摘要:现代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评价了荀子,为我们提供了讨论的基础。荀子超迈前人的学术贡献表现在天人关系、人性学说、社会理论与礼治建构、认识论与逻辑学等方面。他是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集大成者,是经学大师,对礼乐有大的发明。
他针对时代提出的问题,全面地丰富与发展了儒学与中国哲学。他是现实主义儒学传统的奠定者,在外王学,即统一中国及其制度文明的理论设计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方法论上他着力发展了分疏、析别的思想传统。荀子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后世对他的不同评价正说明他的思想张力巨大。对荀子的批评史也成为荀学思想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荀子 儒家 礼治 学术贡献 历史地位
荀子是中国文化史、学术史、哲学史与儒学史上的大家,贡献卓著,影响深远。如何评价、定位荀子,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谈到荀子,就不能不涉及到孟荀关系、儒法关系、荀子对中国文化的各方面影响。从汉代刘向到唐代韩愈,宋代王安石、苏轼、程颐、朱熹,明代罗钦顺、黄百家等,都对荀子有严苛的批评。
我们先看看现代一些学者是如何评价荀子的。他们从不同视角检视荀子,为我们提供了讨论的基础。冯友兰说:“孟子以后,儒者无杰出之士。至荀卿而儒家壁垒,始又一新。上文谓中国哲学家中,荀子最善于批评哲学。西汉经师,亦多得荀子传授。盖其用力甚勤,学问极博。”[①]
张岱年说:“孟子所谓性善,并非谓人生来的本能都是善的,乃是说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要素即人之特性是善的。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生来即有仁义礼智之端,故人性是善。荀子主性恶,认为人之性是好利多欲的,性中并无礼义,一切善的行为都是后来勉强训练而成……人有善之可能,是荀子所承认的。
但何以仍讲性恶……荀子所谓性,乃指生而完成的性质或行为,所以说是‘天之就’,‘生之所已然’,‘不事而自然’。生来即完具、完全无待于练习的,方谓之性,性不是仅仅一点可能倾向;只是一点萌芽,尚须扩充而后完成的,便不当名为性。
生而完成者谓之性;生而不论有萌芽与否,待习而后完成者,都是伪。由此看来,荀子所谓性,与孟子所谓性,实截然两事。
孟子言性,用端字用才字,具见萌芽可能之意;据荀子的界说讲……所谓端,当然也不能说是伪,但决不在性中。”[②]张岱年先生认为,孟荀虽一主性善,一主性恶,其实并非完全相反,从究竟上说,两说虽有很大不同,但未始不可以相容。
李泽厚说:“荀与孔孟的共同点,其一脉相承处是更为基本和主要的。荀子可说上承孔孟,下接易庸,旁收诸子,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史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荀子实际都大体遵循了孔孟的路线……如果说,孟子对孔学的发扬主要在‘内圣’,那么荀子则主要在‘外王’(说‘主要’,是因为孟也有‘外王’的一面,而荀也有‘内圣’的一面)。
‘外王’比‘内圣’有更为充分的现实实践品格,也是更为基础的方面……在荀子所有的思想观念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便是上述这点:即追溯‘礼’的起源及其服务于人群秩序的需要,从而认为人必须努力学习,自觉地用社会的规范法度来约束和改造自己,利用和支配自然。”[③]
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说:“孟子和荀子在人性学说上的冲突导致他们对孔子的两个主要关切点‘礼’与‘仁’抱有不同的态度……孟子强调从人性的善自然流出的仁。而荀子则把礼看成在给混乱的人欲设置秩序方面系对刑罚的替代。”[④]
我比较同意以上诸先生的论断。但另一另面,蒙文通、牟宗三、韦政通先生的评论也不是绝对没有道理的。蒙文通说:“以‘性恶’论荀卿之学,则不足以尽荀卿。卿学之所由立,在《解蔽篇》之言‘心’……卿所言之‘心’非‘本心’,而实并‘放心’言之。
则其所谓‘心’,惟觉知之明,无德性之实……孟子之学有本,而荀氏之学为无本也。荀氏所谓之‘心’,与孟子所谓之‘心’,名则同而事则异,惟其不知‘性’之本善,‘知’之本良。所由孟子养心,主于勿害其‘直’;荀氏养心,主于勿蔽其‘明’,然后足以‘化性’而‘起伪’ ……盖明不足以知孔孟之微,而徬徨以乱采索之旨,激而攻难孟子之义,亦可悲也。”[⑤]
牟宗三也认为荀子丢掉了终极本源:“自孔孟言,礼义法度皆由天出,即皆自性分中出,而气质人欲非所谓天也。自荀子言,礼义法度皆由人为,返而治诸天,气质人欲皆天也。彼所见于天者唯是此,故礼义法度无安顿处,只好归之于人为,此其不见本源也。”[⑥]如此,价值世界的终极根据旁落了。
韦政通是反对持宋代理学家与现代新儒家的观念来评价荀子的,尽管如此,他也说荀子的系统让人有点“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的感觉,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新儒家相类似。“其言上不在天,是说他超越精神的缺失;其言下不在田,是说价值主体一面的黯淡。”[⑦]韦先生认为,荀子将“礼义之统”与“心的认知”相结合,在某种意义上遮蔽了道德主体,“隆礼义、知统类”成为纯粹外在性的行为。这就使其思想体系缺失了超越性的价值支点。
韩德民针对韦先生的上述论断说:“缺少超越性的价值支点,这确实是荀学潜含的重要缺陷。但换个角度,站在实践效应的立场上,也未尝不可以说,正是由于他这种立足点的虚悬状态,而导致了在秩序规范原则问题上的相对开放性。礼义的实质,既不是天道的下载,也不是心性的外显,它只是某种经验性的措施手段。正是出于对礼义性质的这种经验性理解,荀子超越了孟子的王道政治原则,而能够用更现实的眼光看待霸道。”[⑧]
以上所引各位学者的评论颇具启发意义。我们现在要问:荀子比他的前辈与同时代的思想家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呢?荀子超迈前人的学术贡献,我以为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天人关系的新见解。其实荀子也继承了以天为神的传统,如说“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把“天”、“帝”合称为“动如天帝”等。荀子也以“诚”说“天”:“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荀子•不苟》,以下引本书只注篇名。
)他的“君子与天地相参”等思想亦与《中庸》相通。荀子天论的创新发展在于阐发了“天”的自然义和规律义。他提出“天行有常”的命题,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天论》) 他又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也就是界定好天的职分和人的职分。他指出,加强农业,厉行节约,天就不会使人贫穷;给养充备,动作得时,天就不会使人困顿;遵循着“道”,不出偏差,天就不会使人受祸。
违背了自然规律(“道”),任意妄行,天就不会使人吉祥。人事处理不当,即使没有发生自然灾害,人民也要遭殃,因此不可以埋怨上天。他说,天和人各有不同的职能:“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论》);“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礼论》)。
人类的命运在上天,国家的命运在礼制。产生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是自然之天,而治理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则是有为的人。
荀子主张不要迷信天,但要尊重天道,在尊重的前提下,人是有所作为的。荀子进而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总之,他的“天”更多的是自然之天,他认为天人各有不同的职份,有分而后合的思想,人在最高境界上可以与天、地鼎足而三,但天、地、人各有其领域、职责与功能。
荀子冲破了在人与自然之天的关系上的重重迷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弘扬了人的主体性,这是他此前的儒学和诸家所没有的思想。但他并未导致人对天地自然的破坏,如对于天地本源的尊重,关于山林泽梁的保护,与孟子和其他儒家无异。
第二、人性学说的新开拓。如前引张岱年先生等人的论述,荀子对“性”的定义及人性论思想确与孟子不同,但二者不是绝不相容的。他提出“性伪之分”、“化性起伪”的命题,指出:“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于性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
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 (《性恶》)导情、化性而起伪,改变人性,造就治世,是荀子的主要思路。荀子主张“性伪合而天下治”(《礼论》) ,通过后天的教育,或通过国家刑罚与社会规范的制约,使人以理性支配感性,维护社会道德秩序,达到天下出于治、合于善的目标。
“涂之人可以为禹。”(《性恶》)因此,凡人都要改变自己的性情,化性起伪,化恶为善,可以成为像禹那样的圣人。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在现实性上,并非人人都可以成君子、成圣人。因为人性随后天环境可以发生多重变化,人们“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注错习俗之所积耳。
”(《荣辱》)“注错习俗”是指行动和习惯的积累和人对客观生活环境的影响。荀子性恶论的主要意图是要改变人的恶性之质而迁于善。因为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结果。
他肯定人有智能,可以向善,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教化,成就自己。“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性恶》)这为现实人的道德修养提供了普遍性的道路。
第三、礼治秩序的新建构。我们似不能说荀子不知本。他有“礼有三本”之说:天地是生命的本元,先祖是族类的本元,君长是政治的本元。三者偏缺一种,就无从安定人民。所以,礼文,在上方事奉天,在下方事奉地,尊敬先祖,尊重君长。
三本,只是指人们生命、族类的本元与政治的主导。人们为什么要祭祀天地、先祖,尊重君师?人有根源感,人总是要眷怀、追思、甚至回归自己所以出生之处。祭祀天地、先祖,尊重君师的礼俗逐渐演变成礼治。
礼治是为了人心的安定,社会的秩序化。从社会与人的性情的角度,荀子认为,礼义起源于对人的自然本性、情欲情感的限制,起源于人们无限的欲求与社会有限的财富的矛盾。人们正当的物质欲求必须满足,但财富毕竟有限,因此只能按社会名分等级来确立消费的多寡,以解决需求和生活资料的矛盾。
荀子认为,人们的生存离不开社会,一个社会的组成及其秩序化,靠社会分工和等级名分制度加以确立。礼、义则是维系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纽带。他提出“明分使群”的社会起源说,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群”。
而人所以能群居,是能“分”。靠什么“分”?靠礼、义。荀子主张“以礼正国”。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富国》) 礼是差别性的社会秩序,又是德位禄用的相称:“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
”(《富国》)他强调隆礼义,是因为礼义法度属于后王现行的东西,比起先王的《诗》、《书》更为切近明确。君子可以制定法、执行法,小人则只可能践踏法,利用法生乱。
这里有三个层次的划分,光拘守法而不识其义是不够的,识其义能固其志以实践道而不能类通先王之典,也是不够的。荀子还是主张信用贤能,天下为公。荀子向秦昭王明确表示了实行王道政治的立场,肯定儒家的仁义爱民主张,并认为只有儒家之道才能统一中国。
礼是由仁义所生,礼治本质上也是仁政,由君子实行。礼义是社会认同的道义原则,统治者与庶民都必须遵守。在这些方面,荀子与讲法、术、势的法家有很大的区别。
荀子的礼论又是与乐论相结合的,礼乐不仅调节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儒家的治道,是一种教化形态,它也包含法治、刑政,但主要是通过礼乐教化提升每一个人的人格。以礼节民,以乐和民。礼乐刑政,相辅相成。荀子把儒家的礼乐相辅相成之道发挥到极致,主张“美善相乐”,指出通过礼乐教化可以提高百姓的文化素养,纯洁人心,成就每一个和乐庄敬的生命,达到理想的胜境。
第四、认识论上的新创造。他肯定人有认识能力,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他肯定“缘天官(即感官)”、“天官簿类”、“心有征知”的路子,以“天君”即“心”为神明之主。“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
”(《天论》)他又提出了“解蔽”的方法论,肯定理性思维,肯定克服片面性与把握认识规律。但他的认识论与西方知识论仍不一样,他吸收道家思想,主张“虚壹而静”:“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
”(《解蔽》)这里强调了“心”的空灵、专一、宁静,企望达到“大清明”的境界。《解蔽》用明镜与止水之喻,又讲圣人知心术之患,用“衡”之喻:“兼陈万物而中悬衡”,并以“道”为衡准。荀子的知,由“知”上升到“智”(“知有所合谓之智”),他虽然肯定了感性与理性认识,最终还是超越了感性与理性,由体验之知上达通透而无所偏蔽的“大清明”之境。
在知行关系上,他更重体验道之后的行为:“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解蔽》)另一方面,又开启了“符验”说的闸门:“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性恶》)检验之后,仍要落实到施行。
第五、逻辑学上的新发明。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正名思想,主张“制名以指实”,指出语言的正确使用,是实现良好秩序与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他的正名学说中有一套名、辞、辩、说的逻辑系统。他提出“制名之枢要”,即制名的几条原则。
第一,“约定俗成”。 这就是重视“名”的社会性,即同一社会中的人,大家都认同并遵守。第二,“同则同之,异则异之。” (《正名》)名必须依据于实。物同则名同,物异则名异;异实则异名,同实则同名。
第三,“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 (《正名》)能用一个字的就用单名(如马、牛),不能用一个字的就用兼名,即词组(如白马、骊牛)。
如果单名、兼名所表达的事物属同一类,就可以用共名(如黄牛、黑牛,以“牛”为共名)。第四,对名相作出分类。提出了“大共名”、“大别名”的概念。前者为遍举,是从逻辑综合的角度言;后者为偏举,是从逻辑分析的角度言。
所谓“大”,并非最大或最终之共名与别名,因为它们都可以“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也就是说,它们可以继续综合和继续分析,不是最大的共名,也不是最小的别名。
第五,“稽实定数”。此外,荀子还提出了辩论的逻辑原则,如“正其名”、“当其辞”、“辩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辩则尽故”等(《正名》) 。他不仅提出逻辑推理的规则,而且提出了论辩的道德原则:“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正名》)他认为,论辩中一定要符合仁德礼义,要公正,虚心听取对方的论说,不畏权势,不为传言所左右。
荀子所处的时代与孔、孟不同,面对战国末期新的时代问题,他发展了儒学与中国哲学。我们认为,荀子可以这样予以定位:
第一、他是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集大成者,对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作了系统总结与评析,博采众长,又富有批评与论辩精神。
第二、他是经学大师与传经之儒的代表,特别是对礼乐文化与学说有大的发明,是承前启后者,在社会治理上融摄法、刑,在历史观上以王道统摄霸道,在统一中国及其制度文明的理论设计方面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
第三、荀子在社会学、政治学与政治哲学、人性论、道德哲学、修养论、教育学、知识论、逻辑学、生态环境伦理上都有全面的建树,极大丰富了儒学与中国哲学。他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第四、他是儒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开拓者,尤其是现实主义的儒家的典范。在孔子之后,孟子与荀子均继承了儒家的主要的思想内涵,孟荀之间同大于异,他们各自有所偏重,有创建。荀子也有理想,但未导向理想主义。他的现实主义是对孟子理想主义的重要补充,对儒家外王学的拓展意义极大。
第五、我们不仅有“天人合一”的传统,也有“天人相分”的传统。从元方法论上来说,中国哲学主要的思维方式是合一,是和合性,是圆融一体,然而荀子却提供、开启了另一思想传统,即分疏与析别的方式。善于分疏也是儒家的传统,我们“宜对以荀子为代表的另一种注重分解、彼此独立的倾向予以应有的关注,也应该重视并充分认识到这一思想资源的重要意义,如此才能对儒家文化及其内在精神和发展趋向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才能避免在面对现代性的挑战时自陷困境。
”[⑨]
第六、正因为荀子思想的内在张力很大,故在思想史上的各方面影响尤大。荀子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几个思想流派,包括后期法家,但他与商韩之法有本质的区别。我们不能因为学生的问题而罪及老师,何况法家作为思想流派也有合理性。从汉代到现今,对荀子的批评史也成为荀学思想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很多问题是儒学内部的问题与分歧,由此也可知儒学的多元多样。
原载《河北学刊》2012年第5期。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上册,第349—350页。
[②]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87—189页。
[③]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6、115---116页。
[④] [英]葛瑞汉著、张海晏译:《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⑤] 蒙文通:《儒学五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10页、12页。
[⑥] 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94年,第214页。
[⑦] 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19页。
[⑧] 韩德民:《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539页。
[⑨] 储昭华:《明分之道----从荀子看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