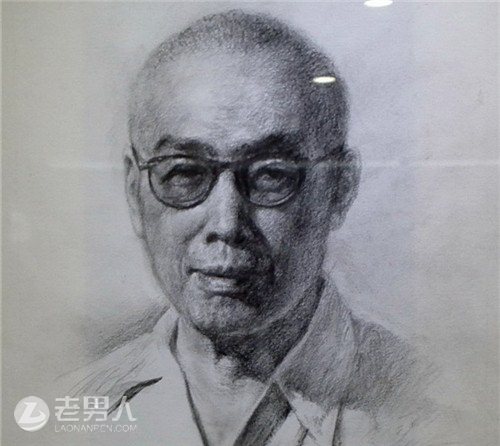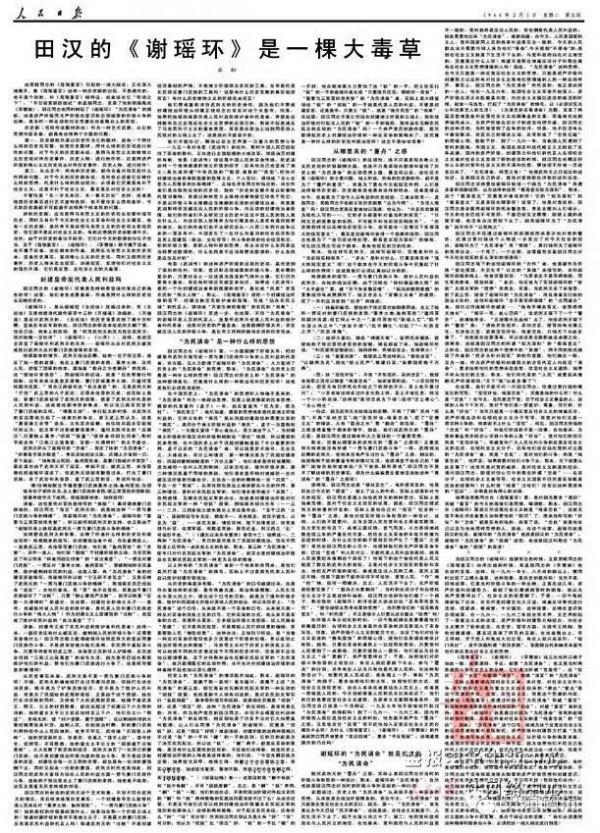田汉女儿 田汉儿子田大畏回忆:父母一生爱得艰难
“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1934年,电影《渔光曲》在上海公映,创下了连映84天的纪录。影片中由任光谱曲、安娥作词的同名电影主题曲也随之传唱全国。
几个月后,一名与安娥有过感情纠葛的男子,无意间听到了这首歌,优美的旋律令他顿时思绪万千。他随即用短短28个字,表达了自己对安娥的复杂情感:“君应爱极翻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这名男子,就是后来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著名剧作家田汉。
然而,田汉与安娥之间的爱情故事,不是这短短二十几个字能够说清楚的,就连他们的儿子田大畏也说:“对于父母的经历,我也是后来才了解,他们几乎不和我谈过去。”
2010年10月13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东直门附近田大畏的家。田老已年近八旬,是我国著名的俄文翻译家、国家图书馆原副馆长。他的书桌上堆满了俄文书稿,厚厚的俄文大辞典已经翻得泛了黄。老人很豁达,对于过往直言不讳。“我们家里,爸爸、妈妈和我,是3个独立的生活轨迹,直到晚年才有些许重叠。”
一生最爱三个人
田汉原名寿昌,189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小山村。他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易克勤带着3个孩子艰难生活。田汉曾在《三叶集》中提到,自己最爱的人有3位:一位是母亲,一位是他的舅父兼岳父易象,另一位就是自己的妻子易漱瑜。田汉的母亲是一位坚强倔强的女性,遇到困难从不低头。看到田汉从小聪慧好学,为了供他读书,母亲把家里唯一的被单也当掉了,长期盖着破棉絮过冬。
田汉的舅父易象是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对田汉的才华非常赏识,把他当儿子一样对待,并想把唯一的女儿易漱渝许配给他,亲上加亲。1916年,易象出资送刚 从长沙师范毕业的田汉和自己的女儿去日本留学。田汉和易漱渝可以说青梅竹马,又都喜欢诗文,情投意合。
1920年底,他们在日本结婚。这一时期田汉的话剧 创作也进入了丰收期,如《乡愁》、《咖啡店之一夜》等。应该说,与易漱瑜的爱情,是田汉一生中感到最幸福、最满意的。
1922年,夫妻二人回到国内,联合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刊物的名字取自王维名诗《相思》中的“红豆生南国”,这也是田汉发表自己戏剧作品的园地。然而,不幸的是,易漱瑜1925年病逝。临终前,易漱瑜将自己的同窗好友黄大琳介绍给田汉,希望他们能结婚。
在田汉的恋情中,黄大琳不过是一个过渡人物。田汉在给日本友人、著名作家村松梢风的信中说:“妻子去世后又有了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不过,1927年,田汉还是与黄大琳结了婚。但与此同时,他开始和一位远在新加坡的女教师林维中有了联系,彼此通信3年。
林维中因逃婚而出走南洋,1925年,她偶然在刊物上读到了田汉在丧妻悲痛中写的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被深深打动了。林维中风姿绰约,一直想找一位有 文化的丈夫。她大胆地给田汉写了一封信,坦承自己的爱慕之情。
就这样,刚再婚一年的田汉与林维中凭着传递信件和照片,感情一发不可收拾。田汉天性浪漫,他 在给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信中写道:“怀念着旧的,又憧憬着新的,捉牢这一个,又舍不得丢那一个。于是,我成了暴风雨中的小舟似的,只好让它漂流,让它颠 簸,毫不能勇猛地向着某一个目标疾驶迈进了。”
1927年秋,田汉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并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颇具影响力。1928年夏天,林维中利用暑 假回上海与田汉见面,当她听说田汉办学没钱,立即把自己积攒下的500元钱交给了他。当时,500元可是一笔不菲的资财,上海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不过几十 元钱。
1929年新年刚过,田汉率领南国社去广州公演。虽然异常繁忙,但他一个月之内还是给林维中写了7封信,热恋之情可见一斑。这时,他已决定与黄大琳分手, 娶林维中为妻。不久,田汉和黄大琳的婚姻宣告结束,他们不但友好分手,还专门去照了一张离婚合影。田汉在合影下写道:“为着我们精神的自由,为着我们不渝 的友谊,我决然与你小别了,亲爱的大琳!”
和莫斯科“红色女郎”相识
1929年,对田汉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形势,使他决定“转换一个新的方向”,即从思想上、政治上、文艺作风上转向“左翼”文艺战 线。因为田汉在上海的影响力,他成了各方势力争取的对象。恰在此时,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红色女郎”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她就是安娥。当年,安娥只有24 岁,身份是上海中共特科成员。在田汉看来,安娥不单具有政治魅力,还有诗人的才情,浪漫、热烈且具叛逆精神。
安娥1905年出生在现石家庄市长安区一个书香之家,原名张式沅。父亲是清末民初教育家。田大畏告诉记者,“母亲在少女时代,就表现出追求自由、独立的个 性。她15岁上初中就‘不安分’,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安娥因学监压迫学生,就带领全班同学罢课,住在旅馆不回学校,迫使学监辞了职。事后,安娥离开 学校,被父亲带到北京读书。1923年,安娥进入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田大畏说:“我的外祖母性格很刚强,这一点母亲和她很像。听说母亲加入地下党,她直接来到北京,硬是从学校里把母亲抓回家。”当时正值1926年“三一 八”惨案发生,安娥在报纸上看到25名学生被杀,再也按捺不住,索性逃走。“母亲的这一选择,让外祖父直到去世都不认这个女儿。外祖父不赞成母亲走上共产 革命道路,他发表声明‘从此不再有这个女儿’。”
同年,安娥受李大钊派遣,到大连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又被周恩来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她第一次接触到了情报工作,也由此开始了特工生涯。她做特工时有许多化名,“安娥”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成了她的正式名字。
田大畏说,“在中山大学时,母亲因为历史比较简单,俄文也不错,被选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来叫克格勃,当时叫格别乌,做东方部主任的助手,帮助他们办案。”
1929年,学成归国的安娥被安插在国民党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身边担任秘书。她负责将收集来的信息,及时抄送给陈赓,再由陈赓报周恩来。这些重要的情报使许多地下党员化险为夷。安娥参与营救的就有任弼时、关向应等人。这位从莫斯科回来的“红色女郎”,一天可以变换好几个身份,一会儿是衣着华贵的秘书小姐,一会儿是女工,一会儿又成了大学校园里的意气学生。
田大畏说:“当时父亲已经是一位左翼作家,各方面来往的人很多。母亲懂文艺,自己也会写东西,组织就派她去接近田汉。”那时,田汉已成立南国社。他本以为所见的是一位积极要求入社的女学生,却见安娥眉清目秀,不卑不亢,举止大方,颇有几分英豪气,很是欢喜。
这以后,安娥便经常带着她写的一些作品来找田汉。当她将小说《莫斯科》交给田汉时,这位“靠思想飞翔的艺术家”震惊了,作品反映出的丰富阅历以及不俗才情让田汉兴奋和感动。
在安娥的影响下,田汉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加入了“左联”,并申请入党。正是这一思想的转变,使田汉成为“时代之子”,并创作出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频繁的接触与交流,急剧增进了两人的感情。1930年秋,在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隐居的情况下,安娥选择了与田汉同居。
争爱情不争躯壳
然而,甜蜜的爱情并没有维持多久。与田汉保持了5年通信恋爱关系的林维中,不久从南洋归国,她曾资助过田汉的事业,且早已被田母默认为儿媳。林维中知道安娥与田汉的关系后,当面去质问她。而田汉,既不愿伤害这个,也不愿伤害那个,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是安娥帮他下了决心。她告诉林维中:“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与他结婚吧。”最终,田汉决定遵守诺言,与林维中完婚。
谈起此事,田大畏说:“母亲是地下党员,从事秘密工作,是个四海为家的革命者,当时并不能结婚。不仅如此,她听说父亲结婚没有房子,甚至还张罗着给他们找婚房,这是父亲后来在回忆录中写的。”而田汉并不知道,这时的安娥正怀着自己的骨肉。
1931年8月,田大畏出生了。可是,革命工作不容安娥过多沉迷于儿女私情,出于经济和安全等考虑,她不得不把儿子送走。“在最难的时候,母亲唯一想到能依靠的,只有姥姥。她踏上了6年未回的家乡。母亲再次出现,还带着私生子,当时的场面可以想象。据说,她是跪着求姥姥,请她照看我的,姥姥搂着母亲失声痛哭。”之后,安娥果断地回到了上海,来到田汉面前,亲口告诉他:“孩子已死,勿需挂念。”
1933年,由于叛徒的破坏,安娥的直接领导姚篷子被捕叛变,作为姚的下线,安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经作曲家任光介绍,她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脍炙人口的《渔光曲》、《卖报歌》等,都写于这一时期。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安娥撤离上海,在由上海辗转武汉的路上,她竟然又与田汉相遇了。民族存亡战线上的再相聚,决定了他们的爱情命运。“母亲告诉父亲,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父亲听后很激动。”当时,田汉的妻子林维中住在重庆,而他和安娥住在武汉,两人密切配合,一起出席各种活动,爱情又明朗化了。
在田大畏看来,父亲当时根本不可能选择离婚,“他并不是很风流的人,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很犹豫,哪个也放不下,但那边有妻子有孩子,毕竟是一个家庭,我父亲在这个问题上很传统。”
诚如作家吴似鸿在《回忆田汉》一文中所言,田汉虽然兑现了跟林维中结婚的诺言,但无论是政治倾向、艺术观点和人生态度,他都跟安娥更加契合。经历诸多感情波澜,田汉“被爱的伤痕留遍”,甚至曾说:“婚姻是一条绳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结婚,用情人制。”
1948年2月,安娥接受上海《新民报》专访,开诚布公地表明了自己的爱情观。她说:“争,或许可以得到一个人的躯壳,但却不一定能得到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爱情。”当记者问她,面对如今的局面如何应付?安娥笑言,“无所谓应付”,“一切应该随田先生”,“是他自己因善良而产生出来的痛苦,也正因为他这一份善良,在日常生活里,时常使我感动”。
抗日战争期间,安娥曾任战地记者,1938年后辗转武汉、重庆、桂林、昆明等地,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这时,田汉已经与林维中离异。1948年,安娥和田汉同赴解放区,安娥次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相濡以沫度晚年
战乱、纷争、婚变,安娥与田汉在历经20年风风雨雨后,1948年前后终于厮守在一起。他们在创作上的相互帮助,成就了中国现当代文坛的一段佳话。新中国成立后,安娥将田汉创作的16场京剧剧本《白蛇传》改编为11场地方剧本;将田汉17场京剧剧本《情探》改写为9场越剧剧本;还将田汉整理加工的湘剧高腔剧本《追鱼》改写成越剧。
田汉对安娥的帮助则更多。他为安娥的诗剧《高粱红了》作序,为安娥的报告文学《五月榴花照眼明》润饰文字,修改安娥的戏曲剧本《新纺棉花》。
安娥把田汉的湘剧高腔剧本《追鱼》改编成越剧之后,田汉又在此基础上把《追鱼》改成了《金鳞记》,使这个剧本渗透了夫妻二人的感情和智慧,真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田大畏说,他的父母亲从1949年至1954年依旧过着独立的“宿舍生活”,没有称为“家”的住所,各忙各的。1954年,虽然有了共同的宿舍,但他们仍是聚少离多。“我感觉父亲是为了戏剧来到这个世界的,而母亲是为了革命和理想。他们无论环境怎么恶劣,怎么困难,只要跟这些事有关,都不知疲倦,把物质和权势完全抛之脑后。”
田大畏说,他曾因对父亲不够理解、不够体谅,而和父亲有过争执,但当他看到父母晚年相濡以沫的情景,也不禁想落泪。“我9岁才被母亲接到重庆,见了父亲一面,之后几乎联系很少,多半都是自己住校。但当我翻阅父亲晚年写给母亲的信时,才了解他原来对家人有那么细腻的情感。”
1954年,田汉率中国京剧团赴云南慰问解放军,他给北京的安娥写信说:“你已回京否?为什么不见只字来?应该知道我是如此念你。母亲处也请你去看看,听说她老人家又有小病,已好些吗?”之后,田汉又在浙江写信:“亲爱的沅:到这里住了三天,完成了《白蛇》初稿……我们住在一百号,下次一定同你来,也住一百号。”
1956年,安娥在郑州观摩豫剧演出时突然病倒,中风不语,半身瘫痪。田大畏说:“父亲始终鼓励母亲别泄气,同病魔作斗争。他给母亲找最好的医生,给母亲读报、读文件、讲国际形势。为使母亲不完全脱离文艺界,父亲无论到外地参观游览还是观摩演出,都尽可能带着母亲。
”其实,当时田汉的处境也不好,很压抑,即便如此,他还坚持多年如一日,找来小故事和笑话,耐心地讲给安娥听。在田汉同常香玉等艺术家的合影中,总能看到安娥灿烂的笑容。
1956年,田汉在颐和园创作,听说安娥突然生气了,非常不安地写信给她:“……你昨天回去生了气,不吃饭,生了谁的气呢?应该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乐观,这样对于病才有好处……两三天后再回来开会。同你到万寿山玩玩吧。
”安娥中风后失去了写作能力,1961年,她在广东养病时,勉强用左手给田汉写了一封信。田汉收到信后无比高兴,立刻回信说:“……信皮上写得花花搭搭地像一幅画,但绿衣使者给正确地投到了。知道你又顽强地在练习用左手写字,我多么高兴……汉”。
安娥在上海养病时,田汉不时写信叮嘱:“……棉衣找给你,不知对不对”,“四川带去的药,一定要做成药丸,按时吃一年再说,不要忘记。北京的人都好,不要挂念。汉”1963年,田汉因病在北京住院,他在病床上仍关心着在昆明疗养的安娥:“亲爱的沅:我的病好转,勿虑。听说你安心静养,我放心。”
“文革”期间,田汉被分配到顺义牛栏山参加“四清”。行动不便的安娥总要陪田汉到车站,目送他离去,有时甚至拖着病残的身子,到市郊看望丈夫。1968年12月10日,田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安娥也被疑为“王明苏修特务”,受到迫害。1976年8月18日,安娥谢世于北京隆福医院。
这对20世纪革命情侣的执著与热诚,今天的人可能难以理解;但他们在那个热血年代的革命情怀,却让人难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