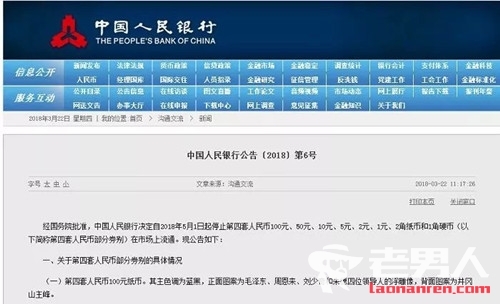为什么说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开创者?
摘要:笛卡尔哲学是现象学的真正发源地,同时又与维特根斯坦核心思想紧密相联。他的正在性思想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我思故我在”、理性主义、“二元论”等思想,致使“剪不断,理还乱”。他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主要话题,也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我思故我在”;正在性思想;反思;“笛卡尔的循环”
笛卡尔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他从根本上对人类知识体系的怀疑与重建,他的关于“我思故我在”的著名推论(关于“推论”是有争议的;下面将有讨论),他的理论中所深刻蕴含的理性主义和二元论思想等,都与后世哲学各主要流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上所述,论说极多,几为共识。但正如黑格尔所言:“这个人对他的时代以及对近代的影响,我们决不能以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这句话很有道理。第一,我们都知道,说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的始祖”、“真正的创始人”,主要之点就在于他不再把外部存在,而是把“思维”作为“绝对的开端”,
这很重要,为什么?笛卡尔的“思”或“我思”的具体情形如何,以至于能作为“绝对的开端”?第二,他的理性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对整个笛卡尔哲学有着怎样的价值,存在哪些问题等,从这里开始,我们就有些语焉不详了,缺乏深入而又融贯的理解。
另外,对笛卡尔的“二元论”,我们更多谈论的是“身-心”二元,进一步的探讨将表明,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三,也是最重要之点,正如整个近代哲学所表明的那样,笛卡尔并没有简单地指引近代哲学走上一条光明大道,进一步的讨论将表明,如果说笛卡尔哲学是近代哲学的始源处,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他的哲学也是近代哲学几乎所有主要问题乃至核心问题的发轫处;这一点在笛卡尔哲学中有着怎样的情形?当然还有一些问题,都有待我们潜心探索。
这是一个在哲学史上非常著名的命题,也是笛卡尔哲学的所谓“第一原理”。首先,笛卡尔是怎样得到这个命题的呢?大家都知道,他是通过所谓“普遍怀疑”的方法而得到的。他写道:“很多年前,我就被一大堆我自幼以来就当作真实的来接受的错误观念所震动,并且也被我后来建立在这些观念上的整个知识体系的高度可怀疑性所震动”。
怎么回事?仔细分析之后发现,原来感官在欺骗我们。比如塔,远看是圆形,近看却是方形;其实二者都是可疑的。
不过,比如“现在我醒着,正在看文章”;“我有身体”,“这是一只手,这是另一只手”,这应该是不可怀疑的吧,笛卡尔指出,这些情形统统有可能在比如一个被截肢的人的梦中出现,并且我们却信以为真。
笛卡尔逐次指出,上述复合的东西是可怀疑的,简单和普遍的东西也是可怀疑的,其中包括算术、几何学和其他这类学科。
笛卡尔认为,我们甚至可以同意无神论者的说法:“关于上帝所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最后得出结论:“我以前的信念没有一个是不能被恰当地加以怀疑的”。
黑格尔认为,“怀疑一切”“是笛卡尔的第一个命题”。
大家知道,笛卡尔怀疑一切,但却不能列入怀疑主义,就是因为笛卡尔怀疑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怀疑,或为怀疑而怀疑,他的目的是通过普遍怀疑,最终寻找到不可怀疑的确定的东西,一个他所要寻找的阿基米德点。
这种东西还真被笛卡尔找到了。具体过程是这样的:通过彻底怀疑,笛卡尔写道:“我已经使自己相信在这个世界中绝对不存在什么东西”。
然而在作出彻底清除的同时,笛卡尔发现一个问题:我们能否在清除的同时连这个清除也清除掉呢?即同时认为“我已经使自己相信在这个世界中绝对不存在什么东西”,因而引号里的话也不存在呢?不能,因为这是明显的自相矛盾。
不难理解,如果“我思”即引号里的话可以自我清除,那么我在思即意味着我不在思或我思不存在。结论是:什么都可以怀疑而否定其存在,但我在怀疑或这个“我思”本身的存在却是不可怀疑的。在任何情况下,即使这时“有一个拥有最大能力和诡计的欺骗者”“正在欺骗我”,情况也是如此。
关于这一点,笛卡尔曾有过这样非常形象的表述。比如面对眼前这块蜂蜡,“有可能我所看见的并不是真实的蜡;也有可能是我连看东西的眼睛都没有。可是,当我看见或者当我认为我看见(在这里我没有区别它们)的时候,这个在思维着的我倒什么都不是,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了”。
笛卡尔就此认为,“这个在想这件事的‘我’必然应当是某种东西,并且发觉到‘我思想,所以我存在’这条真理是这样确切,这样可靠,连怀疑派的任何一种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于是我就立刻断定,我可以毫无疑虑地接受这条真理,把它当作我所研求的哲学的第一原理”。
对于“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后世哲学家有非常多的解读,但遗憾的是,其中有一个最为重要的思想,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阐发。因为,就“我思故我在”言,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样一点,即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我思”,或正在的“我思”。
通过上述可见一斑。实际上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在解读这一思想时频繁地使用“正在”一词。那么什么是正在的“我思”?就是当下的、本真态的“我思”,或者说是“我思”本身。
笔者将其表述为正在性思想。比如当我们正在想“塔是圆的吗?”之时,正在进行的“塔是圆的吗?”本身才是笛卡尔所说的“我思”;对此,现象学有非常丰富的表述。就笛卡尔来说,为什么一切都可以怀疑,唯独“我思故我在”不可怀疑呢?根本原因就在于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是正在的“我思”。
不难理解,当“我思”正在进行时,“我思”作为一个思维实体(“我”或“心灵”;因为,“在严格意义上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心灵”。
),怎么能说它不存在呢?在笛卡尔看来,正在的“我不存在”这一否定本身,同时也就是对“我”存在的明确肯定。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思维实体”并非仅指思维作为实体本身,因为,“由于我们不能直接认识实体本身,所以我们习惯把不同行为的主体称作实体”。
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所谓“思维实体”、“心灵实体”、“我”,都是指正在进行的“我思”。
高秉江先生指出,笛卡尔“从来没有在自明给予的意识之外去谈论实体”。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说笛卡尔的“我思”是正在的“我思”,笛卡尔本人是如何表述的?应该说笛卡尔关于“我思”应该是正在的“我思”的表述,一方面核心内容应该说是明确的,不过在方式上也是很丰富、多样的。重点可参看“第二沉思”;类似表述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可以怀疑一切,但“心灵注意到,在进行怀疑时,心灵本身是不可能不存在的”。
这里所说的“在进行怀疑时”,实质上指的就是比如正在的“我有身体吗?”这样的怀疑本身。刚才讲过,正是因为这样的“我思”,所以才必然地导出“我在”。“自然的光明向我揭示出来的任何东西—-例如从我正在怀疑这个事实推出我存在,等等---是一点都不能被怀疑的”。
“过去这几天我在询问世界上是否有什么东西存在,并且认识到仅仅从我提出这个问题事实,就能很明显地推出我是存在的”。
上述都可以看作是关于“我思”正在性的阐述。针对有人认为“我思故我在”的大前提是“谁思谁就在”,笛卡尔指出,“我思故我在”并不是“把一般性的命题当作前提”它“是从特殊概念开始的”。
所谓“特殊概念”在这里实际上讲的就是正在的“我思”。
在笛卡尔看来,“我思”是正在的“我思”,所以“我思故我在”不可怀疑;如果“我思”不是正在的“我思”,“我思故我在”就能被怀疑吗?是的。因为,如果“我思”仅仅是一个通常被反思的、简单的对象,“我思”就要面临“我走”的问题,就无法不可怀疑地推得“我在”。
因为,针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有人就提出,何必“我思故我在”,比如“我走故我在”不也一样吗?笛卡尔指出,作为简单对象的“我走”是可怀疑的,比如在梦里(我在走而我并没有走);而一旦把“我走”看作一个“我思”(我正在思想“我走”),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2]101-102、[3]63
这里的问题是这个“我思”讲的一定得是正在的“我思“,不能是单纯的被反思的作为简单对象的“我思”。具体地讲,如果“我思”是过去的、曾经的“我思”,因而存在一个简单对象,那么关于这一点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记错?(因为有可能“记忆在向我说谎,并且记忆所告诉我的事情中没有一件曾经发生过”。
)比如经常会有:“我说过那句话(思)吗?”这样,作为简单对象的“我思”,其存在也是可怀疑的。
所以说,笛卡尔的“我思”一定不能是被简单反思的“我思”。在笛卡尔看来,只有正在的或必须正在的“我思”,才不可怀疑,才可以作为“绝对的开端”。
这里我们可以提到被广泛注意到的圣奥斯汀的“我错故我在”论题。
“我思故我在”与“我错故我在”这两个命题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我思”依据的是正在性,只是因为正在性,笛卡尔才认为“我思故我在”是直接自明的。而后者依据的则是逻辑推理,在笛卡尔看来,这就不能说是直接自明的。前者是一个革命性的哲学结论,后者仅仅是一个逻辑结论,缺乏对“我错”的正在性的把握。
关于“我思”,罗素曾认为,“这里‘我’字其实于理不通,他该把原始前提叙述成‘思维是有的’这个形式才对。‘我’字在语法上虽然便当,但它表述的不是已知事项”。
对罗素这一见解笔者不能完全同意。因为,就笛卡尔哲学而言,这个“我”字特别重要,它表现了“思”的当下性特征,承载着他对哲学的开创性贡献。为了帮助理解,这里我们很有必要讲一下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中对“唯我论”的阐释。维特根斯坦就认为:“唯我论的命意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它不可说,而是显示出来。世界是我的世界,这一点就显示在语言(惟一能为我所理解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
5.62大家都知道,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所说的“我”,不是某一个“我”,而是形而上学的主体。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第一,“语言-世界”仅仅是“我”或“唯我”的“语言-世界”,用笛卡尔的话说,其它都是可被怀疑的;在《哲学研究》一书中,维特根斯坦将其表述为“第一人称现在时直陈式”,
这作为正在的“语言-世界”的一种表述,尽管比较笨拙,但却非常形象。第二,就这个世界而言,尽管“我”不可说,但可以通过这个正在的世界而显示出来。为什么不可说?原因就在于这时“语言-世界”是正在的,关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有非常丰富的论述,这里不再多说。
“我”在这时尽管不可说,但却可以通过正在的“语言-世界”而得到“显示”。什么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显示”?简单地讲,就是既不能说正在的“语言-世界”中有“我”,也不能说没有“我”,用笔者的话讲就是无所谓。
这样,就维特根斯坦和笛卡尔而言,去掉“我”而仅仅“语言-世界”或“思”(作为“原始前提”),是一个不能容忍的误解。我们有理由认为,就这一点而言,维特根斯坦的“我”与笛卡尔的“我”在学理上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罗素的认为完全错了吗?也不是,原因就在于他正确地抓住了笛卡尔的“我思”的第二个意思。“我思”的第二个意思,正如罗素所言,表现为一个“已知事项”,通俗地讲就是一个被通常反思的“我思”。作为一个简单对象,不用细说,“我”字在这里确实于理有碍。
因为,这时我已经在反思,无论如何,把一个被反思的对象称作“我思”总有些不妥。但实际情况是,“我思”不同时作为一个反思的对象又不行,因为,“我思”如果仅仅作为当下的“我思”,正如刚才所指出的,就无法说是否“我在”,一切进一步的推论,知识体系的重建都将无从谈起。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有人甚至认为“我首先是他”。
可以说这也是很多人不顾笛卡尔的反对,一再地把“我思故我在”看作一个推论的原因所在。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我思”可以是正在的“我思”,也可以是被反思的“我思”,问题仅仅在于,正在的“我思”与被反思的“我思”要不要区分,能否不加区分,关于这一点,笛卡尔有非常明确的意见。
他在阐释“我在”时曾有这样的说法:关于眼前的这块“蜡”,“有可能我所看见的并不是真实的蜡,也有可能我连看东西的眼睛都没有,可是当我看见或者当我认为我看见(在这里我没有区别它们)的时候,这个在思维着的我倒什么都不是,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了”。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知道当下的“思”(“当我看见”)与被反思的“思”(“当我认为我看见”)有区别,但他没有加以区别。“在这里我没有区别它们”,在其它地方,他更加明确地认为,这是可以不加区别的。
在答复“反思活动”有无必要时他说:“我们意识到某些东西的第一层思想,和我们意识到我们意识到某些东西的第二层意识,并没有什么不同,这第二层意识和我们意识到我们意识到我们意识到某些东西的第三层意识也同样没有什么不同”。
这就已经讲的很清楚了。这样,由于可以不加区分,当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不是一个通常推论而是一个直接自明的结论时,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2]102、103[5]53
当“思”时与当“思”被反思时可以不加区分,这个问题与整个笛卡尔哲学有着怎样的关系,在笛卡尔哲学中有着怎样的情形、效用、结果?这是本文要搞清的核心问题。
从这里开始,笛卡尔与维特根斯坦的区别开始显现出来。上面已经讲过,维特根斯坦认为,当“语言-世界”正在时,“我”不是没有,但也不是有,而是不可说的,或“显示”着的。而笛卡尔则认为,当“思”正在时,“我在”是蕴含在“思”之中的,所以正在的“思”也就是“我思”。
读者可以关注一下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显示”与笛卡尔所说的“蕴含”的相似之处。然而,从这里开始,二人便各奔东西了。维特根斯坦认为可“显示”者不可说,而笛卡尔则认为,“我在”蕴含于“我思”,
这种蕴含是直接自明的,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进一步讲,正在的“我思”与作为反思结果的“我在”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或者说是“等同关系”;
这样,“我思故我在”实际上被认为是一个自谓(或自述、自指)句。这一点在后世哲学中特别是在现象学研究中,一再地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特别注意到,当时就已经有人给胡塞尔指出过“自我观察”的困难,但遗憾的是,现在我们只能说他当时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首先,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作为一种方法的理性演绎法;其次,笛卡尔意义上的“理性”(“自然的光明”),并不同于现在通常所说的相对于“感性”的“理性”。笛卡尔所说的“理性”,更确切地讲,应该是一种恒真性。
它对知识作为理性认识主要有两方面的要求,首先是知识或“思”的正在性要求,也就是说,凡真的,首先必须是正在的,或者说是“明白的”;单纯作为简单对象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必然为真。其次是不可怀疑的或者说“清晰的”要求。
笛卡尔在《哲学原理》一书中曾这样表述这两点:“我们所依靠的知识不仅要明白,而且要清晰。所谓明白的对象,就是明显地呈现于能注意它的那个心灵的对象,就如一些对象如果呈现于观察它们的那个眼睛前面,以充分的力量来刺激它,而且眼睛也处于观察它们的适当位置,那么我们可以说自己是明白地看到了那些对象。
至于所谓清晰的对象,则是界限分明与其他一切对象厘然各别,而其中只包括明白内容的一个对象”。
我们逐次来说明。笛卡尔在这里所说的“明白的”显然就是“正在的”意思。关于“正在”,通过本文第一节的讨论,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初步说明。问题是应该怎样理解“正在”与“真”的必然联系呢?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对现代语言哲学中“真之去引号”理论的简要分析,有更为深入的把握。
所谓“真之去引号”理论,说起来非常简单,它认为,所谓“真”,就是去掉引号之后的语句本身(目前仅指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暂不讨论),比如“雪是白的”是真的,其意思就是并且仅仅是:雪是白的。这一理论的现代起源,可以追溯到塔尔斯基的所谓T等式
明确持有这种看法的还有蒯因等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语句本身”是什么意思?所谓“语句本身”,实际上就是正在进行的语句,比如正在的“雪是白的”,(本文仍然要对去掉引号后的语句加上引号,但这不是引号的通常使用,而是引号的一种特殊使用,或唯一论使用。
仅仅表明它是当下的正在的“雪是白的”罢了。详见《根源》。)而正在的“雪是白的”,当然并且必然是在肯定地认为“雪是白的”。而肯定性的“雪是白的”的意思,真之去引号论者认为,就是“雪是白的”是真的的意思;二者是一回事。语句“雪是白的”当然还可以有其它形态的存在,笼统地讲就是作为通常被反思的对象的存在。相应地,维特根斯坦将二者区分为惊呼的与报告的两种形态,
比如张三问李四:“王五刚才说什么?”李四答:“雪是白的”。这实际上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报告性语句。作为惊呼的或正在的“雪是白的”,它的真理性是不言而喻的,是当然的,而作为通常反思对象的“雪是白的”,一旦无所谓正在性,也就无所谓真理性的了。
对于“真之去引号”理论,笔者是持保留意见的,这一点本文不便展开,但对其中包含的这样一层意思,却是完全赞成的,即语句的“真”与语句的正在性有必然联系。而就这一点而言,“去引号”理论与笛卡尔的真之理论,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指出:“至于观念,假定只考虑它们本身,……严格说来,它们不能是假的;因此不管我想象一只山羊或一个怪物,在我想象中前者和后者都是同样真实的”。
这里所说的“真实”是什么意思呢?这仅是一个当下性概念,显然不是下面将要谈到的反思性的“符合论”意义上的“真实”,而仅仅是“知识本身”的意思,即当“知识本身”正在如此时的意思。
按照去引号理论,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所有的语句,最起码是陈述句(大致相当于笛卡尔所说的“判断”。
)当其正在时,它们便都是真的。问题是这能不能也是笛卡尔的结论呢?不能。理由很简单,因为,就笛卡尔言,在限定的意义上,感性知觉也是“我思”,
并且当其正在时,如果我们不让它们涉及其他任何东西,则它们不能为假。
这样,如果正在的都是真的,并且任何知识都不可能缺乏正在性,这样,认识中的“怀疑”和“错误”等现象的存在就无法得到说明。所以说,在笛卡尔看来,正在性只是“我思”作为理性之思的条件之一,它单独不能构成理性之思。
也就是说,知识如果是真的,首先它必须是正在的,其次还得有一个条件,就是同时又必须是不可怀疑的。比如“我思故我在”,之所以是真理,如本文第一节所述,首先它必须是正在的“我思”,同时它又必须是不可怀疑的。什么是“不可怀疑”呢?有人将其表述为“不可纠正”,
这是有道理的。但再问一下,为什么“不可纠正”呢?笛卡尔指出,因为“纠正”会导致自相矛盾。就是说,凡对某类知识作出否定的判断就会导致自相矛盾,那么这类知识就是不可怀疑的。
比如“我思故我在”。对知识的这样两个方面的要求,构成了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核心内容。笛卡尔在《方法论》一书中将其称作“自明律”,即“明”和“晰”。
循此我们就可以对人类知识进行甄别,搞清哪些知识是真的,和在什么程度上是真的。哪些知识是错误的,最终使人类知识体系在理性的指引下重新建立起来。
哪些知识是明白、清晰的呢?与“我思故我在”相似的还有“算术和几何学中某些很简单、很直接的东西,比如三加二等于五,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就这些知识而言,是否仍然有被骗的可能呢?笛卡尔明确认为:“每当我转向我以为领会得十分清楚的事物本身时,我是如此地被这些东西说服,以致我不得不说:不管是谁,随他怎么骗吧,只要我想我是什么东西,他就决不能使我什么都不是;或者既然现在我存在是真实的,他就决不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使我没有存在过;他也决不能使三加二之和多于五或少于五,或者其它这类我看出明显是矛盾的事情”。
不过,为了使此类知识成为“可完全确信”的知识,笛卡尔认为,我们在此类知识上“受骗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在适当的时候,还是应该彻底予以澄清。问题具体表现为上帝是否存在,他会不会是个骗子。
最后是“上帝”观念(知识)。由于“上帝”观念的真实性(“明白”、“清晰”)、客观实在性,需要启用稍后的因果性证明,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文第三节讨论。笛卡尔认为,上述一类观念(知识),具有“真实、不变的本性”,
人类知识是否都是如此呢?笛卡尔认为,人类知识在真实性上是分等级的。
天赋观念是永真的,比如“上帝”观念便具有无限完满性和客观实在性。其次是关于“物体性东西”的某些观念。所谓“物体性东西”,一般地讲,就是“有广延无思维的东西”“一个能够独立存在的东西”,具体地讲就是作为“实体的表象”的东西,比如“石头”观念。笛卡尔指出:“把实体作为表象呈现给我的那些观念,要比仅仅代表方式或偶性的观念多一点什么,或者说,在它们自身中包含了更多的客观实在性”。
关于物体性东西的观念,有些是清楚明白的,比如“实体、时间、数目”以及“广延、形状、位置和运动”,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观念比声、色、味、温等观念包含有更多的“客观实在性”。所谓“客观实在性”,第三节将有讨论。“剩下来的东西,包括光、颜色、声音、气味、味道、热、冷以及其它的触觉性质,我仅仅是以那么混乱和模糊不清的方式来思考这些观念以至于我简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过笛卡尔又认为,尽管“感性知觉”或“感性意识”(不管是外感还是内感)是极其可疑和不确定的,但“我确信我甚至能在这些问题上得到真理。实际上,毫无疑问,自然所教导我的任何东西里都包含着一些真理”。比如,“当我感到疼痛时,身体就出问题了;当我饥饿或口渴时,身体需要食物和饮水,等等”。
这些都是“真”的“等级系统”中的一个等级,而等级系统的自然总体就是上帝自身,因而其中一些等级并不是简单的不完满、不够真,相反而是“上帝”的丰富性和“真”的具体体现。“我不应该对它们的实在性有哪怕是丝毫的怀疑。……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是完全免于出错的”。
所以,由于“理性的教导”,我不应该害怕感官的“错误报告”,因此,以前对感性知觉的那种被“夸大的怀疑应该被当作可笑的而予以抛弃”。
有没有完全错误的知识呢?有,这就是一再被笛卡尔提到的符合或相似论,也即反映论。
[2]26、28-29、30、80-82
笛卡尔认为,认识中之所以有错误,这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自然”(身体)的有限性所造成的,并且由于时间的匆忙,使我们来不及作出理性的考察而轻率地完全听从自然的教导所造成的。比如“热”的知觉,这其中无疑是有些真理的,但“热”毕竟不是“物体性东西”的“真实、不变的本性”,
但由于我们的自然的有限性,我们往往认为“热”是比如“火”的真实、不变的本性,因此,错误也就产生了。
至此,笛卡尔认为,人类知识体系在理性的指引下就可靠地、“分等级”地建立起来了。通过这个过程可以看出,首先,凡真的知识,必须具有当下或正在的特性。其次,凡真的知识,还必须具有不可怀疑的特性。可以说,这两点构成了笛卡尔哲学中理性主义特征的主要内容。
我们在准确、充分地把握笛卡尔哲学中理性主义特征的同时,尤其要注意到这样一点:第一节已经讲过,笛卡尔认为,当下的“我思”与反思性质的“我思(在)”是可以不加区分的,而在知识体系的重建过程中,“真”的确认同样有这个问题,具体地讲即“真”的当下确认(“明白”)与反思确认(“清晰”)的对象是可以不加区分的。
“真”的这两种确定方法,同一地构成了人类对知识体系的理性观照和重建。
说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开创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提出了二元论思想。所谓“二元”是哪二元?作为其中一元的“心灵”是比较清楚的,还有一元是什么,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这里要求我们首先搞清提出“二元论”的原因。
笛卡尔提出“二元论”的主要考虑,就是对知识、对“我思”(内容)的“源”或“因”的追求。这无疑是哲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笛卡尔之前,我们考虑的更多的是关于“万事万物”的原因,自笛卡尔始,作为主流,对“(我)思”、知识的原因的追问,原则上代替了对“万事万物”的原因的追问,从而开始了由存在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转变。
对“我思”的“源”的追问,当然不完全是对作为思维实体或心灵的“源”的追问,而是对“我思”的客观实在性的“源”或“因”的追问,因为在笛卡尔看来,思维实体与广延实体是可以相互脱离而存在的,而思维实体或“我思”中的客观实在性却不能也作如此看,否则就会有所谓“无中生有”的问题,而无中生有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