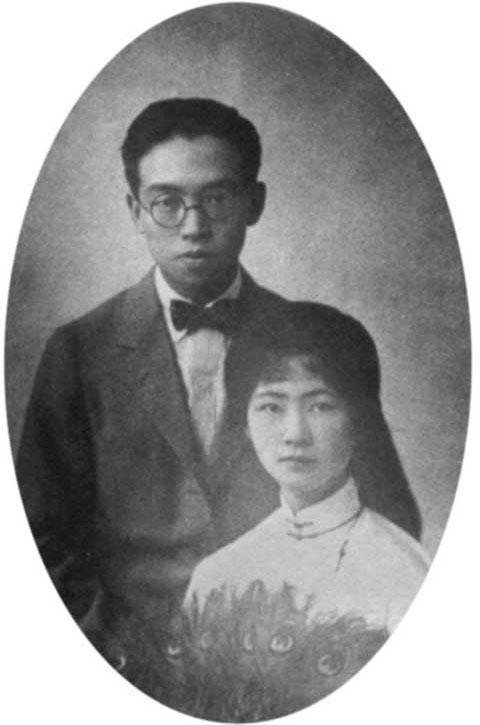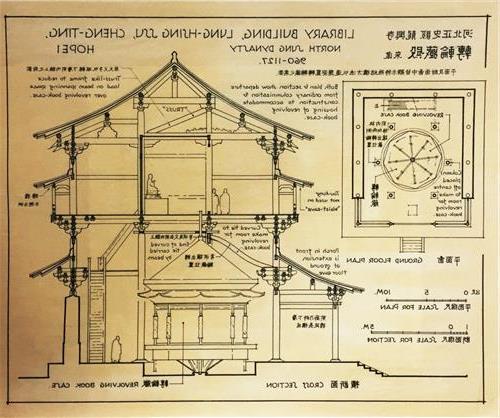梁从诫:悲壮的执着
今天,梁从诫先生的告别仪式在北京世纪坛医院举行。遗憾的是,我远在外地无法参加,只能谨以此文遥为纪念。
初次结识梁从诫先生,是在8年前。梁先生及其夫人方晶老师带我一起骑自行车去北总布胡同,踏访那著名的“太太客厅”。
众所周知,梁从诫的祖父是梁启超,父母是同为著名建筑学家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可谓出身名门。
为了表达对《营造法式》修撰者李诫的仰慕之情,在儿子出生的时候,梁思成与林徽因为他取名“从诫”,实有“望子成‘匠’”之意。尽管梁从诫后来并没有继承父母的专业,但却尽心整理、翻译、出版了父母的大量遗著,可算是不负父母之望了。
梁从诫于1932年8月4日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关于自己的出生,他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他去协和医院检查身体,挂号的时候护士问:“您是初诊还是复诊?”──如果是复诊病人,协和医院必然有以往的病历。
梁从诫回忆了一下,好像从来也没有在这里看过病,他说:“但我是在这里出生的。”护士记下他父母的姓名及出生时的家庭住址:“梁思成、林徽因,北总布胡同3号”,然后请他等一会儿。梁从诫本以为间隔了这么多年,既使能够找到病历也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没想到刚在椅子上坐下来,就听到护士叫他的名字,如此快的速度,是他未曾料到的。
拿到自己几十年前的出生记录,梁从诫自然十分激动,那病历里居然还有他当年留下的小脚丫的印迹呢!而病历上那一笔漂亮的英文字迹,竟是出自林巧稚之手。原来梁从诫是著名医生林巧稚亲手接生的!
那时,他的家就在北总布胡同3号,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
应当说,北总布胡同3号是一所很宽敞、很舒适的大宅子,也曾有过高朋满座、名人汇聚的热闹时光,无论家人还是朋友,它都有无数让人喜欢与留恋的地方。但是,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打进北平,在面临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梁思成与林徽因却能毫不犹豫地作出决断,毅然抛弃家产,与民众共赴国难。这种精神,让人敬佩和赞叹!
梁从诫对我说过:“我好像和八月很有缘:出生是在八月;随父母逃出北平是在八月;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也是在八月……”
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辗转于云南、四川,林徽因肺病复发,竟致卧床4年。在最艰苦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把家里仅有的一些东西陆续送进当铺,以换取必要的食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保持着乐观的情绪,梁思成有时和孩子们开玩笑,商量着“把这只表‘红烧’了吧!
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以苦为乐,毫不沮丧。林徽因躺在床上,写出了许多格调清新的诗句,从那里面,丝毫看不出任何颓唐;梁思成在昏暗的油灯下,编纂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当时,一些美国朋友曾来信劝他们到国外去工作或治病,梁思成回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林徽因支持他的选择。
梁从诫给我看过一张他小时候画的水彩画,在青山绿水、树丛环抱中是一些小巧的楼房和一个孩子,笔触虽然稚嫩,但画面色调明快。他说已经记不得是这幅画是什么时候的“作品”了。根据构图及内容,我推测那应当是他家住在李庄时画的,也就是他八九岁刚刚上小学的时候。
因为6岁前他生活在北平这个大城市,不可能画出田园风光。后来颠沛流离,到李庄后才暂时得到平静。有一张摄于1941年的照片:重病中的林徽因倚着一个大枕头躺在床上,梳着齐耳短发的梁再冰紧靠在妈妈身边,梁从诫头发剪得短短的,乖乖地坐在床前,眼巴巴地看着母亲。
那时尽管他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但窘困的家境给他造成了深刻的印象,使他难免会想起当年在北平那个大院子里的幸福时光。因此,当他用画笔描绘眼下四周的景物时,情不自禁地在画纸上添加了几座代表城市特征的楼房,以寄托自己的美好向往。
尽管梁从诫从幼年开始便随父母颠沛流离,但并未荒废学业。高中毕业后,他理所当然地报考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不料仅以两分之差而未被录取。本来雄心勃勃打算“子承父业”,却意外地受此挫折,最后改投北大历史系。有意思的是,五十年后梁从诫谈到此事,丝毫也没有懊悔和沮丧,反而充满了自豪。
当时他的父亲梁思成正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如果用现在许多人的眼光去看,自己的儿子仅仅差了两分却不能设法录取,实在是个笑话。但作为梁思成那一代人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如果不择手段地“走后门”才是真正可耻的!
梁从诫走出大学校门后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先是分配到云南教书,后来调回北京在外交部的一个研究所工作,“文革”中被发配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直到十年浩劫结束后才重新回到北京,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再后来,他应聘到中国文化书院担任了教授。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积极投身环境保护事业,成了一位著名的环保主义者。
1994年,梁从诫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联合创立了“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他本人担任院长。说到“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大概很少有人了解,但是它的另一个名字“自然之友”如今已是世所共知的了。这是我国第一个群众性民间环保团体,其宗旨是“开展群众性环境教育、倡导绿色文明、建立和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文化、促进中国的环保事业”。
在交谈中,我向梁从诫提出了一个始终未能理解的问题:他为什么选择了一条似乎与建筑、历史乃至编辑工作风马牛不相及的道路?
他说得很简单。那还是在当编辑的时候,由于改革形势的推进,中国的乡镇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这一“新生事物”受到各界热烈赞扬,而一篇“另类”稿件却引起了梁从诫的注意。文章尖锐地指出:乡镇企业无计划、无节制地发展,将导致污染源的扩散;如不及时采取措施,迟早会发展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严重问题。这篇文章使梁从诫受到很大震动,从此开始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
我有些不相信:就这么简单?
他微笑:就这么简单。因为那时候他并没有料到环保问题竟会复杂到这种程度,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否则他也许没有勇气进行了。如今既然已经“深陷其中”,也只有咬牙坚持下去了。
这些年来,梁从诫东奔西走,为促进中国环保工作的发展而竭力呼喊。由于他在环境及野生动物保护方面所做的贡献,曾先后获得“亚洲环境奖”、“地球奖”等等荣誉,并被评为“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最有影响的二十五位民间人士”之一,如今他已是享誉海内外的名人了。如果在计算机互联网上点击“梁从诫”这个名字,会看到与其相关的信息竟有27万条条之多。
但是,在谈话中我不能不感到他隐隐流露出的一种无奈心情。
环保工作,似乎注定是一个极难取得成效的事业──恕我直言,说“极难”已经是非常含蓄了。那简直就是一项基本不会取得成效的事业!尽管他们以超前的意识及时发现种种问题并不厌其烦地企图使人们警醒,但是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在以金钱为本的世人面前,他们往往被看作不识时务的傻子或疯子。
所以,环保工作者往往是“悲观的预言家”。比如当年那篇文章所提到的关于乡镇企业将造成污染源扩散的问题如今已成为现实,而同样的错误还在不断重演,这种情况很容易使人感到绝望。
就拿“自然之友”来说,它的入会条件是“真心实意,身体力行。”梁从诫曾经不断强调:环保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全体公众的事。他希望保护环境成为每个人自觉的行动。我总觉得似乎太理想化了一些。这就好像“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人人都与犯罪作斗争”等善良的愿望一样,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在充满忧患意识、不断遭遇挫折的境况中,仍能始终保持蓬勃高昂的乐观情绪和持之以恒的坚韧精神,这正是如梁从诫者令我最为敬佩的地方。
“人人如何如何”难以实现,那么能不能让大部分人实现?大部分人一时难以做到,那么能不能争取先有一部分人──哪怕只是很少的一小部分人──来做?如果连一小部分人也暂时不能取得统一的意见,那么起码可以从自己做起!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梁从诫正是从自己做起。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给我一张名片,是印在一张废纸上的──似乎是来自那种普通的小学生横格作业本。上面印着他的“头衔”:“自然之友”会长、全国政协常委、历史学教授。那次当我们分析他母亲所画的那张北总布胡同3号平面图的时候,他为我复印了一份,也是用了一张背面有字的“废纸”。
梁从诫外出时总习惯骑自行车。他刚当选政协委员时骑自行车去报到,竟在大门口被拦住了,因为他的模样实在不像一个“当官的”,这已成为一则流传甚广的轶事。但梁从诫绝非“有意做秀”、成心扮出一副平民姿态。他骑自行车,一方面是方便、对身体有好处,另一方面,是他自己提倡少坐或不坐汽车,所以要带头坚持骑自行车。
这种执着让我感动。
“执着”,似乎是梁家的传统。整个20世纪,梁氏三代始终活跃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梁启超为拯救危难中的国家而奔走呼号,梁思成为拯救面临消亡的传统城市建筑而奔走呼号,梁从诫为拯救世间万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奔走呼号。三代人各自所投身的事业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似乎注定都不能成功──起码暂时看不到成功。这不能不叫人为之长叹。
我说: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梁家三代人的独特经历,也许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悲壮”。
我觉得,这种悲壮的执着,也许正是将“以天下为己任”作为立世之本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特征。
听到我的话,梁从诫只是笑笑。
2002年8月,梁从诫与夫人方晶在北总布胡同老宅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