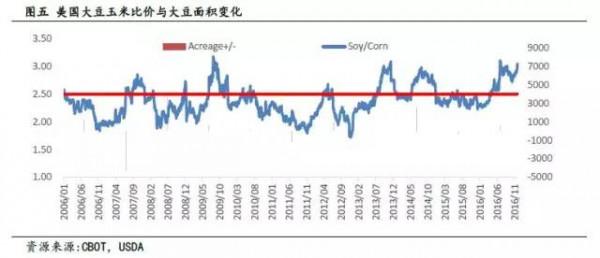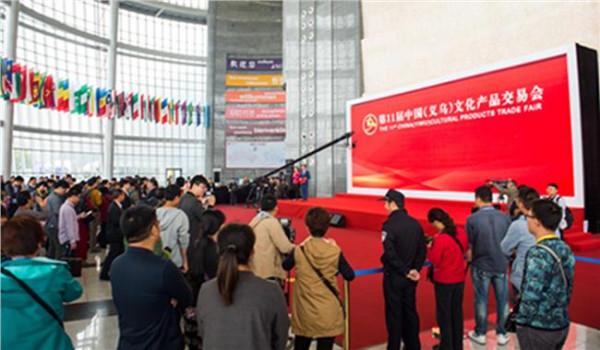陈先发明月 转:陈先发新作十七首(08年4月
《难咽的粽子》 早餐是粽子。我吃着粽子的时候 突然被一件古老的东西 我称之为“千岁忧”的东西 牢牢地抓住了。 我和儿子隔桌而坐 看着彼此 一下子瓦解在不断涌入的晨雾里 我告诉儿子,必须懂得在晨雾 鸟鸣 粽子,厨房,屋舍,道路,峡谷和 无人的小水电站里 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和 街角炸麻雀的油锅里 在尺度,愿望,成败和反复到来的细雨里 在闹钟的表面 在结着黄澄澄芒果的林间 在我们写秃掉的毛笔里 处处深埋着这件东西。
像一口活着的气长叹至今 这是白发盖顶的教义。 或许,心口相传将在我们这一代结束 将不再有人 借鸟鸣而看到叶子背面的 永恒沉没的另一个世界 另一片永不可犯的黑色领域。 除了那些依然醒目的―― 譬如,横亘在枝桠间的月亮 即便在叛逆眼里 在约翰•列侬和嬉皮士眼里 也依然是一句古训 让我们认识到,从厄运中领悟的与 在街头俯首可拾的, 依然是毫无二致。
如果我们那么多的安慰 仅仅来自它已经被毁掉的,脆弱的外壳 为什么仍须有另外的哲学 另外的折磨?在这盘难以咽下的粽子和 它不可捉摸的味道之上―― 在这个安静的早晨。
为什么? 2009年5月 《良马》 半夜起床,看见玻璃中犹如 被剥光的良马。
在桌上,这一切―― 筷子,劳作,病历,典籍,空白。 不忍卒读的 康德和僧璨 都像我徒具蓬勃之躯 有偶尔到来的幻觉又任其消灭在过度使用中。 “……哦,你在讲什么呢”,她问。 几分钟前,还在 别的世界, 还有你 被我赤裸的,慢慢挺起生殖器的样子吓着。
而此刻。空气中布满沉默的长跑者 是树影在那边移动。 树影中离去的鸟儿,还记得脚底下微弱的弹性。 树叶轻轻一动 让人想起 担当――已是 多么久远的事情了。
现象的良马 现象的鸟儿 是这首诗对语言的浪费给足了我自知。 我无人 可以对话,也无身子可以出汗。 我趴在墙上 像是用尽毕生力气才跑到了这一刻 2009年5月 《绳子的两端》 夏夜, 乐于睡在自家小庭院里。
死去的亲人化作微风 摇着我的椅子。 松驰下来的绳索上 吊着当天的脏衣服。 我睡着了 又反复醒来 像绳子的两端仍有呼吸 我反对阐释两端。 也反对述说中间的部分。 一如身旁树丛 我知道那里有一道长廊远未建成―― 在它的尽头 有红砖的如来。
钢筋搅拌水泥的上帝。或者说, 有卡夫卡在 他的地窖中 博尔赫斯在曲折的图书馆里。我看见, 他们在恐惧中微笑。他们在随时随地说错话。他们在拒绝。 我不是他们。
我反对他们。 我唯有脏衣服孤单迷人 我在人间鼾声大作 过度的困惑已像月轮渐隐 我的方法全是古老的方法。 我从梦中醒过来。 我从爬满墙头的 金银花模糊的语调中醒过来。 我从一件 脏衣服上醒过来。
我在醒着的时候再次醒过来。 但我,假托自己永远活在两端之间 2009年5月 《中年读王维》 “我扶墙而立,体虚得像一座花园”。 而花园,充斥着鸟笼子 涂抹他的不合时宜, 始于对王维的反动。 我特地剃了光头并保持 贪睡的习惯, 以纪念变声期所受的山水与教育―― 街上人来人往像每只鸟取悦自我的笼子。
反复地对抗,甚至不惜寄之色情, 获得原本的那一、两点。 仍在自己这张床上醒来。 我起誓像你们一样在笼子里, 笃信泛灵论,爱华尔街乃至成癖―― 以一座花园的连续破产来加固另一座的围墙。
2008年9月 《暴雨频来》 暴雨无休止冲刷耳根 所幸我们的舌头 是干燥的 晚报上死者的名字是干燥的 灯笼是干燥的。
宿命论者正跨过教室外边的长廊 他坚信在某处 有一顶旧皇冠 始终为他空着 而他绝不至再一次戴上它 绝不至与偶尔搭车的酷吏为伴 不与狱卒为伴 不与僧人为伴 有几年我宁可弃塔远游 也不与深怀戒律者并行 于两场暴雨的间歇里。
我得感谢上苍,让我尽得寡言之欢。 我久久看着雨中的 教堂和精神病院 看着台阶上 两个戴眼镜的男子 抬着一根巨大圆木在雨中飞奔。 鞭出来历不明的人 是这场暴雨的责任 当这眼球上 一两片儿灰暗的云翳聚集 我知道无论一场雨下得多大 “丧失”――这根蜡烛 会准时点亮在我们心底 所幸它照出的脸 是干燥的 这张脸正摆脱此刻的假寐 将邀你一起 为晚报上唯恶的社会公器而哭 将等着你,你们 抬着巨大圆木扑入我的书房 取了我向无所惧的灯笼远去 2009年5月 《晚安,菊花》 晚安,地底下仍醒着的人们。
当我看到电视上涌来 那么多祭祀的菊花 我立刻切断了电源―― 去年此日,八万多人一下子埋进我的体内 如今我需要更多、更漫长的 一日三餐去消化你们 我深知这些火车站 铁塔 小桥 把妻子遗体绑在摩托车上的 丈夫们 乱石中只逃出了一只手的 小学生们 在湖心烧掉的白鹭,与这些白鹭构成奇特对应的 降落伞上的老兵们 形状不一的公墓 未完成的建筑们 终将溶化在我每天的小米粥里 我被迫在这小米粥中踱步 看着窗外 时刻都在抬高的湖面 我说晚安,湖面 另一个我在那边闪着臆想的白光 从体制中夺回失神的脸 我说晚安, 远未到时节的菊花。
像一根被切断电源的电线通向更隐秘的所在 在那里 我从未祈祷,也绝不相信超度 只对采集在手的事物 说声谢谢―― 我深知是我亲手埋掉的你们 我深知随之而来的明日之稀 2009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一周年。
《怀人》 每日。在树下捡到钥匙。 以此定义忘却。 又以枯枝猛击湖水, 似布满长堤的不知不觉。 踏入更多空宅。 四顾而生冠冕。 还记得些什么? 蓦然到来的新树梢茫然又可数。
二十年。去沪郊找一个人。 青丘寂静地扑了一脸。 而我,斑驳的好奇心总惯于 长久地无人来答―― 曾几何时。在你的鞍前马后。 年青的体用轻旋。 一笑,像描绘必须就简, 或几乎不用。 空宅子仍将开花。 往复已无以定义。
你还在那边的小石凳上, 仍用当年旧报纸遮着脸。 2009年4月 《可以缩小的棍棒》 傍晚的小区。孩子们舞着 金箍棒①。红色的,五毛或六毛钱一根。 在这个年纪 他们自有降魔之趣 而老人们身心不定 需要红灯笼引路 把拆掉的街道逡巡一遍,祝福更多孩子 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们仍在否定。
告诉孩子 棍棒可以如此之小,藏进耳朵里。 也可以很大,搅得伪天堂不安。 互称父子又相互为敌 形而上的湖水围着 几株老柳树。
也映着几处灯火。 有多少建立在玩具之上的知觉 需要在此时醒来? 傍晚的细雨覆盖了两代人。 迟钝的步子成灰。 曾记起新枝轻拂, 那遥远的欢呼声仍在湖底。 注①:语出《西游记》。见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类尽除名》。
2009年3月 《孤峰》 孤峰独自旋转,在我们每日鞭打的 陀螺之上。 有一张桌子始终不动 铺着它目睹又一直被拒之于外的一切 其历炼,平行于我们的膝盖。 其颜色掩之于晚霞。
称之曰孤峰 实则不能跨出这一步 向墙外唤来邋遢的早餐, 为了早已丧失的这一课。 呼之为孤峰 实则已无春色可看 大陆架在我的酒杯中退去。 荡漾掩蔽着惶恐。 桌面说峰在其孤 其实是一个人,连转身都不可能 像语言附着于一张白纸。
其实头颅过大 又无法尽废其白 只能说今夜我在京城。一个人。远行无以表达隐身之难。 2009年3月 《蟾蜍》 脚下 蟾蜍忽然一动。 头顶 孤鸟回村,拉着一根直线。 有更多无邪的线条 像婴儿无声滑下楼梯 我靠在电线杆上抽烟 看着从大坝和泡沫中穿行的铁路 看着幻觉的蟾蜍: 他们是各自的发光体。
跟我遭受的政治暗算不同 他们 迷信无为的哲学。 像风中清净的树枝,挥动一笔而成的《快雪时晴帖》 区区二十八字 为了完成俗世的誓言。
也为了躯壳在其间更快地分解―― 听它沉闷的“咕咕”声 仿佛舌头上压着一座寺院。 因其母语 赋予河对岸以更广大的沉默 它的丑陋构成重檐: 我不得不 ――隔绝,与那些生下我们的人。
在薄暮的草丛 收拢它们散于各处的器官 其间有离别。有不忍。有哭泣。有各种异己的标本。 那些线条 状如故土之名。 柜子里,有它们无端的,缩小的尸体。 2009年3月 《听儿子在隔壁初弹肖邦》 他尚不懂声音附于何物 琴谱半开,像林间晦明不辩。
祖父曾说,这里 鹅卵石由刽子手转化而来 对此我深信不疑 小溪汹涌。未知的花儿皆白 我愿意放弃自律。 我隔着一堵墙 听他的十指倾诉我之不能 他将承担自己的礼崩乐坏 他将止步 为了一个被分裂的肖邦 在众人瞩目的花园里 刽子手难免物伤其类 像绝望的鹅卵石被反复冲刷 世界是他们的 我率“众无名”远远地避在斜坡上 2009年2月 《正月十五与朋友同游合肥明教寺》 散步。
看那人,抱着一口古井走来 吹去泡沫 获得满口袋闪烁的石英的剖面―― 我们猜想这个时代,在它之下 井水是均衡的 阻止我们向内张望 也拒绝摄影师随意放大其中的两张脸 而头脑立起四壁 在青苔呈现独特的青色之前。
我们一无所思 只是散步。散步。散步,供每一日的井水形成。 有多年没见了吧 嗯 春风在两个拮据的耳朵间传送当年的问候。 散步 绕着亭子 看寺院翻倒在我们的喉咙里 夜里。
井底的稻田爬上我们的脸哭泣 成为又一年的开始 2009年2月 《十字架上的鸡冠》 在乡下 我们是一群雷劈过的孩子 遗忘是醒目的天性。 从未有人记得,是谁来到我们的喉咙中 让我们鸣叫 任此叫声――浮起大清早无边的草垛。
而所有文学必将以公鸡作乡村的化身: 当词语在手上变硬 乡村列车也籍此,穿过我的乱发而来。 公鸡的叫声,在那颅骨里 在灯笼中 在旧的柏油马路上 鸣叫之上的隐喻, 点缀鸣叫之中的孤单。
倘我的喉咙,是所有喉咙中未曾磨损的一个。 从未有人记得,是谁在逼迫我 永记此鸣叫, 在我恒久沉默的桌面之上―― 像记得那滋润着良知的 是病床之侧的泪水 而非冥想,或别的任何事物 永记那年,十字架上鸡冠像我父亲的脑溢血一样红。
2008年11月 《湖边》 垂柳摁住我的肩膀,在湖边矮凳上 坐了整个下午。今年冬天,我像只被剥了皮的狗 没有同类。也没有异类。 没有喷嚏。也没有语言。 湖水裹着重症室里老父亲 昏馈的脑袋伏在我的膝上。
我看见不是我的手 是来自对岸的一双手撑住他。 僵直的柳条, 垂下和解的宫殿。 医生和算命先生的话, 听上去多么像是忠告。 夜间两点多,母亲捧着剥掉的黄皮走来 要替代我到淤泥的走廊上,歇息一会儿 2008年12月24日 《翠鸟》 池塘里, 荷叶正在烂掉。
但上面的鸟儿还没有烂掉―― 它长出了更加璀璨的脸。 时而平白无故地 怪笑一下。 时而递给我一个杯子, 又来抢这只杯子,剥去我手心的玻璃。
我们差不多同时 看见了彼此。却从未同时忘掉。 如今有更多容器供我回忆, 复制老一辈人的戒心。 还有许多自我。 有许多平衡。 哦,这里有多么璀璨,多么忠实的脸。 让母亲在晚饭中煮熟更远的亭子。
而我们相互的折磨将坚持到第二天早晨。 2008年9月 《同类》 早上起床,看见树梢上 某个东西正在远去。 朝它深深鞠了一躬――― 不管它是什么, 我必须认之为同类。 我记得一些事,为一、两件小事活着 又时时避开它们 这才有踝骨中的誓言, 满桌子,对抗的经卷。
树梢淡出淡入, 从未中断过对我们的记录。 他们说些什么,我却 全然不顾了――― 昨夜湖边,众人哭喊着 “周琪,周琪”: 等着尸体从水底浮上来。
早上,湖水还在。 警察和隐士还在。 “周琪”是谁,是我的同类? 或许不是。如果她不浮上来 我将度过这一日。 树梢下不可更改的荫凉 正该如此地,不为人所觉 2008年8月 《两次短跑》 几年前,当我读到乔治.
巴塔耶, 我随即坐立不安。 一下午我牢牢地抓着椅背。 “下肢的鱼腥味”,“对立”:瞧瞧巴大爷爱用的这些词。 瞧瞧我这人间的多余之物。 脱胎换骨是不必了。 也不必玩新的色情。
这些年我被不相干的事物养活着。 ――-我的偶然加上她的偶然, 这相见叫人痛苦。 就像15岁第一次读到李商隐。在小喷水池边, 我全身的器官微微发烫。 有人在喊我。我几乎答不出声来――― 我一口气跑到那堵 不可解释的断墙下。 2008年4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