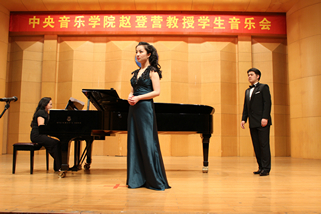赵毅衡私生活 学生眼中的赵毅衡老师?
仍然记得遇到老赵的那个九月的黄昏。
那是我研究生生涯的开始,当时为了完成出版社两本小说的约稿,退掉学生宿舍,临时到学校教职工小区租了一套小房子。小区是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略显灰暗的老楼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爬山虎,坚韧苍翠的植被似乎在诉说着这里的古旧与寂寞。
当我抱着一摞书刚要跨入自己所住的单元时,他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从单元楼走出。茶色的墨镜,略显倾颓的背影,没错,就是他!我的心砰砰直跳。等他走远,我才敢回头张望,看到自行车上赵老师的背影消融在橘红色的黄昏中。
没错。我确定他就是传说中的赵毅衡--那个早年留学海外,有着诸如卞之琳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伯克利博士,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终身讲席等一系列头衔的大学者。在这个导师普遍被称为“老板”、高校海归人才如织的年代,自己忽然因为这样一次偶遇而激动是别有原因的。
记得早在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酷爱读书的我就记住了这样一个名字。从父亲的书架上翻过两本厚厚的《美国现代诗选》,编译者便是赵毅衡;读过小说《金银岛》,译者还是赵毅衡。曾有一段时间迷上高行健的戏剧,在互联网上翻看所有评述,发现评述最精彩的还是赵毅衡。直到读大学后才知晓,有位在海外多年的大学者退掉英国国籍,卖掉伦敦的别墅,叶落归根来到西部高校川大任教。
读研以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偶尔能在楼道里听到他的脚步,却只敢远远躲开。赵老师那段时间刚好住在我临时居所的楼上。晚上翻看他的随笔集《对岸的诱惑》《有个半岛叫欧洲》的时候,常常觉得恍如梦幻。我翻看着这些有趣、使人敬畏的文字,而它们的作者却正住在楼上。
每当翻看莎士比亚剧作,遇到难懂之处常常有种到楼上敲门请教的冲动。然而我没有,害怕破坏这位大学者的清净。
学术地板工
赵毅衡老师教符号学与叙述学。当我和几位死党选修了他的课程,溜入教室之后,发现这里的气氛俨然不同。虽是研究生课堂,却聚集了上百人,把偌大的教室塞地满满当当。仔细观察,既有不少人到中年的成人,还有不少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有年轻的学子,有头发略白的老者,有功成名就的学校教授,还有孕妇出没。
赵老师果真学识丰富,声音磁性而洪亮,简单几张PPT却简简单单道出学问真谛。如果说学术世界是一个庞大的花园,那么他的课程则能引领着学生们很快穿越眼花缭乱的秘境,直达学问的边缘领地。他可以简单地指一指,诺,你的身后就是无数学人所探索出的领地,而我们则正站在这领地的边缘,前面那片黑暗,便是学术的未知地了,我们的任务便是在未知地里开垦出花园。不容多讲,全场人都能感受到学术未知地的黑暗、神秘与刺激。
老赵很幽默,善于自我调侃,于是我们一帮人有时会放下应有的尊敬,称为“老赵”。面对着课堂黑压压的人,他有趣地调侃,“没事,下节课来人就少了。我知道你们就是想来看看赵毅衡是何许人也,结果一看——就是一个糟老头子,下节课就不会来了。
”老赵自称受虐狂,最希望便是有学生向他提出挑战。为此他还精心建立“符号学论坛”网站,公布自己的邮箱。“问题不隔夜”是老赵的承诺。只要有学生向他提出问题,他一定在最快的时间里回复。
老赵讲课深入浅出,也是出了名的认真。尽管上百人都听得津津有味,他说为保证教学质量,还是要通过作业的形式了解学生对内容的理解程度。第一次交作业,当我把写满5页A4纸的作业用电子邮件发给他之后,让我没想到的是,一周后的课堂上,赵老师捧着一摞打印好的作业,一份份亲手发到学生手里。
翻开作业,发现赵老师的批改细致而认真。“有错题的同学记得把题目修正后返给我”,老赵高声宣布。每一学期的课堂,都能发现老赵的学术脚步在迅速向未知领域推进。同一门课程时隔半年,会发现课件内容已经完全变了。
老赵极为博学,也极其低调谦逊,虽然带领着一帮优秀的学生做学术研究,却喜欢自称“地板工”。他所教的符号学与叙述学本来就是横跨整个大文科的专业,其间涉及的知识更是庞杂。老赵的博学算是众所周知的,他出版过小说,写过热播电视剧。
这些被他称之为“小玩意”的创作,却都有口皆碑。他做过极优秀的翻译,80年代的几部学术著作如《远游的诗神》所滋养的学子如今已经是全国各大高校里的学术主流人群。然而,他却选择了一种默不作声的存在方式,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向学术的未知领域进发。
当我们学生偶然向他提到一本他没读过的新书之类的话题,下次上课时便知老赵已经仔细读完了。面对课堂不同国家的学生,某次老赵出于礼貌居然分别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同他们对话,几种外语在他嘴中切换自如,其语言能力很让我们这些学生汗颜。
他曾在一本书里写道,对于学术本身的意义,“正如一出戏剧的优美,不必由剧院的地板工来提醒观众。如果说我们有什么,或者将要有什么可以自夸之处,那或许就是,通过我们卑微的劳作,观众们已经,或者对将要上演的剧目感到熟悉、亲切,甚至狂热。”
不可否认,老赵是个狂热的“学术地板工”。老赵极少缺课,一次因为学校开会不得已停课一次,后来就听到了老赵的无奈自嘲,“上节课被学校叫去,本来说是开会,结果是填表,填了一堆表。我都成了填表教授了。”
曾听闻学友谈起,2008年5.12大地震后,余震不断,天旋地转。川大河畔堆满了帐篷,聚满了惊慌的人群。而老赵当时住在三十楼,周围人都跑光了只有他还独坐在家中搞学问。别人提醒,赵老师,危险啊!三十层楼,一点小余震都晃的不得了,更别现在这情况了。赵老师摇摇头,“能修三十层,肯定是防震的!”之后继续埋头做学问。
那个点灯的老男人
在我刚选老赵课之后,又一次楼梯口的偶遇,他认出了我。曾经的激动与羞怯很快变为平缓,在不断的相遇与求学中,时光一晃而过。尽管小说写完后便搬离了老楼,可在老赵的影响下却开始走向真正的学术之路。
关于学术期刊版面费,一直是研究生们私下的话题。哪个期刊好发,或者哪个期刊版面费低,几乎在每个研究生心里都有了一套谱系。毕竟,学校规定毕业要发文章,交版面费发吧,觉得没有尊严。不交吧,想评硬本事发表又很困难,文科生尤其如此。
不过在老赵的课上,他总能迅速给学生一个可以填充展开的前沿框架,只要具备足够的努力与细致去填充框架,便不难写出有创建性的学术文章。每学期末老赵都会把一批新产生的学术论文作为成果推向各大期刊。捧着极有质量与操守的期刊,翻看自己发表的掷地有声的论文,越发觉得自己的研究生生涯含金量十足。
老赵打造了一个大文科概念范畴的课堂,这同他反对过于死板的教学和研究分科有关。在老赵的课堂上,也结识了很多朋友。有研究生的同学,有教授讲师。原本应隶属于师生关系的人群,只要来到老赵的课堂却都有了共同的身份与称谓:学友。有些毕业的硕博奔赴全国各地高校的教研岗位之后,我们之间还时常通信,讨论学术问题,最后总是询问赵老师是否还好。
一次课余与老赵闲聊,谈及学术与文艺创作,老赵的一句话突然让我体会到他生命深处的坚持,他说:即便死了,也要把理论做好!当老赵说提高嗓音说完那句话,我觉得这位充满浪漫与风度的老男人身上,散发着另一种闪亮的光彩。
“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在老赵身上我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学问迷宫的背后总藏着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门的那边黑暗、神秘,同时也充满了智慧与刺激。因此总刺激着人类在认知世界与认知自我的路上前行。这是一场贯穿人类文明史的接力大赛,既是光明对黑暗的接力,已知对未知的接力,也是时间跟时间的接力,知识跟知识的传承。
所谓导师,既是在未知世界的探寻者,也是对后来人的传承者。有一口气,点一盏。一盏灯照亮未知的路途,也照亮后来者的面孔。时代轮转,一条路上人会泯灭,灯光却永恒。这些灯构筑着世界的坐标,诉说着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将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