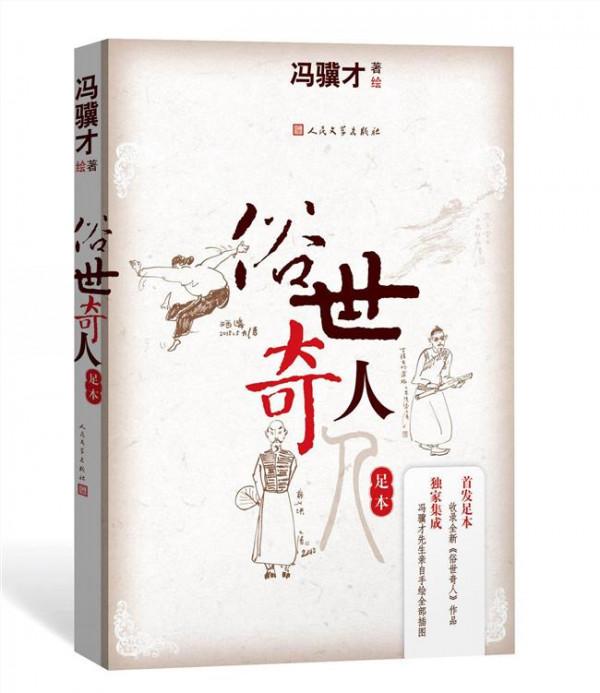于是之幼学纪事 于是之《幼学纪事》原文
“别考了。现在大伙都不富裕,你也不小了,出去找点事做吧。”
我沉默了,母亲也无言。吃人嘴短,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我合上了笔记本和书,从此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
“找点事做”,那时很难。先要买些“履历片”回来填写,写好后再托本家、亲戚四面八方找门路,呈送上去。回音,大都是没有的,但是要等待。母子两个茫茫然地等着,等着一个谁也不愿多想的茫茫然的未来。
茫然中还是有事可做的。子承母业,去当当。比每天上学稍晚的时间,便挟个包去当铺,当了钱出来径直奔粮店买粮。家底单薄,当得的钱,只够一天的“嚼裹儿”,计:棒子面一斤,青菜若干,剩下的买些油盐。当得无可再当了,便去押“小押”。
那是比当铺更低一等,因此也是更加苛酷的买卖。他们为“方便”穷人计,可以不收实物,拿了当铺的“当票”就能押。押得无可再押了,仍旧有办法,就是找“打小鼓的”把“押票”再卖掉。卖,就更“方便”了。每天胡同里清脆的小鼓声不绝如缕,叫来就可以交易。一当二押三卖,手续虽不繁难,我和母亲的一间小屋里可就渐渐地显露出空旷来,与老郝叔的家日益接近。
或者我是个侥幸者,或者生活本来就是由许多的“偶然”所铸成。辍学以后,在过着“一当二押三卖”的日子里,我居然进入了当时的最高学府辅仁大学中文系,当了一阵子一文不花的大学生。那是由于有几位好友,和我们住得邻近,他们比我年纪大些,都是那所高等学府的学生。
他们同情我的境遇,于是就夹带着我混进了辅仁大学。事是好事,但头一天我一进校门,就觉出浑身上下都不自在起来,眼睛只敢看地板,看楼梯。好像是走了一段很长的路,才进了教室。
教室里学生们大部已经就座,只有我兀立一旁,这就更增加了我的紧张。我真想掉头归去,回到我的家,回到我或当或押或卖的“自由”的生活中去。我的热心的好友走去找他的几个同学,只见他们嘁嘁喳喳了一阵以后,就指着一个空位子告诉我:“你今天先坐这儿吧。
”我于是坐下。心想,我明天坐哪儿呢?果然,第二天我就更换了一个地方。此后天天如是,先是我浑身不自在地进入教室,他们则照例要嘁嘁喳喳一阵,而后为我指出一个安身的所在。
尽管是这样,然而听课还是令我神往。现在记得起的是一位孙教授讲秦少游,一位顾教授讲辛弃疾。从他们精到的讲解里,叫我领略出这些大词人的妙处:他们能在婉约近人的文字中抒发出忧国、爱国的深情以至豪情来。多么美呀,多么精巧啊,我们祖国的语言!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都像是一个可爱的小精灵,只要你调度得当,它就能把你心里的最细微的情绪表达出来!
听课虽然有趣而令人神往,但内心的恐惧却不容易消除。日久天长,我才明白,高等学府里的教授们是不管点名的。学生们都有固定的位子,点名的人只能在窗外,看位子空着的便画“旷课”,位子上只要坐着人,不管是谁,他便画“到”。
我之所以能坐上位子,而位子又须每天更换,就是由于每天总免不了有人旷课的缘故。但在当时,我于听课神往之余,心里总不免于忐忑,谁知道那些花了钱的学子什么时候会突然闯进教室把我撵走呢?因此,我那时常生做贼之感,觉得自己是一个偷窃知识的人。
此后,靠朋友们的帮忙,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业。那时我只有十六岁,而我的同事们,比起我的年龄来,翻一番的寥寥可数,多数都是翻了两番以上的老头子们。他们同我无话可讲,我也只能报之以沉默。虽然有了职业,但并不足以糊口,前途依旧茫然。只是偶然在一根电线杆子上的招生广告里,我又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就在我做事的地方附近,有一家中法汉学研究所,广告上说那里要办一个法文研究班,每周晚上开两堂法语课。一个“汉学”,一个“法语”,再加上是个夜校,这对我简直是个天赐的机缘。于是我去报名了。经过口试,我说了我对“汉学”和“语言”的兴趣,很快便通知我被录取了。从此,我又进入了另一所特殊的高等学府。
这个夜校简直是一座法兰西文学的殿堂。头一年照例是从字母念起,学些简单的对话和短文。第二年选文里可就出现了莫里哀和雨果。依次读下去,到了最后的一年,就读到了19世纪末的散文和诗。教授讲得津津有味,学生们也听得入神。以至于在上课时,我竟仿佛觉得自己已近“雅人”。但是,在课前和课后,我却不能不继续过我的“俗人”的生活。
我那时住在北京西单,每天需步行过北海大桥,才能到达近东四我上班的地方。平时只带一顿午饭,不过是窝头小菜之类。赶到上夜校时,就需带上晚餐了。把窝头带进法兰西文学的殿堂,已经很不协调,更何况“殿堂”里是只烧暖气而不生炉火的。
到了冬天,暖气烤不了窝头,冷餐总不舒服。幸好,“殿堂”之外的院子里有一间小厕所。为了使上下水道不至于受冻,那里面安着一个火炉。于是这厕所便成了我的餐厅。把窝头掰为几块,烤后吃下,热乎乎的,使我感到了棒子面原有的香甜。
香甜过后,再去上课,听的偏是菩提树、夜莺鸟这样的诗情。下课以后,又需步行回家。天高夜冷,静得可以听见自己的足音。且走且诵,路成了我最好的温课的地方。早晨上班也一样,将生字写在小纸片上,看一眼就可以背一会子,也发生不了什么交通事故。据我那时的经验,从西单走到东四,少说可以背下四五个单词来。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我衷心地喜欢这两句话,读起来总感到亲切。我庆幸自己在那样恶劣的政治制度下竟遇上那么多好的老师和好的朋友,他们为我启蒙,教我知道书这种东西的宝贵,使我没有胡乱地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