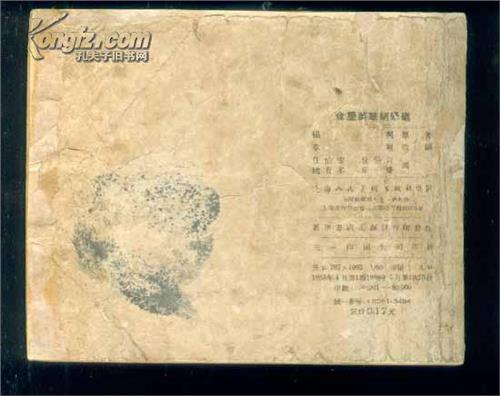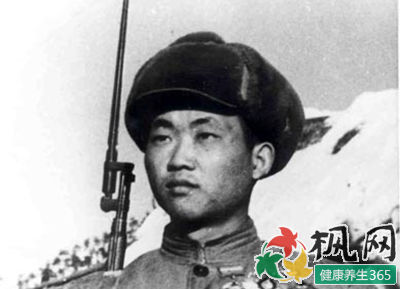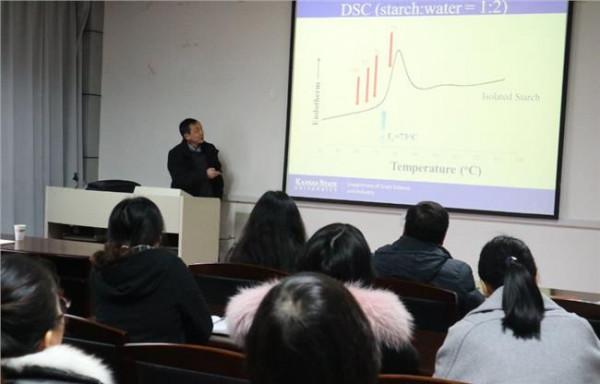美国人怎么看胡修道 美国人怎么看日本人
邱震海:我们将一连五天向大家介绍日本人和中国人各自一些国民性格和国民心理结构。昨天跟大家分享了由日本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土居健郎先生,在70年代写的一本叫《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也就是日本人如何看自己。那么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看美国人是怎么看日本人的?
《菊与刀》
大家一定听过一本书《菊与刀》,这本书想必它的历史要比《日本人的心理结构》早,因为它是1946年写的,而且作者叫鲁恩·本尼迪克特,是一位美国文化学家、人类学家。
鲁恩·本尼迪克特
并不是说这本书古老就介绍,关键是《菊与刀》这两个字。“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象征。一个是美的、一个是武的,一个是顺从的、一个是反抗的,一个是美丽的、一个是血淋淋的。所以这种性格可能是交织组合在大和民族的深处,也成为它心理结构或者国民精神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边。
关键还不在于此。你看我老说关键不在于此,最最关键的就是,这本书在1946年出版,而鲁恩·本尼迪克特作为美国非常有名的人类学家,是一位女士,她1944年授命于美国的军政府,因为当时正在进行太平洋战争,美日交战,所以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日本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于是就委托一个人类心理学家,说你来研究,我们马上就要把日本人打败了,打败之后日本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如何统治?所以当时美国面临的困难,一个是如何统治即将被战败的德国,一个是如何统治即将被战败的日本。
可想而知,当时美国人非常不了解日本人,当时的美国非常缺乏日本问题专家。于是这位本身不是日本问题专家的美国女人类学家,就承担了这个任务。非常艰难,在美国境内展开了对居住在美国境内的日本侨民的调查、调研工作。在两年之后写成了这本书。最后她有一章专门是建议美国的军政、当局如何去对付投降之后的日本人。
总而言之,昨天我们讲到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当中有一种对别人有一种依赖、有一种人情、有一种义理的感觉,同时有一种对自由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欧美人。这本书里面同样写到了日本人的这些民族性格,而且她写的日本的民族性格之一,就是要每个人都要各得其所、各得其位。
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当中,他对社会的理解、他对自己秩序的理解,他永远认为是有一个等级的。比如说天皇就是天皇,天皇是永远不会推翻的。这一点跟我们中国人是完全不同。中国人几千年历史上皇帝是可以推翻。起义就可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胜利的就可以当皇帝,皇帝是可以一届一届被换的。所以从秦朝到汉朝,到这个元朝、宋朝、明朝、清朝等等,皇帝是不断的在换。而日本人天皇是永远不换的。所以从这意义上说,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当中有各得其所、各谋其位的一种观点。
这其实也是一种依赖。昨天我讲过了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当中说,其实国民对天皇是有一种永恒的依赖感。同样雇员对他的公司、下属对他的上属,也是有一种永恒的依赖感。所以日本人40、50年在一个公司打工是毫无稀奇的。
这点跟香港同胞有很大的不同。香港人一年跳三次槽,非常的不忠诚。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当中,有这么一种秩序感,而这种秩序感在鲁恩·本尼迪克特看起来,是导致日本人在战后可能不太顺从美国军政府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当然这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其它的原因。比如说她还讲到日本人对整个武士道精神的理解、对人的精神的理解。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说在战争当中有一个伤兵,上面的军官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已经受伤了?然后那个伤兵站起来说,报告长官我没有受伤,我已经被打死了。
所以可想而知,日本人从小的教育,就是那种武士道精神,精神能够战胜一切。我们中国人以前说人定胜天,这一点上好像似乎中日两国,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中国人有等级观念,但这种等级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但是日本人的等级观念往往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这位《菊与刀》这位作者,美国的非常著名的女人类学家,她就描绘日本人顺从的一面,同时有武士勇敢反抗乃至血淋淋的一面。最后她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日本人是不可能被一个外来的民族所统治的,要统治像这样的一个民族,必须要了解这个民族的特点,必须从他的心理结构出发,必须从他对道德秩序、人的等级秩序、尤其对天皇的尊严这一点上来出发。于是这个结论不用她得出,电视机前的您和我,我想我们大家都得出这个结论。
1946年,这位非常可爱的美国女人类学家告诉美军的长官们,天皇是不可以推翻的,天皇制度一定要维系的,因为只有通过天皇我们才能够去统治这样的一批日本的臣民,使他们成为美军的顺民。
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有了这本《菊与刀》,美国的最高决策当局就保留了天皇的体制。虽然战后的天皇已经不是战前的天皇,他的军政大权远远缩小,但是由于天皇体制一直沿用了下来、遗留了下来、延续了下来。尤其是由于天皇被保留了下来,所以在所有日本人的心目中,都找不到一个战争的责任者,因为战前他们为天皇而战,战后天皇依然在,你说谁是战争的责任者?难道你要他们指责目前还在位置上的那个天皇吗?
所以从这一点上,日本人战后对历史的清理,跟德国人对历史的清理形成一个截然的反差。我当年在德国生活,德国人非常简单,由于他们找到了一个战争的责任者,那个人就是希特勒,而希特勒已经灭亡了,这个体制已经灭亡了,所以一个全新的德国可以产生,整个德国人都感到非常轻松。这种轻松从某种程度上,必须承认,是一种逃遁。
但是可怜的日本人,他逃遁也无处逃遁,因为那个天皇还在东京存在。于是对历史的清理和反思,在战后60多年就这么模模糊糊遗留下来。也许《菊与刀》是战后一本非常重要的有关日本的研究著作,但是它为战后60年的亚洲和世界留下了无穷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