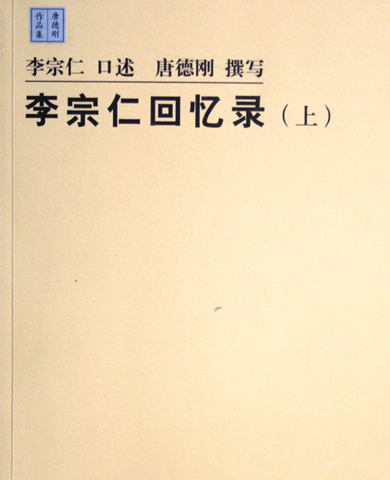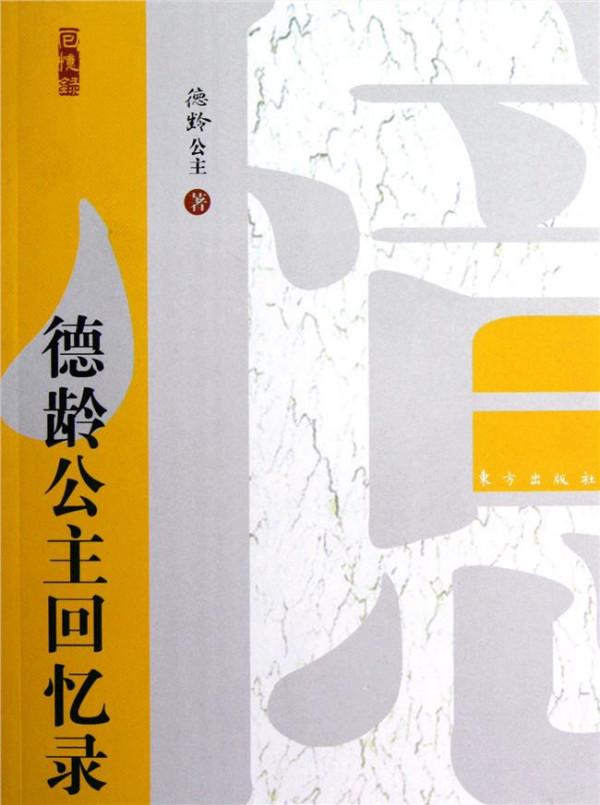李宗仁回忆录版本 杂说《李宗仁回忆录》的版本
最初读到《李宗仁回忆录》是在1980年,距今已三十年,那是作为“广西文史资料专辑”,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注明“内部发行,未经许可,不得翻印”,全书共八编七十二章,洋洋五十六万字,分上、下两册,定价为人民币三元二角。
当年6月印出第一版,是这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著述最早的版本,据说印数达六十万册,后又一再加印。从了解民国史及李宗仁本人经历的阅读需求看,除了“文革”前发行范围极其有限的文史资料散册外,该书实为当时唯一最系统、最详实的长篇读本,受欢迎程度自不待言。
回忆录正文前,有出版单位署于该年3月21日的“出版说明”,称对原稿进行了校订,对有明显错误的人名、地名、时间、部队番号和错别字作了改正,“但对其中一些不符史实的记述和错误的论点,为了保持原稿的本来面貌,未作改动,有的只加注说明”。直接改正之处,书中无迹可寻,而某些章节末的“编者注”,大都引用全国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中相关的回忆文字,作为客观的参照。
这个最早的版本,未署美籍华裔历史学者唐德刚的大名,尽管“结论”部分提及,这是1958年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为保存当代史料而促成,“该校旋派研究员唐德刚博士前来助理撰述,中、英文稿同时并举”;并说“我口述后,由唐笔录,整理成篇,然后再就有关史料,详加核订,再经我复核认可后,视为定稿”,但既然没有署上唐氏之名,当时读过此书便不会对他留下任何印象,更不会认为其对该书的贡献可与书中的“我”即李宗仁本人相提并论。
但正如台湾著名作家李敖所言,“《李宗仁回忆录》的得以完成,除李宗仁本人外,有一位关键性人物,就是唐德刚先生。”(见《推荐〈李宗仁回忆录〉》,载《李敖大全集》第28册,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2000年版)从1958年暮春开始,唐德刚向李宗仁断断续续访谈3年,又悉心整理、撰写并修改4年。
他说,李氏流寓美国期间,身无片纸数据,只能就记忆含混地口述,从有关史料搜集、写作计划拟订直到全部文稿撰写,一切都由他“偏劳”,更感慨“我壮年执笔,历时7载,为它牺牲了一切,通宵不寝的情况,记忆犹新”;“披肝沥胆,前后凡二十有二年”;“我回想20多年的曲折遭遇,真不禁捧书泣下!
”有关回忆录缘起、撰着经过和出版周折,唐氏1980年7月28日作竣的长文《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详述缕析,读后令人同情之心、理解之情并生。
不过,早前唐德刚的撰稿者身份被排除在外,并非哪一人之过失。回忆录中文稿系1979年夏,由李宗仁长子李幼邻伺奉生母李秀文从纽约返居桂林时,赠予广西政协而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得以“内部发行”。按唐德刚在上文中的说法,“该会显然不知此稿的来龙去脉—因为幼邻本人亦不知道—他们并未征询我这位‘著作人’的意见,便径自出版了。
”故此,他花了不少篇幅特意解释著述权及版权之所属,说明当年经过哥大提议和李氏同意,署名用“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稿”。
1980年11月,《李宗仁回忆录》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1988年,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1986年和1988年,香港和台北相继出版此书。此外,市面上还有几种盗版本。这些后来印行的版本,均确认该书乃口述历史之作,而撰稿者可与口述者分享著作权。
前些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唐德刚作品集”,则将其所撰的口述历史著述都作为个人作品收入,自然也包括这部广为人知的回忆录。如此一来,“分享”似成“独占”,个中分野自非我等局外人所能置喙。
有趣的是,依照唐德刚那篇“沧桑”之文所言,国人读到的回忆录中文版,原本是个“私生子”,因当初哥大口述历史学部保存当代史料所需者为英文稿,而将李宗仁口述整理成中文稿,是唐氏“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一点‘额外工作’”。
程序上,英文稿反而是在中文稿增删、改写的基础上迻译而成,凡五十三章、四十多万字,正是唐德刚呕心沥血首先定稿交差的,而中文稿因属“私生”,且有缺漏之处,还需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补正、修改及润饰,所以他对广西政协在其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内部发行”李幼邻赠予的书稿颇有微辞,亦属情理之中的反应。
其实早在广西政协“内部发行”之前,这部回忆录从1977年4月起,于香港《明报月刊》连载了两年,后曾一度中断,至1980年恢复连载。但其成稿延宕过久的发表及出版,却引发了某些疑问或误解。
在去年7月下旬于香港举行的中华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位本地文史研究者对该书提出严厉的批评,称其上半部是抄袭五、六十年代在《春秋》杂志连载的黄旭初回忆录,下半部则几乎没有一句真话。
这两句指控很严重,但唐德刚在前述长文中说过,这部回忆录誊清的中文稿一式两份,哥大存正本,李氏留副本,并在六十年代寄给定居香港的老部下黄旭初征询意见,“黄氏乃将李宗仁的回忆录大加采用,改头换面地写入他自己的回忆录里去。因此笔者在李稿中的许多笔误和未及改正的小错误,也被黄旭初先生误用了。”
李幼邻携回并赠予广西政协的书稿,正是黄氏多年后归还的那个副本。对于李稿与黄稿究竟谁抄袭谁,唐德刚这番说辞尚称清晰合理,当可澄清疑问。至于下半部是否“几乎没有一句真话”,若无浩繁的证伪工作是不能轻易定论的,这需要对大量史实爬梳剔抉、钩沉索隐,已不在本文谈论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