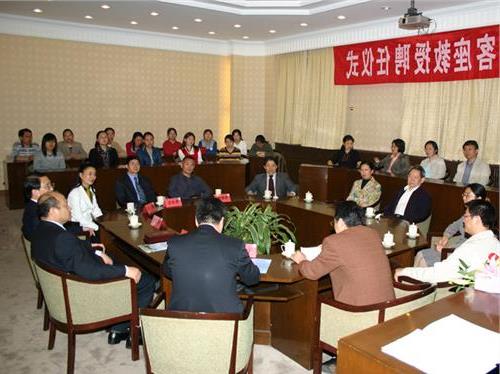金雁教授 金雁:对曹维安教授质疑一事的公开答复
2013年10月26日,学者金雁在网络发布了"对曹维安教授质疑一事的公开答复"一文,以答复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曹维安对她的"抄袭"质疑。此前,曹维安在网上发文《是所见略同,还是公然抄袭?——与金雁同志商榷》,称金雁使用了他硕士论文中的大量文字,30处、共1万多字雷同,"除个别地方外,大多没有做注释和说明"。
曹维安所说的"大多没有注释和说明",金雁在"公开答复"一文中做了特别说明,她认为引发质疑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存在"文献引用疏失"。
在文中,金雁为"早年的疏失给曹教授带来的不便表示诚挚的道歉"。除了"引用疏失",她认为对曹维安论文的引用"是完全合法合规的行为,也是学界的通行做法",并表示"说本书是一本抄袭之作这是无稽之谈","若曹教授认为我的道歉仍有不妥之处,那么请提交到有关学术鉴定部门,付之公论"。
以下为金雁公开答复全文。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金雁,也是《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的第一作者。日前,我偶然得知一篇由曹维安教授撰写的网文《是所见略同,还是公然抄袭?——与金雁同志商榷》在部分网站小范围传播。
文中称我的那本书"公然抄袭"了他的硕士论文,还就我和他的交往讲了许多话。看到此文,作为曹教授的同门和多年的学友,诧异之余更感到痛心。鉴于此事确实引起了各方的诸多关注和误解,在此我想就本件事情的始末做出应有的澄清,还事件以本来面貌。同时也检讨我个人确实存在的过失,请大家以后也引以为戒,并向曹教授本人做出应有的道歉。
一、关于《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文献引用疏失的说明和道歉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是我早年多项研究的结晶。1978年我进兰州大学成为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次年开始撰写硕士论文《1812年战争中的俄国农民与农民运动》时,就产生了对"村社"问题的兴趣,并在该文中有所涉及。
毕业工作不久,1982年我应导师李建教授(后来也是曹维安的导师)之邀参加两卷本《俄国通史简编》写作,撰写"基辅罗斯封建割据"一章时,就觉得对村社问题要重新认识并形成了一些初步想法。1985年起我给学生和硕士生讲授俄国史的过程也加深了我对该领域的思考。
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俄罗斯传统文化与斯大林模式》时期,我陆续在相关领域发表了大量论文[1]和译文,其中一篇于1989年获中国苏联东欧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就是在这些研究基础上,作为上述基金课题而撰写的。但写到十月革命前,字数已达25万,后半段与斯大林模式相关话题还需费时日。于是决定就此截断,到1989年初形成《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的初稿,当时已纳入一套丛书,但不久因不可抗原因丛书夭折。由于1990年我出国后开始做转轨经济比较研究,使该书一直拖到1996年才经过增补在中央编译局出版社出版。
曹维安教授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77级本科毕业生,毕业后希望通过考研重返高校。1982年经人介绍他到访寒舍,向我咨询考研和我了解的学科研究情况,后来他正是报考我出身的兰州大学历史系苏联史方向。也因此,虽然曹教授年长于我,但因为是晚5届的同门,所以我反而是他的师姐,他在定硕士论文方向时也曾找我商讨,当时我便建议他写农村公社这个题目。
1986年曹教授研究生毕业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我们就又从同门变成同事。我与曹教授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即使1994年我调北京后,苏联史圈内的学术活动我们也多次见面交流。后来我成为学会秘书长,他成为常务理事。
1986年曹教授到系工作不久就送了我一本他的硕士论文——《俄国农村公社初探》。文中率先引用和翻译了许多俄文材料,尤其是早期这一段做得比较细致,可以印证我当时关于农村公社的一些认识和观点,为我的研究提供一定的论据补充,所以我当时非常高兴。
应当说,关注农村公社并形成系列观点我比他早,只是当时大都停留在笔记、讲义和交谈上,尽管研究生时代我也是搞"封建时期与近代早期"的,但由于工作后研究室安排我搞苏联初期农民问题,没能像他那样专注于传统村社并作为学位论文来写。在撰写《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时,我确实从曹教授这篇硕士论文获益,为此也很感谢他。
由于《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写作跨度前后达十余年,不仅篇幅有32万字,注释也近700处,再加上在20世纪80~90年代文献资料的引用规范标准远不如今天明细和严格,我在文献引用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疏失。曹教授称本书分"30处""用了(他的论文)约1万余字",因为近期时间有限,我没有查算也未能细考,这里姑且先接受曹教授的说法,也待我做进一步细查。
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初探》曹教授本人的论述5处引用,我均作了明确的注释,见《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的65~66页注15、16;89页注10;127页注43;176页注36。
在书后的征引文献目录中,我也明确列出了曹教授的《俄国农村公社初探》硕士论文。但对曹教授引用的一些文献,我的确有未注转引而直接加以引用的做法,这是非常错误的。
正是我当时的疏失,导致了今天后果。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曹教授当时的研究为支持我的观点提供了事例支持,并为我早年的疏失给曹教授带来的不便表示诚挚的道歉。但也必须指出,《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是我自己十多年研究提炼出的精华,思想的原创和对俄国农村公社的长时段观察我是下了大功夫的,引用曹教授的《俄国农村公社初探》只是为本书提供更精彩的实例,虽然转引作直引是错误的,但即使按曹教授自己提供的数据所言,涉及他论文的引证部分全加起来也绝不超过4%,说本书是一本抄袭之作这是无稽之谈。
如果哪位朋友对此事真感兴趣,大可将二者找来对比阅读。若曹教授认为我的道歉仍有不妥之处,那么请提交有关学术鉴定部门,付之公论。
二、对曹教授其他质疑的回应以及部分事实的说明
在曹教授的网文《是所见略同,还是公然抄袭?——与金雁同志商榷》中,他连续发出三个质问:"既然是我未发表的论文,为什么(引用)事前不征求我的同意?!何况,书中许多用我的论文之处既无注释也不加说明,这算是金雁你的还是我的?再者,我已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何不用(即上述我的第一篇和第二篇论文),偏要用我未发表的硕士论文,目的何在?"对于这三个质问,第二个质问确实是我的疏失对他造成了不便,我在前面已经说明,在此我再次进行道歉。
但是,其它两点质问有必要正面回应。
第一个质问说"既然是我未发表的论文,为什么(引用)事前不征求我的同意?!"。如果是未经答辩的论文稿本,确实未经作者同意别人不能引用。但"未发表的"准确意思是未正式以专著形式出版。而学位论文(除涉及机密的例外)无论是否交付出版,只要通过答辩归档,在规程上就已经公之于众,成为公共学术资源可供查阅和出注引用,而无需一一经作者同意,这在国内外都是学界通则。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现在很多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知网》等数据库都把已通过答辩的博士、硕士论文电子化为资源,以供检索、查阅和引用,使这种情况更为普遍,这些论文以专著来衡量都是"未发表(正式出版)的",但在操作规程上都属于合法的文献来源。
没有哪个研究者会向合法文献来源的原作者一一去说明自己的引用情况。
20世纪80年代的硕士论文虽然今天还没有全部电子化,但在查阅和引用的规程上是完全一样的,没有特殊性。如今多数高校规定在提供答辩的学位论文前页必须附有"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书",就是在资源共享的原则下从法律上规范这一点。所以,在这点上我对曹教授硕士论文的引用是完全合法合规的行为,也是学界的通行做法。
第三个质问说,"再者,我已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何不用(即上述我的第一篇和第二篇论文),偏要用我未发表的硕士论文,目的何在?"这个原因有几个:第一点,我的书初稿1989年以前就完成了,而此时正如曹教授自己所言,他关于本研究的论文大部分还没有发表,他在网文中所称的其余4篇文章都是1991以后的事(而1991年的前后几年也正是我出国转向转轨经济比较研究的时期,那时的信息网络技术远没有现代发达,我当时一度离开这一领域,不可能专门追踪他的论文),特别是有3篇是本书出版后才发表的。
所以即使作为引用材料,主体内容上也只可能引用他的硕士论文。第二点,他在1987年的两篇论文,基本由学位论文分割摘录而成,我自然就应当引用更加完整的硕士论文。
特别是要指出一点,我早年和曹教授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学术交流,《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这本书在出版后我第一时间就送到他的手上,如果他对其引用不当有所不满,早就可以指出,下面将就此事详细说明。
1996年,《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拖沓多年后终于出版。作为同门和学友,我第一时间便将该书送与曹教授,请他提些意见并写个书评。在《是所见略同,还是公然抄袭?——与金雁同志商榷》中他称1996年收到我送他的书后就对我的"抄袭""十分气愤!
"并且对我请他评点此书根本就"无意搭理",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事实是,当时他收到我的书后,给我写了一封回信。信中都是客气话,完全没有对书中的不恰当引用表示过任何异议。
信中回复不搞这一行写不了书评了(他当时曾一度下海)。而1996年那本书初印只有1000册,后来几年中才加印了5次,直到2012年再版,现在大概总有上万册在流传了。因此,他在第一时间拿到书后若真的对我的"抄袭""十分气愤!
",那么那时完全可以在回信中对我指出毛病,当时它不仅不会危害我们的密切学术交流,纠正起来也很容易,他只要在信中指出问题,加印时就可以改正,在序中说明前印之失也无任何难度。
事实是,1996年后的17年间,至少就我的感觉,我们一直保持着双方信任,曹教授本人也始终从未就此事与我有过异议。2002年曹教授自己的著作《俄国史新论》出版后也是第一时间题款送我。在这本书中,把他现在说是一见到就"十分气愤"的"抄袭"之作,即我1996年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列入参考书目,并在正文中多次引证。
实际上,从最初一直到最近他发怒前,我完全没有察觉他的不满,以致我听到风言,感到惊讶,要找他谈此事时,秦晖提醒说这些说法可能就是曹本人的意思,我还自信地说不会,相交30多年了我应该了解他,他要有想法早对我说了。
长期以来我们关系不错,一直保持学术交往,可能也是因为接触太久,我反而未能真正理解曹教授所思所想。具体在农村公社这个学术问题上,我过去有些错觉,觉得我在思想和观点上对他有影响,他对我则在资料和论证上有帮助。
尽管有前述疏失,但如果我存心抄袭又怕别人"抓住证据",就不会第一时间送他拙著,还请他写书评。哪有偷了人的东西又当时就向失主呈上"赃物"的,世间的抄袭必然都要回避被抄袭者。而我与曹教授认识30多年,从他读研究生前的接触,到后来同门师姐弟、同系共事、同行同方向又同在一个学术小圈子,学术上我们彼此几乎是完全透明的。我并不是他的上级或者对他有控制力的什么人,除非傻了疯了,否则怎么敢存心抄袭他。
三、关于曹教授17年后突然散播网文的缘由
17年来,曹教授从未向我提及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对他论文引用有过失一事,随着时间流逝我对这本早年专著撰写细节渐渐淡忘,也正是因为我未能对本书反复严格把关,导致这个问题持续至今,这确实是我的过错。
但是什么导致17年后曹教授突然发播网文《是所见略同,还是公然抄袭?——与金雁同志商榷》,我虽然仍觉得曹教授近期的行为有些令人费解,但能想到的一些事由可能是本次事件的导火索。
曹教授在今年国庆后的两次电话中开始指责我以"名人"自居不把他放在眼里,令他不满已久(该电话前这30年中我始终不知他有这种想法),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我们之间出现了隔阂。他两次提到的一件事是去年在内蒙古开会见面时,我曾托他把我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带回西安送给杨存堂老师,当时竟然没有给他送一本,经他电话一提我才觉得这事的确实有些欠妥。
只是那时我手头只有极少样书,所以想着先送长辈老师,当时我的确应该讲明并在事后补寄一本给他,只是我那时仍以为我们关系不错,所以未曾想这小小的失礼举动竟招致曹教授不满。在这里,我也对当时的失礼行为表示歉意。
另一件事即2013年9月29日我望其帮助澄清一事,当时我听到了一些风言称我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存在抄袭,所以找他当面求证。或许是因为我在不恰当地点且没有回避以前学生的情况下,向他询问了一些可能会让外人产生误解的问题,伤了他面子。
但即便在这两件事以后他来电话时,在沟通过程中我仍然认为我们的关系不至于脆弱如此。当时可能是说了些言不达意或不恰当的话,导致误解增大。在电话中我向他明确说明,关于这件事我会与他进一步沟通。
但恰巧,10月间我因工作需要去俄罗斯一段时间,导致沟通不畅对此我负有一些责任。可在我回国之后,才通过学生突然得知曹教授在网上传播《是所见略同,还是公然抄袭?——与金雁同志商榷》一文,指我抄袭,这确实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不过也是事出有因,我可以以公开的方式予以说明、道歉和澄清。
对于本次事件,我17年前在著书时文献引用疏失,确实是我的错,在此我向曹教授表示真诚的抱歉。既然出现这样的争议,我很快将就《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进行重新修改,纠正这些错误。对于我自己而言,不重视文献引用规范性的问题确实要敲响警钟,以后我一定改正。作为一个教训,我也希望大家以我的过失为戒,在以后的治学中更加重视文献引用的规范性问题,特别是同门内的学术交流也要时刻注意,避免犯错。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谢谢。
金雁
2013年10月26日
[1](《农村公社与十月革命》(《苏联历史问题》1987年第3期);《俄罗斯传统文化与斯大林模式》(《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冲突》(《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对苏联史逻辑体系的重新思考》(《苏联历史问题》1988年第2期);《苏联农村阶级划分的统计学分析》(《史林》1988年第1期);《恰亚诺夫与当代西方农民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4期);《斯托雷平改革与列宁思想的转变》(《苏联历史问题》1990年第3-4期);《村社制度、俄国传统与十月革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