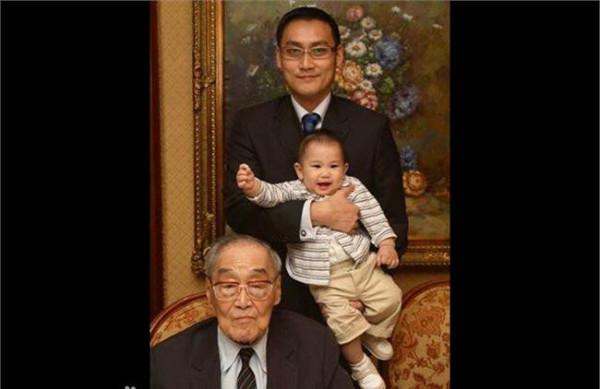费穆孔夫子 费穆版本《孔夫子》:作为神话来阅读(图)
电影由孔子的故乡鲁国被入侵,君王迂腐,贼人当道开始,心怀天下的孔子教导弟子六艺及大丈夫立身之本,在救国不成后,孔夫子开始周游列国,电影以手绘地图交代局势转变,最后,73岁的孔子回到满目疮痍的家乡,身边惟有孙儿相伴。
1938年,费穆、民华电影公司的掌门人金信民以及演员张翼因战事被困香港期间,产生了拍摄《孔夫子》的想法,最终于1940年在上海完成。对于影片的主题,费穆曾自言:“孔子只有道,没有术……自己是一个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却做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的牺牲。”扮演孔子的唐槐秋早年在法国学习航空机械,后受朋友欧阳予倩、田汉等影响,投身话剧表演。
主演:
孔子 —— 唐槐秋
子路 —— 张翼
颜回 —— 司马英才
子贡 —— 裴冲
南子 —— 慕容婉儿
孔夫子是一项神秘的事业。伟大的人需要一种符号,力量过强的人通常会被排除于凡人心理学之外,引入神圣的符号,而符号的操纵,无法不最终握在后来者手里。这些后来者可能首先便是他的徒儿,更多的情况是那些自称“私淑”,能遥契、密应的人。孔夫子不得不成为神话,同时是他们(经营)的事业。
把圣人“人化”的电影?
那么,《孔夫子》是一部怎么样的电影呢?曾出版《诗人导演:费穆》(香港电影评论学会1998年出版)的电影资料馆研究主任黄爱玲表示,那是一部把圣人“人化”的电影。今天,大家都喜欢把英雄、贤人往下拉,展示他们凡人的一面。
当然,英雄、贤人也是人,他们不是神,但所谓展示他们凡人的一面,其实是要表示他们也有失败倒霉的境遇,也有软弱的时候,从这“人化”的向度,可加强人物的可亲和度,亦可相对加强读者或观众的投入感。
然而,《孔夫子》真是这么一部电影吗?像李零教授在《丧家犬》和《去圣乃得真孔子》那样,还孔丘一个历史的“真容”吗?熟悉符号学的我们早明白与其汲汲于考论真伪,不如研究对象为何及如何值得如此“真”。“人化”代表一些人面对孔子这个符号(真实具体的那个人于两千多年前消逝之后,无可避免只留下关于他的符号,意义因不同年代、不同社会、不同人而设下了不同符码/code而异)时拥有的意愿。
作为独立的观众和文本解读者,我们未必(能)呼应相同的意愿。
费穆镜头下的孔子道貌岸然,一脸正气,影片甫开始他便站在高山上,分别向亦恭亦敬的子路、颜回、子贡训示教义。初版这段声音失去了(有待修复),愈发表现出抽空的超人意味。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中分析爱因斯坦的大脑时说得好:“众所周知,科幻小说里的超人,本身都有一点具体化的东西。”爱因斯坦需要他的大脑展示他的超人天才,孔夫子需要的则是木讷肃穆的面容。
细心去看《孔夫子》的观众,如果真的努力去发掘他的“人”味,结果可能是挺尴尬的——你当然不能说电影里的老头不是人,但瞧他一脸正气,由头至尾其实颇为僵化地把那些儒家精神,像口号般向徒儿们宣示,也不准备解说,似乎只期待他们以宗教的态度信奉。
有人认为儒家是道德宗教,但称得上以道德为教,即超越的加持大抵须由内在的体验落实。也许正因为此,电影有一幕由孔子向弟子宣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时,读中国书的人都不由瞠目结舌起来。出于《礼记》的大学篇教义,怎会出于孔子之口呢?较重视超越面和“天道”的《大学》、《中庸》思想不是后儒所长吗?这绝对可以视为某种“附会”的做法,表现了费穆哪种心思呢?
诞生于“孤岛”上海的《孔夫子》
《孔夫子》摄于1940年“孤岛”时期的上海,围城氛围弥漫一切,危机、颓废、焦虑、无奈……夹杂一气,前景悲观的大有人在,对国家失去信心的比比皆是。一向代表中国传统光辉的儒家和圣人理想有望在意识形态上提供某种出路,搭起一道让心灵得以凭依、寄托的桥梁。
然而,电影的诞生也距离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未远,之后还会有“儒法斗争”、“批林批孔”的意识形态斗争运动,儒家的形象远非一边倒的正面,《孔夫子》走的,虽未算是险路,也是一条栈道吧。
楚汉相争,刘邦受封汉中王,自断栈道而示无逐鹿中原之意,后来要出兵了,又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费穆拍《孔夫子》,有没有相似的设计?
回到罗兰·巴特论爱因斯坦大脑,他提及当年有人安排爱因斯坦躺下,电线缠头,记录他的脑电波,然后被要求:“请你想着相对论”。“想着”相对论,多么奇怪而又庸俗的要求……怎样才算想着呢?当爱因斯坦想着相对论,脑电波可会呈现相应的变化?要求的人大抵这样想,如此便能展示伟大的人物——用可记录的伟大的大脑(活动);透过可被观察,可化为一条条曲线的脑电波?
孔子的伟大必须被展示,神话的重点在于,要有一个具体的、可见的(尤其放到电影上,这更是不证自明的吧)东西,如果那便是孔子,不,演员唐槐秋的脸容、他几近僵化的宣示,难道我们便凭之推断费穆是要树立一尊神像,好让彷徨的国民有路可依,团结抗日?
不甘心把费穆如此庸俗化的观众情愿走另一条路吧。把宗教的一面提上来,叫唐槐秋如此演绎孔子,让孔子说出不尽符《论语》思想的话,可会像刘邦那条明修的栈道?假设黄爱玲他们是对的,他们经过种种研究,发掘文献,了解费穆当时的意向,他一方面想将孔子“人化”,另一方面却在影像上选择吊诡的演绎。换言之,是通过建立一种神话来“人化”孔子,栈道是道德宗教的面纱,暗渡的是真实的人、人性以及生活的感染?
以“人性”铺陈的“神性”
《孔夫子》表面上最为“人化”的一段也许便是讲到他困于陈国与蔡国间还弦歌不断的故事吧,偏偏初版可能为了加快叙事节奏,剪去了部分段落,在未回复“原貌”之前,我们看到的是很有限的“从容不迫”。孔子众弟子的表演,尤其是张翼饰演的子路,比老师更为抢镜,体现了智、仁、勇的三元价值,在危机逼近时,勇者难免容易突出。
不过,费穆该明白,仁既是跟智与勇并排的德,更是三者的基础。作为终极仁者的符号内涵,孔子该展示的是无坚不摧的毅力(仁毅),把子路的勇毅比下去。
现在仁毅不彰,勇毅反显,与其说是费穆失手,不如说是他的灵巧。微妙之处正在于:在那条僵化的、宗教的“栈道”上,圣人的终极仁毅也变成被膜拜的神像姿态,子路的勇毅,相形之下,反而显得人情味十足,令观者动容。
明乎此,我们对于费穆如此用力刻画片末子路单枪匹马杀上高楼慷慨就义的情节,不免有豁然贯通之感。兵临城下,国难当前,子路经过老师的教化、感召,杀身成仁。神像被建立然后自行瓦解,孔子的“人性”须透过经他教导的子路才得到真实的铺展。
那唐槐秋的木讷、肃穆、正气,僵硬的宗教表象,反过来衬托了弟子的可歌可泣。神性,同时作为人性的对立面和基础,终于没有带来负面的效果。不错,那神像看来有点孤高乏味,但令我们感动的人性表现,却以它为基石,思索片刻便乐于接受。
初版未收入的片段还包括用字幕交代的齐兵屠杀鲁平民及鲁国反攻的“复仇”情节,这一段有明显,甚至过于明显的宣传抗日的意味。另外,颜回自己没饭吃却把刚讨回的一碗饭给了叫花子,大抵是表现颜回之“仁”及其安贫乐道的一面。窃以为,这段剪掉反倒好,神话的正、反两面完全可交由孔子和子路去完成,支线有时可丰富主调,但有时也会扰乱了旋律,颜回、子贡相对于子路,在主符码的运作下似乎应该简单一点。
作为神话(现代符号学意义的神话)阅读的《孔夫子》,它的层面既复杂又简单。复杂,是因为孔子和子路、师与徒、超越与人世、宗教与人性之间既对立又互倚,包含着明暗转化,内里翻上的微妙巧手;简单,是只要能一眼看穿,抓住主线,观众便可一追到底,丝毫不乱,完成见证《孔夫子》把孔子“人化”的曲折旅程。(作者为香港著名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