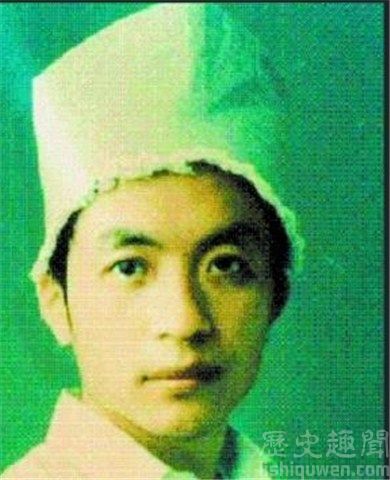顾桃纪录片 顾桃:将纪录片拍摄到底
在过去的十年间,顾桃的生活完全沉寂在自己的纪录片里。用一句话形容他再恰当不过了——“顾桃不是在拍摄纪录片,就是在拍摄纪录片的路上”。三年前,顾桃用了七年的时间记录了鄂温克族的三代人,剪辑完成了三部成片。现在,他将摄影机聚焦在游牧的蒙古族人身上。
在进行了三年的跟拍之后,顾桃计划在九月开始剪辑,片名已经想好了叫做《乌珠穆沁的萨满》,关注的仍然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在当今社会的一种生存状态。这不得不让人们联想到他有关鄂温克族人的纪录片系列。
这多多少少是受到父亲顾德清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顾德清去了额尔古纳左旗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从此引发了想接近族人生活的愿望。在之后四年的时间里,无论严夏或是寒冬,顾德清长途跋涉于原始森林,多次与猎民一起进山,遍拍鄂伦春族服饰、桦皮盒图案、狩猎生活风俗、地貌……后又扩大到对敖鲁古雅饲养鹿鄂温克人的生活考察及摄影。
顾德清每次从山里回来就会立马开始冲洗拍摄的胶卷。十多岁的顾桃就在一旁看着父亲,有时也帮助父亲完成后续工作。当顾桃看到父亲用胶片相机和文字所记录下的鄂温克一家人的生活时,他感到特别好奇,但当时只是觉得他们的生活与自己不一样。
已上初中的顾桃帮父亲最多的就是重新誊写父亲在山里用笔记录的鄂温克族人的生活片段和故事。内容包括了父亲在森林里的故事、鄂温克人们的狩猎场景、猎获的动物、迁徙的状态、房子的建造以及对生活的态度。这些生动的笔记就是顾桃童年时最爱的读物,也让他渐渐熟悉了父亲记录的那个民族。
显然,年轻的顾桃并没有因此特别崇拜自己的父亲,也没有想过要去走父亲那条路。他只是按照传统的教育轨迹,在18岁那年考上了大学。可是,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巨大差距,顾桃在大学毕业后并没有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他决定去做一名北漂。为了生存,顾桃在杂志社做了一名摄影记者,跑了很多地方,拍了很多照片,但那仍然不是顾桃喜欢做的工作。唯一让他欣慰的是在秦皇岛的拍摄经历。当时正值冬季,渔船很沉寂地停泊在码头上,波涛拍打着它们,这种感觉既失落,又充满忧伤。
他忽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此后整整两年时间,他都在拍 “船”。只要有了一点钱,他就坐车去秦皇岛,疯狂地想把他认为有历史感的内容记录在底片上。他形容那十年是“挺痛苦、无奈、茫然的十年,当时没有任何的态度和想法,很苦闷。”
2002年是顾桃从大学毕业的第十个年头,那年冬天他回到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由于多年在森林里拍摄,父亲得了严重的类风湿,已经无法正常行走了。顾桃决心替父亲去敖鲁古雅走一趟,帮父亲把老朋友的照片拍回来。
大年初二,顾桃出发了,此行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临行前,父亲给顾桃写了几个朋友的名字,当他辗转到了敖鲁古雅时,才发现这些人都已经不在世了。生命的脆弱让他十分难过,他走访了两个猎民点,认识了使鹿鄂温克人的标志性人物玛利亚·索的儿子何协。大家对顾桃的到来也很高兴,给他讲了很多故事。
2003年,政府出台了新的政策——“生态移民”。政府建成的定居点位于根河市三车间,也就是新敖鲁古雅乡。那时有五十多户人家,红颜色的屋顶、白色的外墙、黑色的铁栏杆,在湛蓝的天空下很耀眼。这一幢幢政府免费的定居点,让后面原住居民很是羡慕,但对于曾经以森林为家的他们,这里确实是显得拘束了。
当人和鹿都被迁到城市边缘的定居点居住时,顾桃发现这个民族有一种悲壮的美,他们很幽默地说话,很乐观地生活,但是内心却很苦闷。或许这一点与自己有点共鸣。
2005年年初,顾桃找来了一个家用摄像机,带着它上山去了。于是就有了我们后来看到的鄂温克三部曲——《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和《犴达罕》。
这三部片子里记录了鄂温克族的三代人,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敖鲁古雅敖鲁古雅》关注的是北方少数民族在当下的生存状态,他们用最原始的生活方式,演绎一个民族的传统,也哭诉着敖鲁古雅文化消逝的悲哀。影片里出场的柳霞成了第二部片子里的主角。
《雨果的假期》讲的是个人命运。柳霞在雨果很小的时候失去了丈夫,因为酗酒,无力抚养孩子,在社会的资助下将雨果送到了无锡免费接受教育。柳霞终日苦闷,驯鹿和酒成了她思念孩子的寄托。在一个冬天的假期,雨果回到了家乡——大兴安岭深处的鄂温克定居点。此时他已不再是当初离家的那个孩子,而是一个13岁的少年了。面对酗酒的妈妈、诗意的舅舅、纯净的族人、熟悉又陌生的森林,在城市里长大的雨果有些不知所措。
而《犴达罕》则不仅仅记录了一个有着奇特艺术天赋的鄂温克人维加的生命片段,也有着对民族、信仰、文明、政治的反思。维加就是第二部片子主角雨果的舅舅,他是柳霞的弟弟,一个酗酒的部落猎人兼诗人。
“生态移民”政策执行之后,放下了猎枪的族人被迁到山下有很多不适应,无奈地接受着现代化生活的到来。下山的猎民们在不适应圈养的驯鹿大量死亡后,又回到山上居住了。三代人生活方式发生着彻底的改变,顾桃就是从那个时间开始记录的。
当然,也有例外,玛利亚·索就直接选择留山里。何协家住在山下根河三车间16号,他经常是山上山下地跑。山上有妈妈玛利亚·索,山下有老婆卓耶。禁猎后,何协放下了猎枪,拿起了铁锯,负责每年的锯茸工作,锯下的鹿茸经乡里统一加工卖的钱再按比例分给猎民。
禁猎前,何协也是好猎手,就像他父亲拉吉米一样经常能让玛利亚·索吃到野味,所以玛利亚·索说,过去她的血是热的。枪被没收了之后,玛利亚·索很困惑。“过去,日本人给我们发枪,苏联也给我们枪,新中国成立了,毛主席也给我们发枪……想到我们鄂温克人没有枪,也没有了放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梦都在哭。”
顾桃回忆着何协一家的生活状态:“早晨八点的何协家,妻子卓耶经常和妈妈看着窗外的路,每日、每月、每年,春天的雨、夏日的光、秋季的风和冬日的雪。窗外的路永远一样,一点也不新鲜,但看见了路就像是看见了有空气的世界,尽管路是水泥的,但空气总是新鲜的吧。
卓耶在床上的时间多,而床就在窗边,她左面的胳膊和右面的腿依然麻木。十年前在老敖乡,何协和朋友在‘客厅’里擦枪,枪走火了,子弹穿过了薄薄的胶合板,射进了卓耶的脑袋,直至今天还无法取出。
卓耶就在床上十年,越坐越胖,像一口沉重的钟,何协就叫她‘胖子’,并依然爱着他的‘胖子’,这种爱里并不包括他曾经的和现在的内疚。卓耶在窗外的路上,要是看到何协从山里下来,那是她最高兴的时候了。”
渐渐地,偷猎和乱砍乱伐把整个森林给破坏了。在纪录片里,玛利亚·索诉说着自己的梦想:“我们是个弱小的边境民族,是靠打猎过来的,祖祖辈辈生活在大森林里,守着山林,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有猎枪,是中国唯一养驯鹿的民族,跟别的民族不一样,我们应该保护自己民族的东西。我们跟大自然非常亲近,过着自己的生活,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钱,大自然里什么都有。”
顾桃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总会关注这样的一群少数族裔,就是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顾桃在博客里记录着:“2011年,兴安岭的初雪虽然停了,但天还是阴冷的。玛利亚·索搓着手上的面,看着外面阴沉的云,没有表情,她已不需要任何表情,面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叫‘强纳’的小鸟好像也不再来了,不再飞到玛利亚·索的手里觅食。据说今年采树塔和都柿的人比往年的都多。整个秋天摩托嗡鸣,汽车马达的嘶吼,载着丰收的林场工人欢呼而去。
留下的是各种咸菜袋,食品袋满山遍野。维佳今年从海南回来探亲时说过,山川哭了,森林哭了,河流哭了,当然他也哭了。事实上,昨天下午的拍摄,我认为是这六年来最重要的一次。玛利亚·索终于能面对我的摄像机,在二姐德克莎陪伴下,缓慢地讲述自己快近一个世纪的森林生活,只有机器的电流声,面对她的我不忍看到的眼神,这个世界变得宁静了。”
渐渐地顾桃发现,他对朋友发表的旅游微博里浪漫的美景和馋人的美食没有了太大的兴趣,而是越来越爱上了山里凄美的一切。“当别人去到呼伦贝尔草原,他们看到的是蓝天、白云、辽阔的大草原和异族风情,而我看到的却是一种沉重和忧伤,当然也有片中主人公的小幽默和豁达的心境,我自然地沉静在这个状态里。对我来说,做纪录片就像一场没有归程的旅行。”
因此,顾桃把过去的十年时间全部奉献给了纪录片。2011年,《雨果的假期》获得了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的最高奖——小川绅介奖。面对他人的质疑,顾桃认为每个人都是通过观点、角度和态度看待这个世界和周遭的环境,包括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从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视角。
“让我把它呈现地更美好,我也做不到”。我不需要把事实解说地多美好。“就像当年父亲用胶片来展现鄂温克族一样,我认为用影像记录更客观、更直接。”
在拍摄纪录片的路上,45岁的顾桃马上要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他希望等到孩子3、4岁能走路时,带着孩子继续自己的拍摄之路。
顾桃
有着满族血统的顾桃是条真正的草原汉子。在离开家乡很多年以后,顾桃依然要回到那个地方去寻找值得投入一生去做的事情,那就是用影像的方式将那些正在消失的民族文化定格。2013年,他凭借《犴达罕》获得了第二届凤凰视频纪录片大奖最佳纪录长片奖。2014年,此片荣获了第38届香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