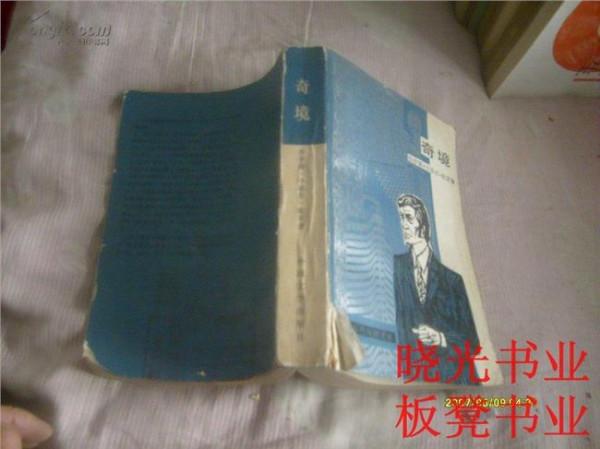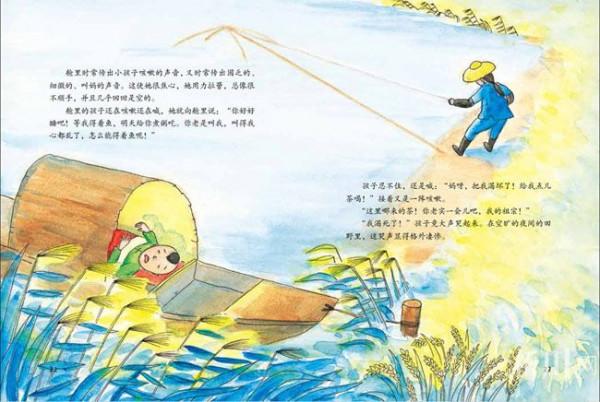发现作家任晓雯从内心写作到当下写作的站位
任晓雯是近年来较引人注目的年轻作家。她创作与理论兼长,始终保持低调、严谨的品质,是当下为数不多的进行严肃文学创作的年轻作家之一。
在阅读任晓雯的小说的时候,我努力去发现作为小说家的她站在哪里?从内心写作到当下写作,她的作品都带着超拔的写作梦想。于是,我们知道,最优美的意义总是在这个世界上最低的地方,最超拔的审美来自最具体的细节。
在阅读任晓雯的中短篇小说集的时候,我首先摆出来的姿态,就是推开那些扑面而来的主题或者意义,推开人物漂浮在文字里的性格与命运,努力去发现小说家站在哪里。这样的问题很重要,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个细节的某个局部,某个细节,每个人都以自己为出发点打量世界。如果我们首先假设这个世界是一种整全的智慧,那么小说家写出来的人和事件,以及与人和事件有关的世界,就是一个细节性的碎片。
我前所未有地避开小说呈现出来的思想或者观念,不是认为这些小说里的观念不重要,事实上它们太重要了,只是我选择了回避,选择了一种技术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路径,因为我相信,当任晓雯的小说出现在我面前,一切的理念都已经隐含在小说的形式里,这是一个辐射面非常开阔的理念,别人看到的是光荣,我看到的是罪恶,别人感受到的是幽暗,我却能发现爱。
没有谁对,没有谁错。那么,就避开观念,去体验技术吧。因为任何意义上的技术,或许都是可以量化的,是可以分析的。
关于任晓雯的小说,首先给我冲击的,是她年轻的作品《阳间》。说年轻,是因为她写这篇作品的时候,才22岁。这的确让我惊讶,小说的结构,有一种后现代的均衡感,而在想象力的维度上,却又沿袭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荒诞。
至于语言的节制能力,具有古典小说意味的缓慢的叙事方式,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作者的年龄,我相信读者都会认为,这是一篇有叙事经验的小说。唯一不足的,是小说里隐含的观念,某种形而上的因果报应,道德意义上的审判,一切都在作者的想象中完成。这是中国传统小说老旧的意义,无力建构一个道德理想国,因此靠人的写作的力量,靠小说家一个人的道德谴责,来营造乌托邦之乡。
我的批评就是从这里开始。我的问题是,在这篇小说里,哪里才是任晓雯的位置。后来我仔细分析,认定这是一篇与内心的工地有关的小说,小说家任晓雯站在自己的内心里。但是内心的工地构筑在哪里,或者说谁来引领小说家的内心,这都是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由此,在这篇小说里,任晓雯与人物,内心的迷茫与生活的迷茫,全部纠缠在一起。罪恶与灰尘比生活更丰富,生活比小说更丰富。读这样的小说,你除了期待一种乌有的因果报应,剩下的全部是绝望。一篇生动的小说,一开始埋葬了作者,接着埋葬了所有与这篇小说偶遇的人。
然后,我的阅读重点来到了任晓雯的另一篇作品《乐鹏程二三事》。乐鹏程这个人在任晓雯营造的小说世界里,是一个非常具有当下意义的形象。事实上,任晓雯的长篇小说《她们》,其叙述逻辑与技术理念,和《乐鹏程二三事》一致,即一种传统叙事技术下的当下意义。
对于一名年轻的小说家而言,一种诚实的、写实的、深度切入细节的、看上去似乎去掉了所有后现代先锋技术的写作方法,其实存在着极为艰难的技术门槛。因为这样的写法,需要心灵和诚实,需要一种与年轻的文笔完全不相符合的克制的叙事技术。
但任晓雯似乎做到了,《乐鹏程二三事》或者《她们》,给任晓雯带来了很好的小说技术口碑,人们在各种浅薄的标新立异之余,忽然读到如此诚实,如此细节密布的小说,一定有某种意外的惊喜。
这正是当下的意义,我的意思是说,在这样的写作语境里,任晓雯的写作位置,就是一种固执的当下性,她通过一种诚实的当下写作,像带着铅笔的画家外出素描一样,将上海的日常细节深刻地写到了纸上。
从内心写作到当下写作的任晓雯,当然有某种超拔的写作梦想。这就是《阳台上》。将三篇小说放在一个分析框架里阅读,我大致看到了任晓雯小说的某种可能性。这正是年轻的小说家值得期待的地方。事实上这篇好评如潮的作品,在语言技术的层面,依然是诚实的当下写作。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任晓雯似乎不愿意魔幻现实。我在初读《阳台上》的时候,好几个地方忍不住手痒,因为张英雄和陆珊珊这两个人物似乎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荒诞性,但任晓雯就是处变不惊,轻易将这种能够后现代处理、能够先锋的细节漏掉了。
这样的节制,一直持续到小说的最后,当张英雄锋利的屠刀竟然转变成一种爱,一种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残留的温柔,任晓雯的某种近似于超拔的人性意义,才来到我们的面前。很久之后,我似乎有些明白了,最优美的意义总是在这个世界上最低的地方,最超拔的审美来自最具体的细节。
在这篇小说里,任晓雯不再是一种内心的铺陈,也不再是一种当下的切入,这个时候她像一个旁观者,她渴望爱,渴望怜悯,于是,在最不该有爱的地方,爱在生长。















![任晓雯的前夫 [任晓雯专号] “乏味”的美女 精敏的作家](https://pic.bilezu.com/upload/a/13/a13c7dd4964d96f0f3a223ae4c483597_thum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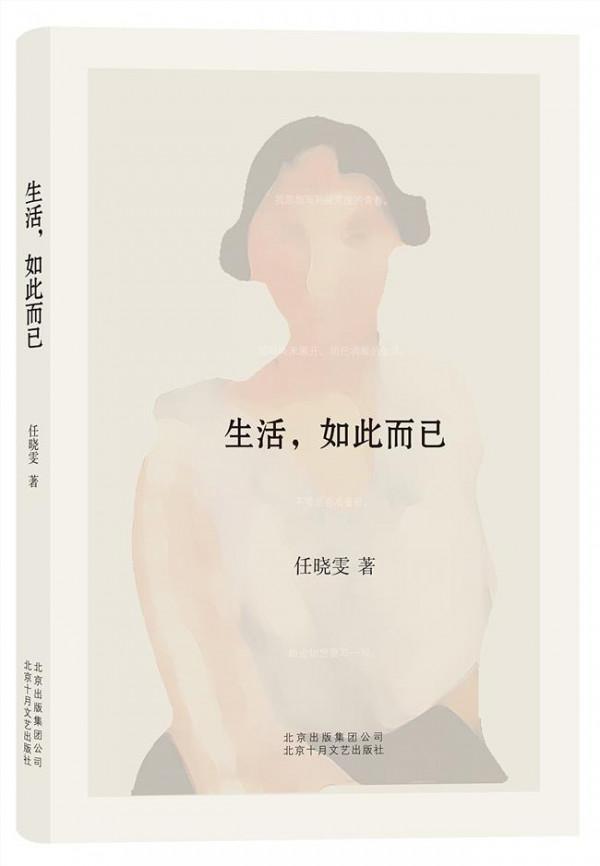
![>[任晓雯专号] “乏味”的美女 精敏的作家](https://pic.bilezu.com/upload/4/58/458084df1bc7ed3679490fd53f995f3f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