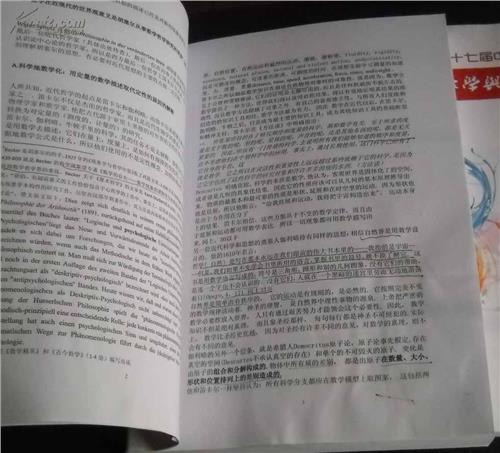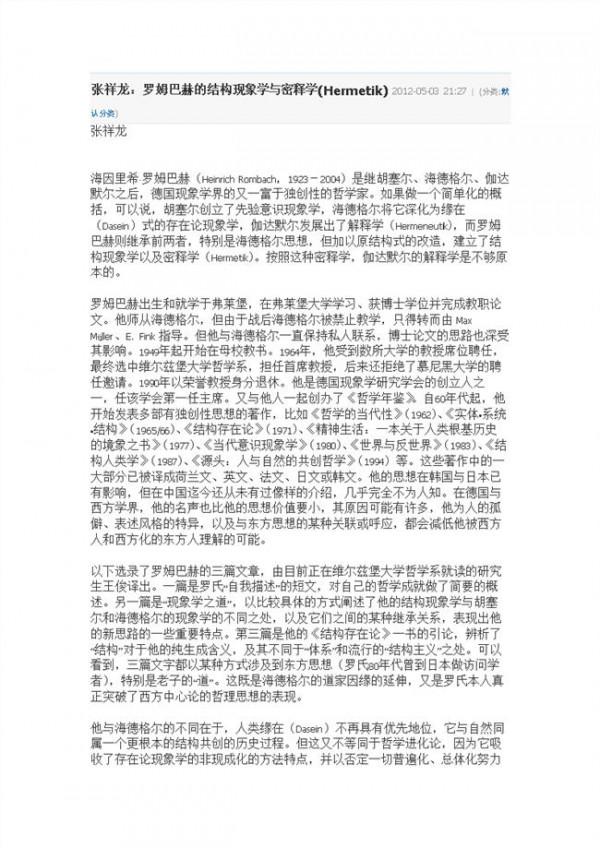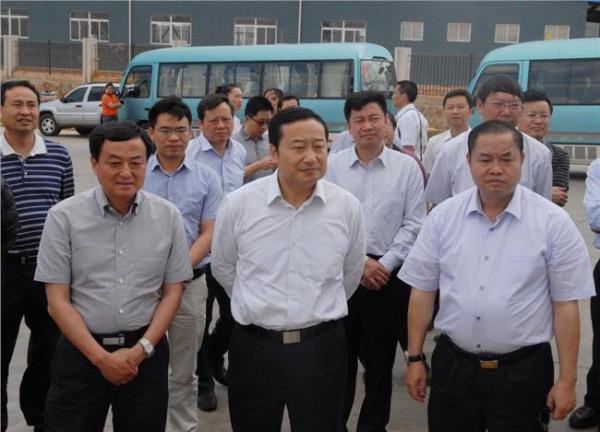张祥龙现象学专题 现象学在中国与中国现象学
现象学关注生命,强调体验,坚持认为在现象的背后一无所有,但现象学并不因此就雷同于实用主义、现象主义和生命哲学。现象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这就是它对先天的认可,对先天论的构建和证明。尽管在现象的背后一无所有,但诚如海德格尔所言,那应该成为现象的东西却没有显现出来。
表象和假象盛行,唯有通过还原,将其置于括号之中,我们才能“回到实事本身”,回到那仅仅来自自身而绝不来自经验的先天之物。这种先天之物,在胡塞尔那里是本质或艾多斯,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存在者的存在和存在本身,在萨特那里是存在和虚无,在梅洛庞蒂那里是身体或肉,在勒维纳斯那里是他者,在德里达那里是不可解构的“过先验性”,在马里翁那里是被给予性。
尽管它们是如此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不仅不是来自经验的累积和抽象,反而是我们一切经验得以可能的前提。
带着这些禀赋和特质,现象学来到中国。
一、现象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
限于篇幅和主旨,本节仅仅提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在中国接受和传播的几个主要节点。一部完整的关于现象学运动诸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在中国的接受史,目前尚未问世。不过,关于意识哲学、存在哲学和解释学三大流派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情况,可参阅张祥龙等:《现象学思潮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西方哲学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始于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1854—1921),他于1896年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选译为中文并以《天演论》为名出版。在其后的数十年内,一大批现代西方哲学著作,如意志主义、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和生命哲学等等,有了自己的汉语译本,并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现象学在中国的接受起步相对较晚且进展相当缓慢。20世纪20年代,一些中国学者如张东荪(1886—1973)等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胡塞尔的一些基本观点已经有所提及,甚至在个别学者那里有一些更为系统的论述,但这些介绍主要基于当时日本的现象学研究而非直接依据德国的现象学运动。
在20世纪上半叶,与日本相比,中国研究德国现象学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屈指数来,排在首位的当推熊伟先生(1911—1994),他属于中国第一代留学德国学习现象学的人。他于30年代来到德国弗莱堡大学,参加海德格尔的研讨班和讲座并深受其思想方式的影响。
回国后,熊先生辗转于多所大学,最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成为海德格尔研究的一代宗师。他是国内介绍和翻译海德格尔思想第一人,也培养、影响了一批海德格尔思想的研究者和翻译者,海德格尔作品的汉译绝大部分出自他的学生或追随者之手。
与熊伟同时期在弗莱堡的中国学生还有两位:一位是萧师毅,他在1946年与海德格尔一起尝试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德语,后任教于台北辅仁大学。另一位是沈有鼎,他的论文是芬克代表胡塞尔指导的,他可能拜访过退休后的胡塞尔,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从30年代末起,中国的现象学研究几近停滞,只有香港和台湾由于历史原因而成为例外。从大陆移居台湾定居在台北的牟宗三先生(1909—1995)是20世纪最重要的儒家思想家之一,他于50年代开始钻研实存哲学并因此而对现象学有所涉猎。胡塞尔现象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选译了《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于1980年问世,译者为移居台湾的胡秋原(1910—2004)。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许多对西方哲学感兴趣的学子远赴欧美学习现象学,这其中也包括熊伟的弟子们。到90年代末,在国内或国外受过专业训练的新一代现象学研究者开始崭露头角。1994年,这些学者组织了中国第一次现象学会议并成立了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这个团体定期举办年会,定期出版年刊《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1996年,香港现象学会成立,旨在利用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学术开放政策为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提供平台,2004年,《现象学与人文科学》杂志在台北出版,成为香港现象学界的核心刊物;在台湾,一些现象学的研究机构和中心先后成立。
从此以后,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现象学界逐步展开越来越密切的合作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