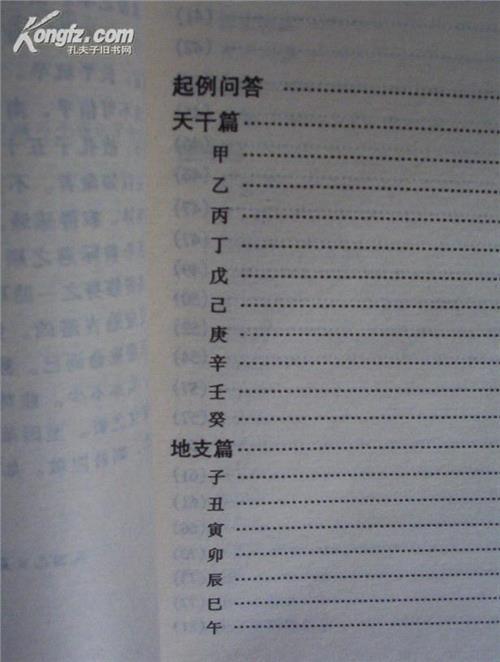程千帆的诗 巩本栋:程千帆先生与我的师生之缘
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我就曾旁听过程先生的课。那时,我尚在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南京师范学院离南京大学很近,两所学校原本同源,那时候又是青年学子和整个社会都努力向学的时期,两个学校的老师们教学特别认真,为了让学生知识掌握得更全面,互相兼课的情况很普遍。
比如段熙仲、钱小云等先生就在南京大学授过课,而鲍明炜等先生,也去南京师院授课。两校的学生读书都很勤奋,互通消息,一些重要的课程和讲座开讲时,台下挤满的听众中,往往都是这两个学校的学生。
那时候,我也常去南京大学听课。像先师程千帆先生的“杜诗研究”、周师勋初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当时在新教学楼上课)和鲍明炜先生的“音韵学”(时在西南楼前平房上课)等课程,我都完整地听过。
程先生讲杜诗,记得是在1981年9月,因为课是给研究生开的,地点就在教学楼一楼南向的一间小教室里,每周两节,听众并不多,但有学生也有本系的老师(如许永璋先生就每次拄着拐杖,坐在最後一排,跟班听讲)。程先生讲杜诗,事先编有讲义,分若干单元,文字繁体竖排,隽秀工整(後来我知道这是出自先师母陶芸先生之手),上课时按专题讲授。
先生上课,经验丰富,尤其是对时间的掌握,最为精确。每次上课,程先生总会略提前几分钟来到教室,稍稍坐定,便开始上课,侃侃而谈,声音宏亮,又从容沉稳。而每当先生把一个问题讲完,宣布这一讲结束时,往往是话音始落,下课的铃声就响了。真是神奇。
先生上课,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而又十分生动。他常常是先提出问题,再层层论证,理论性既强,材料又十分丰富,特别有说服力。同时,先生讲课,又喜用比较之法。通过比较,不但可使听者对杜诗的精神深有领悟,而且又纵横捭阖,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颇富启发性。
比如,他讲杜甫的《望岳》,就将其《青阳峡》、《凤凰台》、《万丈潭》和《剑门》诸诗与之进行比较;讲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联系张衡的《四愁诗》和文天祥的《六歌》;讲前後《出塞》,又附以范成大的《催租行》和《後催租行》,等等。程先生的讲授,深深地吸引了我。
一次,先生讲到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举岑参、高适、薛据和储光羲诸人同时所作,进行比较,并指出这种同题共作的情形,最能见出诗人的用心。我当时就马上联想到:韩愈和孟郊的联句与唱和诗不也是同题共作吗?二者之间是否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呢?程先生在课上讲授的这些专题,後来大多都与我的师兄莫砺锋、张宏生合作,写成文章,结集为杜诗学的专著《被开拓的诗世界》了,我在听先生讲杜诗时所想到的诗歌唱和问题,也从此开始在心里酝酿。
後来,我做硕士论文,便是以唐宋唱和诗词研究为题的,这是得益於先生的启发,也是我与先生结缘的开始吧。
或许是有了旁听程先生讲杜诗的机缘,1987年夏,我从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硕士毕业时,几乎没有多加思索,便报考了程先生和周勋初先生的博士生,而且,事先不曾与两位先生联系,笔试後也没有再面试,就被录取了,顺利进入南京大学,得以师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那一年,两位先生只招收了我一个学生,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缘分。
在南京大学学习的三年中,先生为我指定阅读书目,提出选课意见,批阅日常作业,选定博士论文研究课题,逐章审读、批改论文初稿……,在先生的具体而切实的指导下,尤其是平日里不定期的在先生家中的交谈(先生允我,有问题可随时到家中交谈),这不但使我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奠定了以後学术研究的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教会了我应该怎样走好人生的道路。
这三年的学习和经历,对我来说,其重要意义,是无论怎样估量也不会过高的。现在回想起来,能够跟随两位先生读书问学(当时卞孝萱先生和郭维森先生为副导师),岂止是难得,真是有些“奢侈”了。
我毕业後,在两位先生的鼎力推荐下,留校工作。近水楼台,留在先生身边工作,这使我对先生所说的师生缘分有了新的认识。
记得是从1995年起,程先生开始时常让我整理与撰写一些先生回顾、总结、论述和阐发其学术历程、经验、思想与方法的文章,在先生的指导下,像《我与黄季刚先生》、《敬业、乐群、勤奋、谦虚:关於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谈话》、《关於学术研究的目的、方法及其它》、《贵在创新:关於学术论文写作的问答》等文章,都是那时整理或写成的。
1996年,先生又嘱我编纂《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次年,又编成了意在反映先生研究中“华彩乐段”的《俭腹抄》(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作为先生的及门弟子,编纂学记等,从一个侧面反映先生的学术成就、思想和方法,当然是责无旁贷和十分有幸的。然最初接受这一任务,心里也不免有些担心。因为同门中留校工作的有莫砺锋、张宏生、曹虹、张伯伟和程章灿诸兄,若由他们来承担此责,应当比我做得更好。
也许是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在一次交谈中,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这些年,我的身体衰弱得很厉害,已不能再上课,你来南大後,我也没有给你上过课(先生不知道我曾旁听过他讲杜诗),通过这些文章的整理、编撰,我希望你能对我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有更进一步的体会和理解。
听了先生的这番话,我内心不禁涌起一股热流,我明白了先生何以会十分重视师生缘分,何以会说“(师生之间),要有什么谈什么,师徒之间互相了解和交流,了解彼此做学问是个什么路子,否则也没法子成为师徒”这样的话(见《敬业、乐群、勤奋、谦虚:关於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谈话》)。
所谓师生之缘,就学生来说,便是亲师取友,是要能继承和发扬先生的学问;如果入其门而无所得,犹如虽入宝山却空手而归,既不能领会、承继和发扬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方法,那也就“没法子成为师徒”,算不上有真正意义上的师生之缘。
先生离开我们已十三年了,在怀念先生的时候,我常常扪心自问,从先生读书问学多年,究竟有没有继承和发扬先生的学问呢?当然,这也许是一个更适合由他人来解答的问题,然有一点则可以肯定地说,那就是对先生的学问,弟子是信奉不疑,纵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