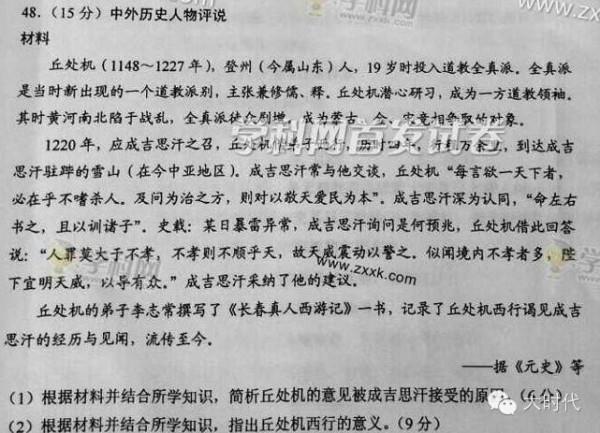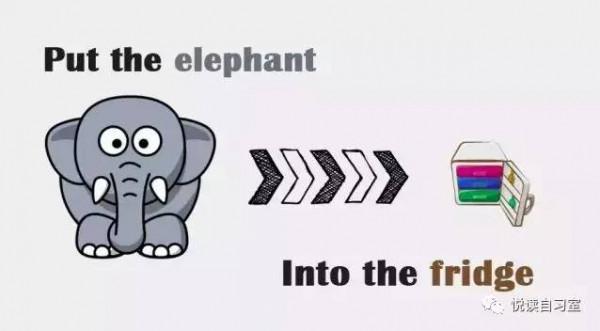蒋多多的现状 对高考制度的无奈接受中蒋多多成为笑话
这个周末,有个故事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个叫蒋多多的河南女孩,她参加高考的目的,竟是希望各科成绩都得零分,以引起社会重视。因此她将考卷的主观题部分,全部用来写自己对高考弊端和当前教育制度的指责。
她还故意把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写到密封线外,所有试卷都用双色笔来写。在离家出走十几天后,她给报社打去电话:“我已走投无路了,不敢回家,我该怎么办?” 这无疑是一个悲剧。
但我却不得不把这个故事定义成“蒋多多笑话”,因为在很多人眼里这就是一个笑话。“她所写的高考制度弊端纯属无稽之谈”,这是班主任对蒋多多行为的定性,并且很恰当地给她安上了一个“上课总是心不在焉,成天不学习”的罪名。
同学们都认为她这样做“很傻”,教育心理研究专家则认为“她的心理不健康”。就连一向以扶助弱者为己任的时评家们,也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淘气的孩子在一个不合时宜的场合,做了一次孩子气的‘撒娇’。
或许是为她不好的学习成绩找到一个掩饰的借口”。 就这样,本应震撼我们心灵的蒋多多,被我们消解和分析成了一个“笑话”。
我们的心灵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撞击,反而获得了一丝身为看客的愉悦。现行高考制度的弊端和不公正,已经被太多人以理性而克制的方式质疑过、抨击过,但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感性而冲动地把它写到自己的高考考卷上。
虽然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后者都理当比前者更有冲击力,但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前者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后者却被视为笑话——口头上我们都是勇将,行动上我们都是逃兵。 当然不是说,应该向蒋多多学习,用自己的前途来和高考制度做“必输博弈”。
但是,当有人做出了我们敢说却不敢做的行为时,我们是否至少应该表达内心的尊重?其实蒋多多期待的也只是引起社会重视,而不是奢望大家都把她当成学习的榜样,前赴后继下去。
显然,“蒋多多笑话”之所以在人们的思维中生成,重要的不是其行为离经叛道,而在于其结果是堂吉诃德式的“大战风车”。
在大多数人看来,蒋多多的举动只能葬送自己的前途,而不会在制度上产生任何改变。大家都已经安于现状,顶多在嘴皮子上发发牢骚,竟然有一个人以为在考卷上发泄不满就能触动制度,怎能不是笑话呢? 明知是一个有瑕疵的制度,但是大家早已习惯与之和平共处,当有人试图以一己之力对抗制度的不公时,人们都发出了爽朗的笑声——这不该作为反证制度合理性的证据,而只能证明改善制度无望给人们造成的“习得性无助”心理。
“习得性无助”缘自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做的一项经典实验: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蜂音器一响,就给以难受的电击,狗在笼子里无处可逃。
多次实验后,在给电击前,先把笼门打开,蜂音器响了,狗不但不逃而是不等电击出现,就卧倒在地开始呻吟和颤抖——本来可以主动地逃避却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这就是“习得性无助”。 深陷“习得性无助”困境里的人们,已经无奈地坚信高考弊端的阶段性不可更改。
此时,不自量力的蒋多多站起来挑战制度的“电击”,于是就成了一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