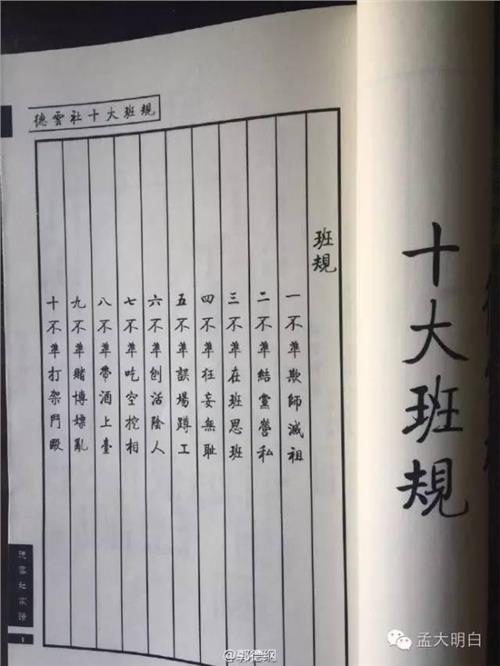林鹤鸣张耀杰 张耀杰:与林毓生谈胡适罪错
2011年1月10日,我在武昌参加由共识网主办的辛亥革命研讨会期间,陪同范泓、李洁、陈浩武三位师友到华中师范大学拜访何卓恩教授,获赠何教授一本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的《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这本书我一直没有通读完毕,一个原因是我没有精力专题研究殷海光;另一个原因是我从该书代序《我所了解的殷海光和自由民主--林毓生先生答本书作者》中,意外读到林毓生及其业师殷海光对于胡适先生的心理黑暗的贬低否定,从而丧失了继续阅读的兴趣。
一、林毓生价值混乱的自相矛盾
此前我通过网络接触过林毓生(Yu-sheng Lin)逻辑混乱的部分文章和演讲视频,当时并没有十分在意,只记得他有几个还算光鲜的身份符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殷海光在台湾大学的从业弟子,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关门弟子。
作为一名胡适研究者,我自从读过林毓生于2003年3月与何卓恩的这篇问答记录,便对他和殷海光的相关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怀疑。
据林毓生介绍:"殷先生从来没有说硬搬西方,把我们中国变成美国人,那是胡适之才这样讲。殷先生看不起胡适,跟我当面讲话的时候,非常厉害的。当然表面上因为不好意思,因为他是长辈吧,而且他是前辈,在一个传统里面,在一个自由主义传统里面。
所以,殷先生在文章里面写过几篇,也是对胡先生还是比较维护的。因为把胡先生这个旗子打倒以后,更没有人顶了。还有胡先生政治上跟蒋家也可以说说话呀,保护保护他。但是殷先生跟我们学生在家里单独讲话的时候,非常看不起他。因为胡适没有东西,没有什么正确的东西……"
作为佐证,林毓生引用了《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中的一段文字:"胡适之流的学养和思想的根基太薄。以'终生崇拜美国文明'的人,怎能负起中国文艺复兴的领导责任?更何况他所崇拜的美国文明主要是五十年前的!他虽常在美国,其实是在新闻边缘和考据纸堆里过日子,跟美国近五十年来发展的学术没有相着干。"
关于胡适的人格,林毓生议论说:"胡先生人格并不是太坏,胡先生不是一个什么英雄啦,但是人还是一个正派人,还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发挥了一些儒家思想的美德啦。比如说,他在美国当大使的时候,他回到家里比较晚,进门,赶快把鞋子脱下来,拿两只手提着,穿着袜子走,怕皮鞋吵着别人睡觉。
这是恕道吧?人倒挺好的。他是个普通人,他不是个伟大人物。这有什么不好?这很好嘛,就是这个人还不错,但是,但是他没有什么伟大的气息,不是一个领导人物啊!胡先生的缺点就是太好名。他好名,好名好得厉害,好到自恋的程度。他是大人物呀,大人物没有他那么好名的呀!"
行文至此,不难发现林毓生自相矛盾的价值混乱:一方面说胡适是"硬搬西方,把我们中国变成美国人",另一方面又说胡适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发挥了一些儒家思想的美德",这种美德叫做"恕道"。与胡适表现出来的所谓"恕道"相比较,自以为"能负起中国文艺复兴的领导责任"的殷海光、林毓生,在评论曾经给予他们相关保护的胡适时所表现出来的,分明是对于中国传统的所谓"恕道"的严重败坏,或者干脆说是一种反传统的反恕道。
为了证明胡适不能够"负起中国文艺复兴的领导责任","反恕道"的林毓生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证胡适的罪错。其一是所谓"科学主义";其二是所谓"太好名";其三是所谓"全盘西化"。
二、林毓生所谓"对科学的误解"
关于胡适的"科学主义",林毓生议论说:"因为胡先生永远没有进步。到临死的时候,还是他早年的那些科学主义,科学救国什么的。实际上胡先生对科学的了解是误解的,把科学当做宗教来崇拜。……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间问题,是对科学的误解。
实际上科学有些贡献,但最主要的大问题,科学有困难,是要用人文来解决。胡先生全都弄错了嘛,在大关大节的地方,思想上都没有弄对。新儒家这方面,我觉得比他强。什么科学救国?我现在举个例子,自由民主都不能用科学来证明,自由民主是哲学问题。
……人的价值也不能用科学证明。为什么人有价值呢?科学证明不出来。甚至科学最基本的观念,科学自己都没办法证明。是理性的东西也好,是上帝的也好,反正永远不是科学。这些很复杂的东西,胡先生没有接触。因为什么?他根本没有到这个程度。一些哲学思考他没有想到。他为什么没有想到?一天到晚去应酬。"
在我个人的阅读印象里,胡适并不是所谓"把科学当做宗教来崇拜"的"科学主义"的倡导者,而只是一度充当过"科学的人生观"又称"自然主义的人生观"的倡导者。1923年11月29日,胡适在为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所写作的序言中,通过他自己所谓"粗枝大叶的叙述"而得出的结论是:"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变是有自然法则的,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竞争的惨剧鞭策着他的一切行为--这个两手动物的自由真是很有限的了。
然而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的这个渺小的两手动物却也有他相当地位和相当的价值。
他用的两手和一个大脑,居然能做出许多器具,想出许多方法,造成一点文化。……总而言之,这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里,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诗意,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充分运用'创造的智慧'的机会。"
胡适所说的生物学偏重于自然科学、社会学偏重于人文科学。从这样一段话中,丝毫看不到林毓生所谓"把科学当做宗教来崇拜"的"误解"。林毓生所谓的"甚至科学最基本的观念,科学自己都没办法证明",同样可以套用于他所谓的"哲学":"甚至哲学最基本的观念,哲学自己都没办法证明。
"道理很简单,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都没有所谓的"自己",拥有"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的,是作为精神生命体的个人及其大同人类。是每一位主体个人利用自己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文化积累和精神创造,赋予自己及人类社会以约定俗成、可供度量的普世性的价值要素和价值谱系。
这些普世性的价值谱系中最具有充分世界化的理性内涵和大同意义的价值要素,是个人自由、契约平等、民主法治、宪政限权。单就作为主体个人及人类社会的第一位的价值要素的个人自由而论,无论其内涵多么复杂,其外延都是可以用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来加以限定和度量的:
其一,自由意味着主体个人意思自治、自我担当、自我规定的责任与权利;
其二,自由需要主体个人运用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充当底线支撑和最低保障;
其三,每一位主体个人的自由都是以力所能及的量力而行作为阈值阀限的;
第四,每一位主体个人的自由都是以其他个人的自由权利作为明确边界的。
在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的现代文明社会里,度量个人自由的最为确切的方式,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和公共领域的法律条款。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毓生所谓的"人的价值也不能用科学证明",显然是一个违背常识的伪命题。在这些常识性问题上,需要的只是诚实理性而不是什么高深程度,林毓生指责胡适"根本没有到这个程度",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真正缺乏科学及学术的常识理性的,并不是胡适,反而是林毓生自己。
三、林毓生所谓的"太好名"
关于胡适的"太好名",林毓生议论道:"我在政大的讲演,讲得很清楚。何炳棣先生,他是一个很好的史学家,很有成就的,……胡先生请何先生住在院长官邸,胡先生很器重他,因为何先生在海外很有成就嘛。……何先生吃了早饭以后,要出去找老同学啦什么,很多事情;胡先生也忙得要死。
他俩就是每天早晨吃一次早饭,晚饭也不在一起吃。这样待了五六天,有一天吃完早饭,何炳棣先生问胡先生,'胡先生,您照我的看法,我的观察,您是不是在醒的时间,三分之二是用在会客上面?'胡先生思考片刻,说'大概不太远,大概是这样。
'一个人用了三分之二醒的时间到处去会客,那怎么能够变成个大思想家呢?没有这样的事。不劳而获,变成一个大思想家,变成领导时代的一个时代的大运动,有些思想,有些系统的想法,这不可能的。
是什么呢?就是名人而已,到处去见,到处去接受。你可以不要嘛,你不是奴隶,你不是会客的奴隶,你自己的问题呀。何先生的文章还提到,有几次当着外国人的面前,胡先生说自己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太好名了,好名好得过分了。好名哪个人不好名,但是有个程度不同嘛,人都有点虚荣心,又不是上帝,也不是天使。问题就是有程度的不同,过分了嘛。"
胡适所谓的"中国文艺复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围绕北京大学与《新青年》杂志而展开的新文化运动,其主要功绩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对于白话文的提倡普及;其二是对于外国先进文化的介绍引进;其三是胡适对于"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价值观的倡导践行。
尽管"中国文艺复兴"由于政治形势的变迁而中途夭折,却并不影响胡适作为"中国文艺复兴"第一人的历史地位。胡适在外国人面前采用拟人化的表述声称"自己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虽然在学术层面上不够严谨,他作为中国文艺复兴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却是不可替代的。
晚年胡适已经不再是一名单纯的学者,而是站立在台湾地区的学术岗位最前沿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一个人用了三分之二醒的时间到处去会客",是为了保证更多学者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而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能够变成个大思想家"。
林毓生为此批评胡适"太好名了,好名好得过分了",所暴露出的恰恰是他自己有失"恕道"的"过分"狭隘和"过分"好名。
四、"全盘西化"的恶意诋毁
关于胡适的所谓"全盘西化",林毓生的议论更加离奇:"他的全盘西化也不通。全盘西化是什么意思?连西方最坏的东西也接收吗?那是李敖这样说。第一,全盘西化本身是不可能的事,世界上没有这种事,不可能全盘西化。第二,你的目的是什么?问题提清楚嘛。
后来胡先生过了几年又说,我不是全盘西化,我是'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充分'现代化。充分现代化最后还是全盘西化。虽然不可能达到全心全意的西化,还是西化呀,因为没有一个限定嘛。"
查勘胡适发表于1935年6月21日天津《大公报》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其中首先检讨了自己1929年"因为用字不小心,引起的一点批评":"潘光旦先生在《中国评论周报》里写了一篇英文书评,差不多全文是讨论我那篇短文的。
他指出我在那短文里用了两个意义不全同的字,一个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一个是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潘先生说,他可以完全赞成后面那个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个字。这就是说,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能赞成'全盘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