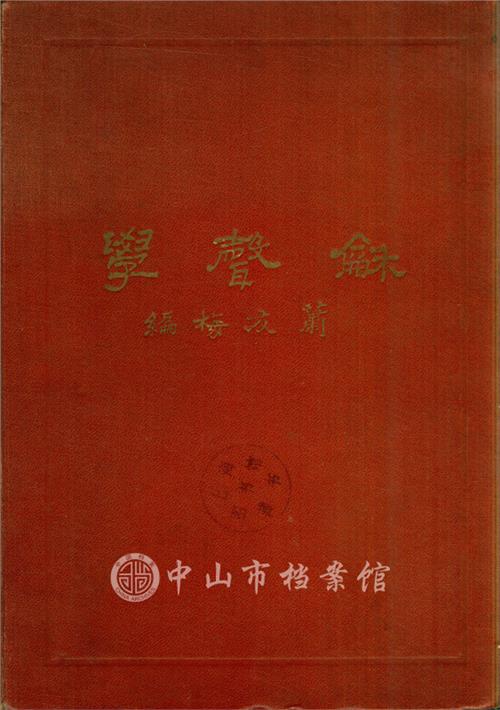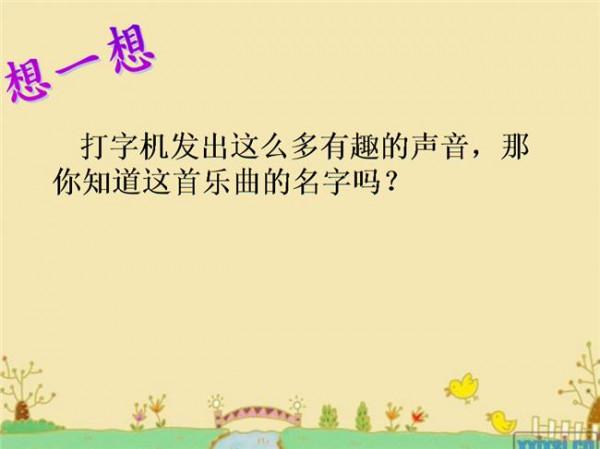萧友梅音乐创作 民族文化题材音乐创作不能丢“本”
随着音乐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文化软硬实力的增强,音乐创作者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加入民族音乐文化的元素,在日益成熟的技术支撑基础上,创作获得了国内外专家同行、普通爱好者的肯定。笔者观看“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的作品选材多属于此类,由此而写了《艺术作品要有国别属性》的短评,意在对此类探索的特点予以肯定。
不曾想与吴跃华的“国界”文“撞车”,招致其回应文章《哪个艺术作品能没有“国别属性”?》(10月19日争鸣版)。看过吴文后觉得,其针对拙文的质疑多属附会,且很多处偷换概念。笔者不想逐一回文,仅想就其中的关键之辞做些辨析。
首先,不能混淆“能否被理解”与“有无民族音乐文化特质”的关系,两者不是对应之辞,前者强调的是受众视角,后者着意的是创作视角。吴文引用某位专家对俄罗斯合唱的肯定,进而“表达俄罗斯音乐也能被我们理解的感叹”。
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观众与俄罗斯观众的理解深浅肯定不同吧?这是音乐体裁局内外文化认同的问题。接着疑问:是不是“能被理解”就可以模糊“民族音乐文化特质”在新创作中的负载了呢?并进而模糊国家文化的品格属性了呢?这一推论拿来反驳我的文章太过牵强。
国内外的任何种音乐都可以或多或少地被理解,它比语言文字的障碍在某种程度上是少一些,有的是深度的理解,有的是浅层次的感受,有的仅是获得某种新奇感,有的可能是附庸风雅甚至是“皇帝的新衣”。小泽征尔认为二胡版本的《二泉映月》比弦乐队版的更能触动其内心,小泽自幼受中国传统音乐浸染,是他“能解”的深浅程度不同。
“能解”有文化局内与局外之别,长期受俄罗斯音乐熏染的其地大众与西安人感受俄罗斯现代合唱的深浅自然有别,这是特质的本民族音乐文化彰显的价值所在。
民族音乐文化不管是古代的题材,还是民间的、传统的题材都一样,我的文章仅就几部古典题材舞剧而谈,吴先生不应偏解。这里要强调的是,当前的音乐家们的创作要多从深层次角度去探索。在强调文化多元化的同时更不能忽视民族音乐文化特质的附加与显现,否则将会有被强势文化逐步侵蚀、占领的可能。
创作要凸显民族音乐文化的本原蕴涵并进而彰显国家性征,需要依托于物化形态的旋律音阶,并进而衍及韵味、精神。“梁祝”之所以感动了世界就在于它对越剧主题旋律的引用,《丝路花雨》之所以盛演不衰就在于它对敦煌古韵的深度附载,《我爱你中国》之所以风行国内外就在于它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歌颂。
国家“非遗”的举措就是在强调民间、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并活态发展,而非吴文作为弱化民族性的挡箭牌。田青特地强调要原型地保存,韩宝强强调全息式保存,就是在强调它们曾有的原汁原味;周湘林等作曲家当年去贵州采风时强调要看村里的民间艺术家的表演,而非文化馆或剧团能手的表演,是强调其创作中能抓住民间音乐文化的本原特质。
模糊民族音乐文化特质甚至消除音乐国别定性的论调是打着多元文化的幌子,无视民族特点,抹煞民族差别,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甚至认为“民族”是虚构的概念,其根本是否认民族的存在!
其次,民族音乐文化特质的彰显永远不会是“老掉牙的宏论”,它是常说常新的话题。它虽有些宽泛,但绝对不是“稻草人”式的形同虚设。历史地看,中国是一个善于接纳外国文化并将之发扬光大的民族,贯通西域的汉唐“丝路”上传来乐器、乐曲、乐人等都已“内化”为中国民族文化大家园中的一份子,如琵琶、觱篥、扬琴、《摩诃兜勒》、苏祗婆的“五旦七声三十五调”等。
这里的“内化”是在本民族音乐文化基础上的一次再创造,而非不假思索的、表层化的“拿来主义”。
上个世纪初传入的西方音乐文化是从当时到现在的占有统领地位的主体文化,但从李叔同、萧友梅、郑瑾文、黄自、刘天华、青主等开始,都有意识地在探索民族音乐文化的内容与外来形式与技术融合、发展问题,崇西、崇中、结合等三种思潮的历史辨析也有余锋、冯长春等人做过,已证明了民族音乐文化特质是为最好的选材思路;新中国成立后,贺绿汀、丁善德、吴祖强、朱践耳等也在西方音乐技术的运用基础上更深入地彰显民族音乐文化特质,民间音乐家被大量地请进音乐学院课堂,饱含民族音乐旋律、韵味与精神的作品如《长征交响曲》、舞剧《红色娘子军》、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等已成为“新中国音乐史”中的经典;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新潮音乐”探索者谭盾、瞿小松、郭文景、叶小纲、何训田、许舒亚等无一例外地以最具民族音乐文化特质的作品在国内外音乐圈中占有一席之地;本世纪开始,音乐家更加强烈地认识到民间音乐文化土壤的破坏而不约而同地将创演视角投入到民族音乐文化特质的发展中,秦文琛、邹航、朱琳、赵曦、宋歌、王丹红、姜莹、秦毅等青年作曲家都以最具民族性征的音乐题材为其创作的素材与目标。
这些证据无一例外地诠释了民族音乐性征的作品创作与研究是“常说常新”的话题。
再次,国别和国界不是一回事,肯定一种现象并不是否定其它现象。国家间的界碑是外在的、有形的,因此,国界往往有明确的标识;而国别是内在的、属性的,没有明确的界限之分,某种程度上是可意会之属。在拙文所论的文化属性语境中,国别是指需要彰显的文化特质,就是那种切身可感的音乐题材,其旋律、音调、色彩及其韵味、内涵、精神是民族文化圈中浸染者自觉可感的中国“味道”,与吴文所谈国界不是一回事。
笔者在肯定“丝绸之路艺术节”上的民族舞剧系列探索中所“彰显艺术作品的中国文化属性”,并非批评其它的素材、技术之选,跟高大上的“二元理论”扯不上丁点儿关系。
溯源方能固本,如果不从创作的民族音乐素材本源进行创作探索,弱视民族音乐文化特质的彰显,忽视国家文化属性的立意,而仅自恋于技术的炫耀,仅满足于“能解”观众礼节性的喝彩,仅流连于概念的“纠缠”,民族音乐的现代之路将会逐渐丢失根本。望与致力于中国音乐发展的实干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