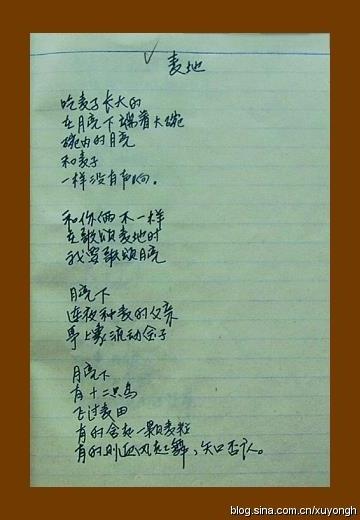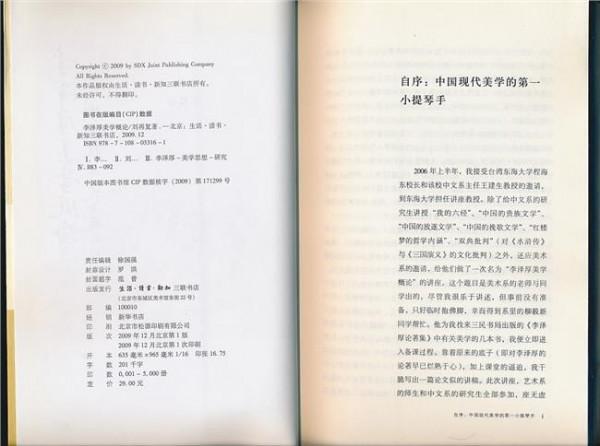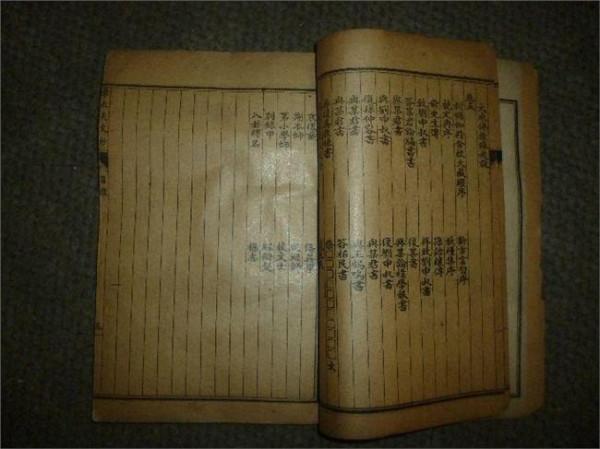刘小枫丹东 国父毛泽东——刘小枫
刘小枫与人关于宪政的对话注定会成为一个事件。他的言论也注定会震惊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作为一个文化基督徒的圣像突然间崩塌了。自由主义者申斥他认毛作父,这不过是因为刘小枫是他们的父,而现在,这个父抛弃了他们。
再也没有什么书,能比《拯救与逍遥》《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更有影响力地塑造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伦理心智,几乎所有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在刘小枫作品的精神场域中成长的。
自由主义者必然困惑万分:一个曾经写过《记恋冬妮娅》的自由主义者,何以会对毛泽东声辩呢?一个个人主义者是怎么转变为国家主义者的?其实,如果我们稍微了解刘小枫近年来的思想脉络,那么他的所有言论都完全在意料之中。这或许说明,很多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永远地定格在了上个世纪。
刘小枫的言论注定会成为一个问题。右派派将此视为恶劣的叛变,左派视为回归正道,而儒家,正如在所有关于现实问题的评价上,一如既往地分裂为两派:拥刘或赞刘。但刘小枫的问题不过反映了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即对毛的评价。
我们与其说在评价刘小枫的问题上针锋相对,不如说是我们在评价毛的问题划为了森严壁垒的两个阵营。因此,无论我们反对或赞同刘小枫,如此剧烈的对峙,恰恰证明了刘小枫的一个判断,即如何评价毛泽东是宪政的最大问题,如果宪政首先意味着某种基本的政治共识的话。自由主义者以他们对刘小枫的反对,证明了刘小枫是对的。
自由主义者或者说右派停留在在低水平的谩骂中,并没有回应刘小枫的这个论断。而国家主义者或者说左派也不外乎看到了刘小枫对毛的辩护,大都没有明白刘小枫的意图。如果我们想要推进这场争论,首先要回答:在刘小枫那里毛泽东何以成为了宪政的问题?
刘小枫并非在法理或纯粹技术的层面看待宪政,他关切的重点在于宪政背后的nomos,这关乎立法的根本价值决断。无论是从对西方古代政治还是对西方现代政治而言,分裂的习俗永远无法支撑起一个整全和健康的政治架构。
希腊人不把外邦人作为他们的公民,柏拉图要把诗人放逐出城邦,霍布斯同分裂利维坦的黑暗王国势不两立,卢梭也为此申斥基督教对共同体的分裂,施米特对一切犹太人意识形态耿耿于怀。刘小枫同意这些政治哲学家的设想,即统一的政治习俗或宗教对政治体而言必不可少,若非如此,征伐不休内乱四起虚弱无力就是这个政治体的命运归宿。
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说,每一个政治体内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存在。然而,刘小枫清楚地知道,对毛的评价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人物评价,一部分中国人把毛视为魔鬼,一部分则视为神明,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内战。
这种精神内战也并非宗教与政治分离之后,两种宗教精神之间无关紧要的争战,它所涉及的是两种政制精神的对决,两方面都已经把对方决断为敌人,“民主之后杀全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毛的评价问题,决定着我们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未来命运。
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现代中国的两种精神之间的争战呢?显然,从刘小枫过去的作品看来,这一罪责必然要归咎于启蒙智识人的伤风败德。
要搞清楚刘小枫的隐秘论证,我们先要明白施特劳斯主义的思路。施特劳斯据说毕生致力于探究雅典和耶路撒冷之争,并把这一争论还原为理性与律法之争,即logos与nomos之争。
施特劳斯否定了任何综合两种传统开出第三条道路的做法,为此,他重返了中世纪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认为他们比基督教哲学家更为敏感地察觉到了两种传统的根本性差异。而基督教传统作为雅典和耶路撒冷的综合,直接地导向了西方的现代性道路。
那么,中世纪的东方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是如何处理哲学与律法之间的冲突的呢?施特劳斯由此发现了一种古老的写作技艺,即所谓的隐微书写。在这种书写中,存在着两种教诲——显白教诲和隐微教诲,显白教诲即是字面上的含义,这是面向大众的教诲,只有天资高的少数贤人,才能透过文本的字里行间明了更深层的隐微教诲。
虽然施特劳斯拒绝向我们提供干货,但更为大胆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不难从他的观点中开出药方:即耶路撒冷传统可以作为西方大众的显白教诲,而雅典的理性主义传统只能作为哲人的隐微教诲而存在,一旦把它向无天资的大众散布,政治共同体必然会分崩离析,生灵涂炭也将不远。
以施特劳斯主义的思路反观刘小枫,我们虽然无法知道刘小枫对毛的好恶,但即便是他个人对毛抱有崇拜之情,也不影响我们做出这样的断言:他为毛辩护的种种言论不过是一种显白教诲,他的真实的意思是:大众需要意识形态幻觉,国家需要统一的公民宗教,而对国父的崇拜正构成了这种崇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毛泽东不容否定。
刘小枫更为隐微的意思是,即便不完全肯定毛泽东,而是完全否定,也比争执不休要好。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只能是一个次好的选择。
为了回应在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和公知中流行的真相史学、宫廷史学、阴谋史学和地摊史学,刘小枫近几年来开始介入历史研究。他的策略也分为两个层面,在显白层面,他极力为毛所领导的革命战争、朝鲜战争甚至文化大革命声辩,然而,在隐微层面,他却提供了这样一种教诲,无论历史的真实如何,如果它对这一公民宗教不利的话,都应当为尊者讳,只留给少数有资质的人去探究,用历史去反毛是危险的。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刘小枫的真实想法是毛是现代秦始皇或暴君,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刘小枫看来,历史学家和公民宗教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前者致力于理性地探究历史的本源和真理,后者则意味着从祖先从英雄人物中得到道德的教化,确立生活的信念以及人生的意义。
我们不妨想想诗人普希金在看过一本有关拿破仑的真相史学之后所发出感慨:为英雄保留一些神圣吧,伟大的虚构好过可鄙的真实(大意如此)。
刘小枫先前在另一场演讲中与杨奎松、沈志华对话,其初衷也是如此。刘并非不关心历史的真实(他毕竟是一个哲人),但他不希望面向大众的历史书写被肆无忌惮的现代理性所劫持,因为这必将危及国家的根基。
然而,现代历史学家却不会作如是观,他们是尼采所说的滥用历史的人。他们揭去了大众的必要的幻觉,以至于危害到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尼采、施特劳斯和刘小枫们的敌人正是这些没有灵魂的专家,被困于理性的牢笼之间,用弱视的双眼窥视着墙洞外影响,却自以为得到了解放,看到了太阳的光亮。
这些专家虽然号称追求真相,却往往成为了意识形态的吹鼓手。施特劳斯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就是,它在事实和价值之间划开了一条虚幻的鸿沟,于是,科学成了反对生命的知识(排除了价值),而哲学则堕落为一种意识形态(排除了事实)。
当历史学家们自以为超越于一切价值判断之时,却不经意被某种意识形态所附体,从事实的领域跨越到价值的领地。
于是,没有灵魂的专家成为公知或被公知所俘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这些公知,正是披着启蒙外衣的现代智术师。他们把意见当做真理,用诡辩代替事实,发明历史,歪曲真相。专家与公知,正是启蒙理性的一体两面,他们既不懂哲学理性,又不懂政治习俗,无论心智还是思维都全面报废了。
他们满足于表达自己的一己好恶或意识形态,如果刘小枫知道了专家和公知对他的谩骂,我们不难想象他会耸一耸肩,轻轻叹口气:“这群报废了的启蒙智识人。”
施特劳斯和刘小枫们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开出的药方是,把logos在一个哲人的秘密城邦中宣讲,而让大众在nomos的幻觉中活着。历史学家们自然可以在学术研究中探究历史的真相,但在大众传媒中,我们只应当传播“好的真相”。
而这些公知启蒙智识人,把理性论辩带入大众,结果只能是我们在一些维系共同体的基本问题上的聚讼不休。因为维系共同体的,只能是意见而不可能是真理,这种意见必然是不可以通过理性探究而达成一致的,它属于修辞学而不是辩证法。
中国的nomos,一还是多?
然而,把理性与律法之争移置到中国是否恰当?这并非毫无疑问。那些以毛为图腾的国家主义者和毛左派,真的只是愚顽的大众的代表?那些专家和公知,真的只是启蒙智识人的代表吗?他们难道不是儒家士大夫的现代传人?《盐铁论》中的文学贤良、明末党争中的东林党人,一样是挂着为民谏言的牌坊,和现在的专家公知们又有什么区别呢?那里面唇枪舌战的儒法斗争,和现在的左右之争相比难道不是似曾相识?我们不难发现,儒法斗争和现在的左右之争的话语何其相似,从儒教士们的“不与民争利”到现在的对国企的诘难,从法家对地方豪民的限制,到现在左派的反吞并国有资产的呼声,这其中的逻辑岂不是一脉相承?
实际上,刘小枫在上个世纪的一些论著中,早已申明中国的革命精神起源儒家的心学成圣论和圣人革命论,而并非由基督教的末世论舶来。刘小枫之所谓沉潜儒学,正是要解决掉这两种儒学传统。
从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家一脉相承的性理之学,以为人人可以为尧舜,被刘小枫视为祸国殃民罪大恶极。为此,他写了一部《共和与经纶》,把新儒家熊十力冷嘲热讽地虐了千百遍。宋明儒者,正是刘小枫眼中的中国古代的启蒙智识人。
然而,刘小枫更可怕的敌人是春秋公羊学中的圣人革命论,他追随廖平向春秋谷梁学求援,甚至背诵起了庄子语录:“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如果刘小枫对革命精神的断言成立的话,他所面临的就将是一个上千年的革命传统,这一传统通过潜移默化的灌输,早已成为中国的nomos。
因此从施特劳斯主义的观点出发,无论刘小枫本人如何反革命,但在显白层面上他却只能支持这种革命。因此,刘小枫知道,启蒙公知并非舶来之物,他早已存在于中国的古代传统中。
但是国家主义者和毛左派们又如何定位?或许他们才是真正的舶来之物?既然启蒙智识人已经是中国的nomos的话,如果用理性与律法的对立来看待这种冲突,那么他们岂不就是logos的体现?刘小枫当然不会这么认为,右派公知会强烈反对,而大多数左派也会申明他们体现的才是中国最纯正的传统。
而且,如果我们深究《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中的革命精神的原型,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的隐约阴影。刘小枫的“两种精神的战争”的说法,或许应当这样来理解,即中国传统一直存在着两种nomos的争战,虽然他并未说清这两种精神究竟是什么。
在刘小枫的思想史研究中,他极为娴熟地运用了类型学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左派儒教士和右派儒教士这样的二元划分。两种精神是否可以溯源到这两种儒教士之争呢?但这两种精神类型不过是一场内部争论,他们都好不怀疑周孔的圣人身位,也在政治法统上没有争议,与现在的左右之争相比,不过是一场杯中风波罢了。
虽然刘小枫极力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左派儒教士,然而我们最好还是遵从他老人家的自我定位:秦始皇加马克思。
在毛以前,秦始皇可谓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他所创制的帝国体制绵延两千年之久。在他身前身后,儒法斗争是当时最主要的思想论战。两种思想之争的解决,最终是以秦始皇在精神上被全面否定,新的帝国以儒表法里的政治体制进行运作而解决的。于是,法家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治国技艺,丧失了它的“精神”,也丧失了它的法统和道统。两种精神的战争就这样解决了。
儒教士全面否定了秦始皇,于是在层层累积的历史书写中,我们已经难辨秦始皇的真实本相,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暴虐无常刻薄寡恩仁义不施的歪曲形象。儒教士和中国的公知一样,他们非常懂得如何发明历史,这一点,只要我们对比一下先秦史书《竹书纪年》和儒教士们书写的史书就知道了。
秦始皇焚毁六朝史书,以尊新王,树立新的道统和法统。但秦国的史书《秦记》在汉朝也失传了,谁又能断定说这和汉朝儒教士没有干系?孔子及其门徒的笔削春秋,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并无不同,都是在发明历史,树立自己的法统。儒教士们全面否定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文化大革命”,却代之以另一场无声无息的文化大革命。
关于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不过是儒法斗争的当代展开,是两种“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较量。当代的左派和右派,也并不是左派儒教士和右派儒教士的当下显灵,毋宁说是法家和儒家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
左派和右派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几乎任何论辩,都可以在咸阳宫儒法论辩和《盐铁论》中找到他们的古代知音。中国现在的公知,与其说是启蒙智识人,不如说是那些活跃于儒法斗争时代的儒教士的现代传人,只不过古代的礼法、仁义,变成了现代的普世价值和自由民主,而左派和工业党们在精神类型和经世策略上跟法家又有什么异样?
中国的“两种精神的战争”,与其说是启蒙智识人向公众散布意见的结果,不如说是儒法斗争的延续。作为当事人的毛泽东,比其他人更为敏锐地把握到了这场斗争的实质,现在看来,他晚年发起的评法批儒运动,不过是在为一场更激烈的左右之争热身罢了。
因此,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包括刘小枫本人,如果他们想要终结这场战争,他们也必须在法家精神和儒家精神之间做一个伟大的决断。左派的决断是确立毛泽东的法统和道统,右派的决断则如汉朝儒教士那样,要在精神上消灭毛泽东,以立新法统。那么,刘小枫的决断呢?他真的成为了国家主义者,或者说一个法家吗?
毛泽东何以成为刘小枫的问题?
从记恋过冬妮娅的小枫,到密不透风的刘子,刘小枫的形象可谓千变万化,但永远不变的是他对革命的恐惧,以及小资产阶级式的自我迷恋。毛的文革是刘小枫的原始创伤,无论是基督教式的基于个体偶在的伦理学,还是施特劳斯主义的隐微书写技艺,都不过是他疗救自我的手段。
刘小枫表面上在为毛的文革申辩,认为它的本义是要比美国更平等,但刘小枫至为恐惧也正是这种平等。在他早期的小资产阶级书写中,毛是一个不在场的存在,但他的阴影却无处不在,他化身为保尔,化身为牛虻,化身为罗伯斯庇尔,而他自己的灵魂则潜藏在读遍了俄罗斯小说的少女冬妮娅那里——他想象中的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贵族式气质,被保尔的革命精神无情地击得粉碎。
毛作为革命的象征,让他自始至终处在恐惧状态之中。于是,他不得不求助于尼采、舍勒的心理学,用来解构革命的崇高形象,在《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中,他终于在精神中完成了一次精彩的弑父。
但他始终无法摆脱对现代性的恐惧,因为这种抹平一切等级秩序的平等主义,并非始于毛主义,而是有着更为久远的源头,虽然他未尝明白这个源头是什么。在施特劳斯主义中,他寻到了恐惧意识的另一种形象,他的自我镜像从冬妮娅变成了苏格拉底,而他自己,也从文化基督徒变成了犬儒。
施特劳斯给刘小枫的教导是,哲人需要谨小慎微,恪守城邦的律法。在中国的语境中,城邦的律法从敬神变成了平等,但他显然难以容忍这种平等主义。
所幸的是施特劳斯主义还给了他另一个教导,哲人可以为城邦立法。于是,他悄无声息地把毛的形象由革命置换为国父。刘小枫清醒地知道,惟有重塑毛的形象,把它从一种革命精神变成一种国家图腾,把保守主义的精神灌注在这尊图腾之上,他才能摆脱恐惧,获得安慰。
在这个意义上,毛的确是他的父,是他想要杀死后来却又发现无法摆脱的父。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宪政的问题,而且首要地是刘小枫的问题。他以一个自由派所能有的最大敏锐,在理论中完美地解决了毛泽东问题。
那么,他何不像右派公知那样,彻底在精神上否定毛泽东,这样岂不是更加干脆利落来得清爽?问题的关键在于,令刘小枫真正恐惧的并非毛身上的法家精神,甚至也并非站在他的敌对面的儒教士的精神,而是在中国无处不在的平等主义的幽灵。
在毛时代,这个幽灵和法家精神确立了同盟,涤荡了儒家的精神即礼法伦理。这种同盟依然存在至今,因为正是在与当代儒教士的对立中,左派和国家主义者连成了一线,以至于二者的界限非常模糊。
毛的肉身中糅合了法家精神和平等主义的精神,他所体现的并不仅仅是古老帝国的法家传统,还是一个古老幽灵的现代显灵,再也没有比他自己的这个说法更能展现他的本质的了:秦始皇 马克思。刘小枫真正要解决的,正是这种平等主义的精神,他或许明白,再也没有什么比弑父更加登峰造极的平等主义了。因此,他他宁愿在法家精神的庇护下修炼他的古典心性,也不愿意让平等主义的幽灵重新游荡。
虽然红色中国中的平等主义与保守派们的政制设想南辕北辙,但比之自由派公知,红色中国重新声张了中国的主体性,而中华帝国古老的官僚体制也在新生的中国那里复活了,这个过程,仿佛是罗马帝国体制在基督教大公教会中的复活,原始基督教的革命精神由此而被扼制。
刘小枫虽然不一定对这种体制抱有好感,但比之任何推翻这个体制的行动,他更愿意接受现状。因为现行体制已经成为阻挡革命洪流的大坝,任何否定的举动,都将让毛主义的幽灵重新开始游荡。
无论自由派是否领受刘小枫的教诲,也无论新法家们最终能否成功捍卫国父的荣誉,更无论在新的儒法斗争中毛泽东是否会被儒教士打成暴君,作为马克思面向的毛泽东却不是可以轻易解决的。
因为这是一种比法家和儒家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惟有它能使人这样自信地宣告:“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当代的政治力量,早已经不再是法家官僚和儒教士之间的斗争,那个历史中面目模糊的人民已经出场,古老的儒家传统和法家传统都免不了成为他借以显现的场所。
无论毛的形象如何朽灭,他作为图腾终将会死去,但他的精神将像幽灵一样徘徊不去。我们期待着这个未来的节日,作为国家主义者图腾的毛的肉体被狂欢的匿名者们放在广场上焚毁,而毛的幽灵从这堆烈火中升腾而出,成为无数匿名者中的一员。
在那匿名者与匿名者的相互信任中,人民的精神像熔岩一样喷出,将烧尽一切儒家,以及法家,于是并且无可朽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