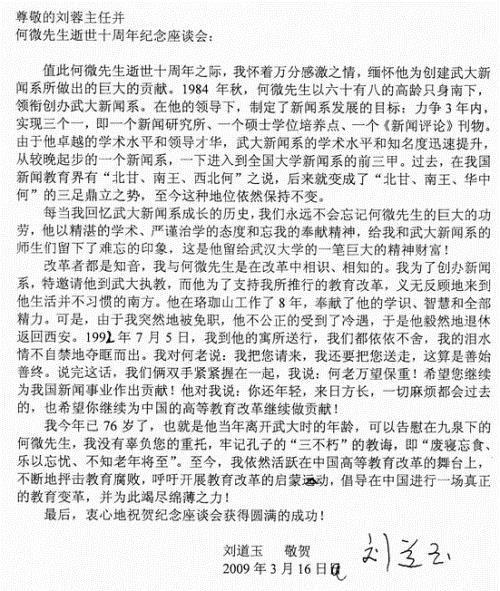武汉大学刘道玉 我与武汉大学—专访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辉煌时期。学界关于给大学松绑,增加教育投入的呼吁,促成了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掀起教育体制改革的高潮。 各地高校中出现了一批教育家和教育改革典型,开放活跃的氛围使大学精神进入复苏、重建的过程。
武汉大学是当时的一座丰碑,是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作为当时国内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率先推行了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取消辅导员、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领全国之先,被奉为“武大的蔡元培”。
如今,刘老已年过七旬,但他仍在为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心竭力,奔波不疲。近日,本报就回顾80年代的武大精神、剖析高等教育现状等问题对刘老进行了专访。刘老以年高体弱之身,在短促的时间内,不顾休息,坚持书面回复本报的提问,并连夜发来,后又发来更正稿。严谨谦和的大家风范,令记者油然而生崇敬感动之情。
是为“追寻缺失的大学精神系列”之二。
1. 80年代的武大精神
《21世纪》:如今,大家提起大学改革和大学精神,对上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是很推崇和怀念的,更是把您称为“武大的蔡元培”。您认为,80年代“武大精神”的核心是什么?
刘道玉:的确,上个世纪80年代是武大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我认为就是紧紧抓住教育改革这个中心链条,我们尝试了许多崭新的教学制度。那时的武大精神就是大学独立,营造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树立勇夺金牌的精神。
比如,我那时所进行的各项改革,除了插班生制度是经过国家计委批准的以外,其他如学分制、主副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等等,我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我认为这些是我的职权。时至今日,20多年过去了,仍然有些省规定,不经过批准不得实行学分制,这简直是笑话!
《21世纪》:大家都知道您不拘一格招揽人才,比如,当年身处困境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被您招进武大。您能否回顾一下,当年您做出这些决定时经历了哪些困难?是什么打动了您?
刘道玉:梅贻琦先生曾说过:“大学非大楼之谓也,而大师之谓也。”这话对我影响很大,我知道要办好武大,延揽大师或者优秀的人才是最为重要的。于是,我发动全校各类人员推荐杰出人才。杨小凯就是我校当时在北京社科院进修教师刘鹰向我推荐的。
为此,我亲自去湖南找到时任湖南第一书记的毛致用,商量为杨小凯彻底平反和调动的事。的确,在杨小凯调入、提升讲师、批准出国、批准他妻子和女儿出国等环节上,都遇到了麻烦,主要是来自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的反对。
但是我对小凯的才华是很欣赏的,我对自己认定的事从来就是一不做二不休。特别是1983年清理所谓的“精神污染”时,有些人想把小凯当作鼓吹自由经济的“自由化分子”批判,把我与杨小凯联系起来,说我重用坏人。当然,我问心无愧,所以泰然处之。
《21世纪》:您的插班生制度和武大作家班,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当年推出这些制度的背景是什么?喻珊曾写过一本《女大学生宿舍》,现在看来,这是一本很大胆的文字,当时是怎样的活跃氛围,能够发表这样活跃的文字?
刘道玉:作家班和插班生制度的确是武大当时教育改革中的两个亮点,从他们当中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人才。萌发这两项改革措施的背景是:第一,过去文人相轻,文学家瞧不起作家,认为他们没有学历、没有高深的学问;而作家又瞧不起文学家,认为他们一生都写不出一本小说来。
于是,我就想打通他们之间的隔阂,借用了遗传学上“杂交原理”,萌发出了要培养学者化的大作家,这一想法与王蒙先生不谋而合。于是,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支持下,武大就创办了史无前例的作家班,先后两期,被称为黄埔一期二期。
第二,插班生的起因有两点:一是我对一次高考定终身甚为不满,希望在高考制度以外,另开辟一条升大学的途径;二是我想把那些自学成才的优秀人才和其他普通大学中学习优秀的学生,以插班的形式招入到武大来,给武大学生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还想把武大已在学但不思进取、学习不好的学生分流出去,形成竞争的局面。
《21世纪》:您是一位化学家,为何钟情于教育事业?您在俄罗斯的留学生涯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道玉:我的主专业是化学,自幼幻想能成为一名诺贝尔式的发明家,可是正当而立之年,我先后被委任为武大副教务长和党委副书记,使我失去了从事发明创造的舞台——化学实验室。但是,创造之梦并没有在我心中消失,而是异化为另一个梦——从事创造教育研究,着力培养更多的创造发明家来。从这时,我就热爱上了教育,特别是创造教育,钻研国内外教育名著,在这一条道路上我踽踽笃行了四分之一世纪。
我崇尚教育改革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我自幼的学习经历,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喜欢跳跃式地学习,对于灌输式的教育极为不满;二是留学苏联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原苏联的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培养制度,基本上是自由民主式的,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例如,我在苏联科学院读副博士研究生,完全是独立自主地学习与研究。导师规定要学习和通过三门课程的考试,但没有教材,不上课,不规定考试时间,入学开始考可以,答辩之前考试也行。科学论文题目和实验方案也发挥学生自己独立思考和独立设计,教授从不包办代替,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创造能力。我在这种培养制度中如鱼得水,这对我在任校长时推行教育改革起了借鉴作用。
《21世纪》:邹恒甫博士创办的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可以说开创了国际化办学的先河。您作为老校长和他的老师,对高级经济研究中心的创立和发展有什么看法?
刘道玉:邹恒甫是我的得意门生,当年正是我找到教育部蒋南翔部长疏通关系,他才得以到哈佛读书,使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获得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杰出人才。我与恒甫之间有不少故事,对他在武大所开展的各项活动是了解的,也是极力支持的。
据我所知,恒甫除了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以外,又创办了武汉大学高级学术研究中心,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内容。这个研究机构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办的高级研究中心。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机构,目的是吸引世界各地的杰出科学家,开展自由民主式的讨论与切磋,以激励新的学术思想的诞生,甚至有可能创建新的学派。
这本来是一个极有创意的设想,可是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他在武大经历了很多挫折,步履艰难。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仍然踯躅笃行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对他的事业,我是支持的,但我爱莫能助,我只能祝福他成功!
2. 创造是一流大学之魂
《21世纪》:您曾经说过,大学必须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做起,特别是要千万百计地物色和培养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大师级的人物。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大学里的大师级学者屈指可数,早已不是上世纪初大师云集的时代。您认为大师匮乏的原因是什么?需要怎样的制度和氛围才能重塑大师时代?
刘道玉:按理说,我国重点大学应当拥有一定数量的学术大师,但是实际上现在能称得上是大师的人真是寥若晨星。这里有一个对大师的理解问题,现在不仅大师少之又少,而且对大师的理解也到了俗不可耐的地步。什么院士是大师,博士生导师是大师,留洋的一个博士是大师,一个商业精英也成了管理大师,简直到了胡言乱语的地步。
到底什么是大师呢?钱穆先生曾说:“大师者,乃是通方之学,超乎各部专门之上而会通其全部之大义者是也。”他又说:“而今日大学教育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成为专家,而不望人为通人。”
由此看来,我国当今出现不了大师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是长期专业化教育造成的恶果。大学里专业越分越细,学生的知识越来越狭窄,大学的教授们往往也只知道一点本专业的知识,所以他们怎么能成为通晓百科的大师呢?
其次,严重的浮躁心态和浮夸的学风,使得许多从事做学问的人滋生了急功近利的思想,从而不能静心下来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我认为做学问就要具有像当和尚那样的精神。什么是当和尚的精神?我认为就是6个字:信念、执著和恬淡。今天的大学有这样甘愿当和尚的学者吗?虽然不能说没有,但肯定是不多。
再次,现在的评估制度和新闻导向都影响了大师的产生。评估是追求数量,宣传是捧杀。一个学者一旦出了一点成就,于是到处作报告,有的马上升官。学者当官已不是个别现象了,这些人虽然还在原单位兼职带研究生,但他们哪里有时间做学问呢?实际上,这也是官本位和华而不实学风的反映。
《21世纪》:中国一直在高喊建立国际一流大学的口号,但直到今天,即使是清华北大这些投入大量国家经费的学校,都与国际一流有相当差距,更不要说其他学校。您认为,一流大学的核心标准是什么?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
刘道玉:环顾世界最著名的大学,没有那一个是规划出来的,也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它不仅仅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漫长的、默默耕耘的过程。中国大学的问题,就出在乱喊口号。自从搞了五花八门的“工程”和提出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口号以后,于是就出现了大学合并风、大学改名风、大专升格风、赶时髦之风、追求大而全之风、互相攀比风、突击上硕士点、博士点,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于是千军万马争过“研究型大学”和“一流大学”这个“独木桥”。
这股浮夸风是自1990年代初开始的,而且是自上而下刮起来的,至今仍然没有刹车的迹象,着实让人忧虑万分。
一流大学的核心是什么呢?我正在写一本书,书名是《创造:一流大学之魂》,这是我对建设中国一流大学思考的心得。现在只提创新而不提创造,实在是一种短视,如果不实施创造教育,创造性的人才哪里来呢?我始终认为,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教育家做职业校长,专心致志地治校;要有创新的、独特的教育理念;要按照创造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培养创造性的人才;要从事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完成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要有学术大师,形成以他们为主体的科学学派。
这些标准是一流大学必须做到的,上述五条也就是我国大学与国外著名大学的差距,不消除这些差距,要想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那只是妄想!
我是一个教育改革论者,也是一个教育危机论者。比如,如果不及时改革,我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危机在10年以后,比现在还要更加严重,因为现在培养的10多万基本上不合格和学风不佳的博士,他们有一个博士的桂冠,所以他们将会充实到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由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养出更多不合格的博士,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怪圈。所以,我预计20年以后,我国的教育和科学水平还要下降,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还要拉大。
《21世纪》:大学,在很多时候都代表着一种精神家园,代表着创新和思想的活力源泉。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学都已沦为职业培训机构,他能提供给大学生的只是应用知识的传授和文凭,而非人的精神的全面塑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您认为,真正的大学精神是什么?如何重新寻回大学的精神动力?
刘道玉:无论在中国或是国外,大学都是最高的学府,是造就优秀人才的基地,是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园地,是新思想、新理论、新文化诞生的摇篮。可是,这些都是以大学独立和自由民主的学风为必要的条件,今天,大学已经衙门化,这里涉及到大学体制改革问题。大学是文化层次最高的地方,因此大学体制改革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率先营造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找回已经失去了大学精神的动力。
3. 振兴的关键在于教育体制改革
《21世纪》:从现在的大学课程来看,以经济学为代表的实用学科可谓显学,学术界也是如此。而曾经的“皇冠上的明珠”的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却落入冷门,很多这些学科毕业的学生也是就业无门。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评价?
刘道玉:现在我国大学仍然是实行专业化教育,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造成的恶果。实行通才教育,这是世界各著名大学共同的经验,也是造就高人文素质人才的必由之路。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周培源、苏步青先生为首的科学家,都呼吁要从专业化教育向通才教育转变,但是20多年过去了,专业化教育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专业越分越细、越来越多,由此可见教育改革的阻力是多么的巨大呀!
至于说到热门与冷门专业,这是相对的。什么东西热过了头,就会冷下来;反之,一门学科冷得太久了,那么它也会热起来的。如果我们实行通才教育,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都是人文素质教育不可少的,他们对于陶冶人的情操、品德和人格具有重要作用,而并非仅仅以谋取职业为目的。
随着大学的大众化,进而普及化,所以以后上大学不再是以谋求职业的技能为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就是培养通用人才,大学毕业生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对口的。这个观点我20多年以前就著文提出过,现在看来越来越明显了。
《21世纪》:您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大学校长。一个好的大学校长不仅仅是属于学校的,也应当是全社会的思想先行者。您对现在的大学校长们有什么样的期许?您认为蔡元培时代的大学精神,有哪些是值得后人传承和发扬的?
刘道玉:1982年9月,我在接见英国上议院的一个资深议员时,他曾经问我:“你认为一个大学校长的职责是什么?”我答:“一个理想的大学校长的主要职责有两点:一是要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优秀的人才;二是一个大学校长要是思想家,他时刻应当走在时代前面,以他的先进的思想影响和引领社会前进。”
我曾经以“中国应当怎样遴选大学校长”为题著文,发表在《高教探索》上。我列举了国内外所有成功的大学校长,如美国的艾略特、博克、陆登廷、雷文和中国的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既是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既心无旁骛地专心致志的治校。
我认为,中国不是没有优秀的人做校长,而是遴选校长的标准不对,没有正确的遴选校长的机制。古代圣贤孟子云:“鱼我所欲也,熊掌我亦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
”由此,我想对现在的大学校长们提出一点希望:我劝你们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带研究生,作一个专心致志的校长。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深刻地指出过:“一个校长,小者影响到千百人的学业,大者则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样的事业难道不值得全心全意地去追求吗?”这话是值得我们现在仍然坚持双肩挑的大学校长们的深思!
美国耶鲁大学之所以办得很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像理查德·雷文(RichardC Levin)这样一批优秀的校长,雷文本是著名的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文学方面的学者,但是他在担任耶鲁大学校长13年内,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倒是写出了《大学工作》专著。
以他为代表的一批职业化校长应当是我们效仿的榜样,希望我国大学校长们不要左顾右盼,不要等待观望,大胆地进行教育改革,充分地行使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办学权,惟有如此,才能领导好自己的大学。
《21世纪》:中国的大学改革的症结在哪里?有怎样的建议?
刘道玉:目前,我国虽然也有些大学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只是局部的添枝加叶式的改革。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我认为主要是没有倡导改革的大环境和宽松的政策,也没有涌现出改革的代表人物和改革的典型。
那么,障碍教育改革的症结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是没有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是大一统的教育体制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开展。1985年5月,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全面论述教育体制改革的权威性文件,但是这个文件基本上没有贯彻实施。
文件指出:“中央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如果依然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领导大学的教育工作,计划经济体制不能振兴我国的经济,难道计划教育体制能够振兴我国的教育吗?
为什么我国大学没有个性、没有特色?为什么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大跃进的速度扩招?大学合并是谁倡导的?为什么大学乱改名和突击升格?现在大学大肆扩大土地和大兴土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教育乱收费为什么禁而不止?素质教育为什么长期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各种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教育“工程”是谁制订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谁造成的?普遍存在的教育不公平又是谁造成的?对这些国家最高的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深思!
国家教育部门应转变职能,要坚决放权,要彻底放权,实现从“大政府抓微观”向“小政府抓宏观”的机制转变。这是大学教育规律和特点所决定的,也是外国大学证明了的成功经验。否则,大学振兴均为奢谈!